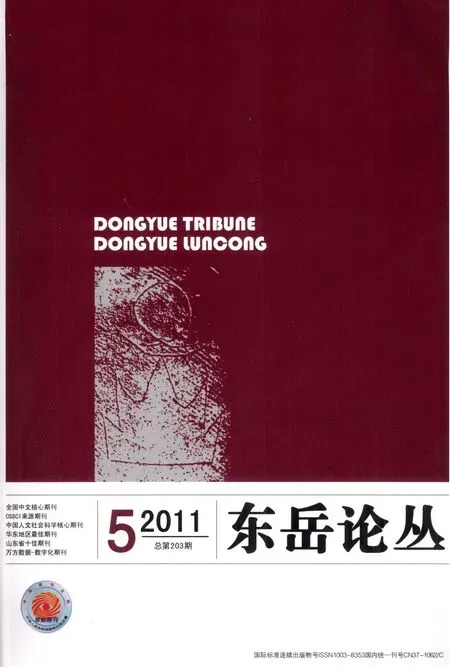近代基督教傳入黔東南黑苗社會的原因探析
莊 勇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 610064;貴州大學法學院,貴陽 550025)
近代基督教傳入黔東南黑苗社會的原因探析
莊 勇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 610064;貴州大學法學院,貴陽 550025)
基督教近代傳入黔東南黑苗社會,究其原因,無論是基督教傳教策略的轉變,還是危機四伏的黑苗社會部分苗民主動或是被動地接納,其實質都是基于功利與現實需要的選擇。
基督教;黔東南;黑苗
一、問題的提出
苗族,這個擁有 89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是中國第五大民族,而貴州約占一半,有 400多萬人。在貴州苗族近現代史上,基督教傳入貴州苗族聚集地是一件影響重大的事件。對于苗族民眾來說,基督教突然闖入他們原本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引起的不僅僅是原有信仰與西方宗教信仰的一場精神會戰,而且還是一場包括價值觀念、生活態度以及生活方式等在內的社會文化大碰撞。
眾所周知,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使英法等國在中國的殖民特權進一步加大,這些條約在傳教方面規定: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游歷、通商、自由傳教;允許教會在內地租買田地,建筑教堂;進入內地傳教的人,地方須厚待保護。這樣,西方基督教(注:這里專指新教,不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傳教士憑借極不平等的各種強勢特權,深入中國內地大肆傳教,地處云貴高原山地農耕社會的貴州黔東南黑苗社會也未能幸免。光緒二十一年(1895),英國基督教內地會總會責令其在西南地區的傳教士們盡快學會少數民族特別是苗族語言,積極在非漢人地區開展傳教 (即所謂“苗疆開荒”)①。1896年,傳教士韋伯和苗族布道員潘壽山,選定清平縣螃蟹 (今凱里市旁海鎮)猴場村中寨,建立了基督教在貴州苗族地區的第一個教會和教堂。為取得苗族民眾的信任,韋伯一邊行醫治病,一邊傳教,吸引部分苗族群眾參加晚禮拜活動。光緒二十四年(1898),澳大利亞籍傳教士明鑒光接替了因病回國的韋伯的傳教工作。同年,明鑒光與苗族布道員潘壽山在“清平縣交界處的黃平州境內”(今黃平縣重安鎮)②被一個名叫許五斤的當地人殺害,此便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旁海教案”。明鑒光死后,旁海傳教點又有傳教士博子頓、切納里、威廉斯等竭力維持,傳播基督教,發展苗族信徒。直至今天,基督教信仰已經融入到這一帶黑苗信眾的日常生活中。
在歷史上,苗族多深居崇山峻嶺之中,受地域所限,苗族各族間幾乎不相往來,語言、習俗也有所差異。在此情況下,早期學者就依照他們的服裝顏色以及其他諸多特性,對其分定了種類名稱。比如以衣服的顏色區分,就有青苗、黑苗、白苗、紅苗、花苗;以居住地域區分,有高坡苗、平地苗、城邊苗、山苗、壩苗等③;另還有根據地名、裝飾等標準為依據而進行的劃分,不再贅述。黑苗是苗族中的一個支系,他們著衣尚黑色,喜食辣,好飲酒,有信仰萬物有靈論的傳統,現主要分布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二、基督教傳播策略的轉變
基督教之所以向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及黑苗社會進發,從其自身動機和目的上看,主要是其傳教策略轉變使然。基督教把傳教區域從城市轉向農村、把傳教重點從中原和沿長江的漢族聚居地轉向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這無不與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與現實的情形有密切的關聯。
首先,由于要與天主教爭奪市場,不得不調整傳教思路。
嚴格意義上講,基督教新教以所謂“合法身份”大舉進犯并在華傳播,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簽訂之后。基督新教組織來華之初,主要是以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為依托開堂傳教的,“因為城市最早向傳教士開放,加上交通便利、人口密集、資源豐富,比偏僻鄉村容易開展布道工作,逐漸形成了來華差會重城市輕鄉村的傳播戰略。在 1865年,無論新來的還是早來的差會,無不把沿海省份和沿長江的城市作為努力的目標。”④但是,“捷足先登”的天主教已占有了相當的地盤,留給新教各派的宗教市場的內部競爭十分激烈;而大多數傳教士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看法,以為城市傳教對周邊的鄉村影響很大,但事實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基督教新教把傳教區域從城市轉向農村,也符合它在華傳教中爭奪更大地盤的初衷和動機。
由城市向農村傳播的轉變,某種意義上講是基督教內部在傳教理念和方式上的轉變。基督教進入中國社會的早期,尤為注重宗教對個人的意義。在傳教理念和方式上,只強調對個人靈魂的拯救和道德層面的教化與凈化,而忽視對個體生存的社會及環境的改造與重建。相形之下,“天主教比新教更重視在鄉村的工作,但其重點更多地放在傳教和‘引人入主’方面”⑤。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過程中,經歷了早期的傳統傳教觀念和方式四處碰壁的體驗后,越來越多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漸漸發現基督教的使命可能不僅僅是對個體的拯救,同時也要拯救個體所生存的環境。正如我國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趙紫宸先生(1888~1979)在《基督教能夠成為中國社會重建的基礎嗎?》(1922)中所說:“即便基督教不以社會整體的重建為目的,它也必須通過使信徒的環境更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完成個體救贖的任務”⑥。這樣一來,如早期只注重在城市發展的基督教“中華內地會”,1875年也到達鄉村⑦,開始重視以醫療、教育等慈善之舉為先行手段的鄉村傳教并因此而名聲大噪。
例如,中華基督教內地會于 1888年派遣英籍傳教士黨居仁到貴州安順地區和黔西北苗族、彝族地區專向苗、彝等民族傳教。1902年,在貴州普定縣苗族聚居的地區建立了教堂。1904年,又到了云貴交界處的赫章縣苗族聚居區葛布傳教,1905年建立了教堂,開辟了“基督教內地會葛布教區”。基督教葛布總堂分為東、西、中、北區四個支堂,從分布區域來看各支堂主要分布于貴州赫章的二、三、四、五、六區,貴州威寧的二、三、十、十一區,貴州水城的四、五區,以及云南的彝良、鎮雄等地,其發展高潮時期,擁有教徒 3萬人,其中苗族占 80%以上,可謂“效果明顯”。
另有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于 1904年派遣英籍傳教士伯格里創立了以貴州威寧縣石門坎為中心的“基督教循道公會石川分教聯區”,以慈善之舉開辦了小學、中學、醫院等,伯格里因此被稱為“苗族的救星”。伯格里在黔西北苗族社會中名聲很大,其傳教范圍還包括云南的昭通、彝良、永善、大關、鎮雄、威信、青明、武定、祿功和四川的琪縣、高縣、綺連等縣。教徒最多時達 6萬多人,以至石門坎一帶的苗族,95%以上(包括未成年的)都是信徒,傳教效果亦很“顯著”。
其次,由于反天主教教案頻發,迫使新教轉變傳播策略。
“沒有殖民主義以軍事力量打開各地大門,世界性的傳教運動根本沒有可能。”⑧雖然,基督教(作者注:廣義的基督教,與新教不是一回事)曾在唐代、元代和明末清初傳入過中國,但性質與鴉片戰爭以后傳入的基督新教完全不同。況且“從康熙末年開始,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歷代統治者都嚴格執行禁絕天主教的政策,也發生了多起教案”⑨。
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通常指的是外國列強利用傳教和教會欺壓中國人民而引起的沖突案件或外交事件。僅以貴州為例,1575年,被羅馬教皇額俄略十三世正式納入澳門教區管轄范圍,“但從 1756年到 1860年,貴州還是先后發生了大小教案 16起,傳教士及教徒被殺者 13人,被打傷者一百多人,還有若干教徒脫離天主教”⑩;鴉片戰爭后,針對天主教,貴州先后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青巖教案”(1861年)、“開州教案”(1862年)和“遵義教案”(1869年)。這些“教案”,表面上看是異質文化之間、外國教會和傳教士與我國民眾之間的矛盾沖突,但實質上不乏深層次的原由,也使“利瑪竇以來天主教在中國的良好態勢轉眼成為泡影。由此觀之,天主教在華傳播過程中的種種失敗經驗教訓,足以讓基督教新教各派當作“前車之鑒”,引以為戒,以免重蹈覆轍。
基督新教把傳教重點轉向非漢人地區即少數民族地區,正是出于主動回避漢人聚居地反洋教的鋒芒的考慮。中原地區是漢人相對集中聚居的地方,傳統的中國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業已本土化的佛教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對西方宗教有極大的排他性;特別是漢族地區文化教育和民眾認知能力普遍較高,而非漢人即少數民族地區情況則大不一樣了。“有鑒于此,以戴德生為首的‘中華內地會’等各種差會認為,西南少數民族經濟文化落后,加之地理環境和人文因素的制約,其接受漢文化影響相對較弱,絕大多數仍保持著本民族比較原始落后的文化傳統,故而易于接受基督教。于是,1895年英國基督教內地會總會責令其在西南地區的傳教士們,盡快學會少數民族語言,就是該策略進入實施程序的第一步。
但是,無論基督教怎樣調整其在華傳播戰略,它早期能夠進入黑苗社會,始終是依仗基督教背后的物質技術文明和殖民主義為強勢后盾,“一切傳教活動得益于歐洲殖民主義和歐洲文明的顯赫。基督教正是憑借西方近代工業革命突飛猛進所取得的物質成果,才得以長驅直入尚處于“刀耕火種”、生產力極端低下的黑苗社會,甚至整個落后的近代中國社會。
三、早期黑苗社會的嚴重短缺
社會危機是宗教發生的必要條件之一,而社會危機總是由于社會的嚴重缺失所致。宗教社會學家格洛克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系統中都難免會有面臨短缺的人群,而在傳統的信仰無法很好地解決他們的這些需要時,他們便會轉而尋找新的答案提供者,接受其他的宗教信仰。早期的黑苗社會就正如格洛克所描述的短缺社會,整個社會資源系統 (包括經濟、社會地位、權利、機會、健康、倫理以及心理等)的嚴重短缺,從而為基督教植入提供了生長的土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黑苗社會反官府的強烈情緒,被基督教“教會不怕官府”的宣言所牽引。
早期黔東南“苗疆”的黑苗是一個飽經苦難的民族,他們反官府的強烈情緒累積已久,這至少可以從雍正年間所謂的“開辟苗疆”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得到印證。“苗疆”是清廷對貴州以苗族為主的聚居地的特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苗疆泛指云、貴、川、兩廣等地區的少數民族居住地;狹義的苗疆主要是指今貴州黔東南的苗族聚居區,除部分侗族外,大多數是黑苗。本文僅以“黔東南”這塊“生苗”區而論。這一區域,作為總理苗疆開辟事務的具體負責人和清廷政令第一執行者的鎮遠知府方顯在《平苗事宜疏》中云:“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勻府以東,鎮遠府以南皆‘生苗’地,廣袤二三千里,……戶口十余萬,不隸版圖。指的就是今天黔東南清水江流域和以雷公山為中心的巴拉河流域的黑苗社會。清雍正年間改土歸流以前,這里幾乎與世隔絕,與外界交往不多,被稱為“苗蠻”、“苗夷”或“生苗”之地。所謂“生苗”與“熟苗”之分,是指“已被納人戶籍,受地方官吏的直接管轄,遭受封建國家賦稅和搖役剝削的少數民族居民,被稱為‘熟苗’。反之,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吏均鞭長莫及,不能進行直接統治和剝削,仍保持某種自立自主狀態的苗民,則屬‘生苗’。有清一代,黔東南“生苗”之患成為清政府西南地區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為拱衛邊疆,消除隱患,將苗疆直接納入流官即朝廷的統治之下,黔東南上述黑苗地區成為雍正年間改土歸流的重點。自雍正五年 (1727)至十一年(1733),朝廷在黔東南用兵 6年,終于達到改土歸流目的,將八寨(今丹寨縣)、丹江(今雷山縣)、臺拱 (今臺江縣)、清江(今劍河縣)、都江(今三都縣)、古州(今榕江縣)正式納入國家王朝體系管理的范圍,這就是所謂“新設六廳”或“新疆六廳”。誠然,“苗疆六廳”的設置,在改變和影響黑苗社會的傳統生活及促進其封建化進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大量的土地、人口被納入流官的控制之下并施以“攤丁入畝”政策,向黑苗民眾征收沉重的賦稅,苗族民眾與封建王朝不可調和的對立矛盾日益尖銳并在不斷的激化之中。與此同時,由于國家權力的強勢介入,清水江流域的航運能力得到空前的開發與提高,過去只限于戰時運送軍需物資、閑時販運食鹽的格局得到大大改變,黔東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運貿易“被納入由沅水經洞庭湖與長江水系連接的全國性市場網絡。雖然,木材貿易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清水江流域兩岸經濟的發展,影響著該區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為漢商進入清水江流域打開方便之門。但是,內地漢人商客的進入在改變黔東南清水江流域的人口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漢商往往憑借雄厚的資本向黑苗及土著民眾大量購買土地,反過來佃租給他們以從中盤剝更大的利益。黑苗逐漸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不得不向清水江、巴拉河沿岸的半山退縮。由于山林已被當地豪強地主占有,靠打獵為生已成為泡影,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黑苗民眾有限的生存技術也無用武之地,其他則無計可施。在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下,接踵而來的便是苗族人民反清斗爭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就爆發過兩次影響重大的苗民起義。一是雍正十三年(1735),在清水江流域黑苗地區爆發的以包利、紅銀領導的旨在反官府苛捐雜稅、欺壓苗族人民的雍乾苗民大起義;二是咸豐五年(1855)在清水江流域和雷公山巴拉河流域黑苗地區爆發的持續時間長達 18年的、旨在減免賦稅的張秀眉領導的黔東南苗族大起義,這些起義都是“被壓迫的生靈”對官府的積極反抗。1896年內地會派傳教士韋伯第一次進入清水江畔的旁海鎮猴場村開堂傳教時,就是打著“教會不怕官府”的旗號迎合那些早已群情激奮的苗族民眾,黑苗群眾對基督教“入教以后不會再受官府壓迫歧視,天災有上帝保佑,人禍有教會抵擋”的宣言抱有好感,部分黑苗群眾加入基督教會,希望由此依靠這個看上去“一點也不怕官府”的組織拯救自己,免遭苦難。可以說,正是在黑苗社會這種民族矛盾尖銳的地區,基督教新教才獲得了生存的空間。
其次,黑苗社群對族群認同和人格尊嚴的渴求與基督教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契合。
黑苗選擇基督教信仰的原始動機,如果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力圖改變其與國家權力間的被動關系的話,那么,他們對人格和族群“尊重”的渴望與追求,則是砸碎沉重精神枷鎖的群體心理的一種表現形式。不僅早期的苗民社會被朝廷侮稱為“蠻”或“夷”,就連上世紀 20、30年代的社會學、人類學學者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這樣稱謂。即便在當代,貴州苗族民族也十分在乎異族對自己族群的看法與態度。每當我們深入黑苗地區調查時,不難發現,黑苗并不是像有關史籍記載的那樣“苗性反復”、“以九股、清江一帶生苗,尤頑梗難化”,而是被他們熱情好客、很講禮數的風土人情深深吸引,從他們歡快的舞蹈和優美動人的“勸酒歌”,都能感知到這個民族對遠道客人的盛情。當然,初到苗家時,客人會高度地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別是對他們簡陋的生活環境、較差的衛生狀況和粗放的飲食方式等不能表現出絲毫的不滿和責怪,這雖然在任何一個民族那里都是共同和相通的,但在黑苗社會,這種行事方式會讓黑苗同胞感到異常的榮幸。一旦苗民的人格和族群得到了應有的尊重,他們會以主人的身份滿腔熱情地接納你的到來,反之,則情況不堪設想。這種反應,顯然是歷史的原因使苗族民眾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對外族特別是漢族人的戒備和防范心理。基督教早期進入黑苗社會時,也充分利用了苗族族群這種共同的心理并大肆宣傳“凡加入教會的都是兄弟姊妹、眾生平等、不分貴賤”等自由、平等、博愛的教義精神,力圖用這些淺顯易懂的說教引起黑苗民眾的共鳴。另一方面,客觀地講,早期進入苗族地區的一些基督教傳教士不辭辛勞,以行醫、救助等現身說法,確實取得了不少苗族民眾的信任。初到旁海黑苗村寨傳教的韋伯夫婦,即在與苗族群眾相處的過程中表現出平等、博愛的姿態,受到部分苗民的好評。
可見,民眾和族群的尊嚴的嚴重短缺,為基督教自由、平等、博愛教義在黑苗社會的植入提供了土壤。
再次,黑苗社會鬼神巫術威力的缺失,為“萬能的上帝”的乘虛而入提供了空間。
苗族和眾多的民族一樣,也經歷了自然、圖騰、鬼神、祖先崇拜等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時期。“原生性宗教一般都保持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觀念,普遍相信人有靈魂,人死后會變成鬼,鬼有善惡之分,可以作用于活人受“萬物有靈”觀念的影響,苗族形成了信鬼尚巫、多神崇拜的原始信仰,直至“公元 1949年前,苗族還停留在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階段在苗族看來,鬼神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常常暗中禍害人們的生產生活,影響人們的生老病死。需要指出的是苗族雖然信仰鬼神,但并沒有把鬼神崇奉到絕對主宰的地位。因此,為了族群的興旺發達、個人和家庭免除災難而獲得幸福,就必須祈求神靈的保護,驅鬼除惡。不過,在神靈與人間之間,還必須借助巫師這個中介實施巫術,妖魔鬼怪才得以驅除。苗族的巫師是指專門從事溝通人世鬼神兩個世界信息的、具有一套遣神差鬼、呼風喚雨、起死回生之超凡法術的人,又稱為鬼師。“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可見,苗族的巫師既有男覡,也有女巫,他們都是苗族社會溝通人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中介。不過,苗族的巫師大多是村莊里不脫產的農民。關于初民社會的人們為什么相信巫術,功能論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當遇到艱難險阻時,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其次是因為知識力量的不足,從而對難以駕馭的對象產生了恐懼和焦慮,“在他的軀體中產生了一種不穩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追尋一種替代的行為”,“讓那遏制的緊張情緒奔放出來,賦予主體以勇氣、信心和力量,于是有了巫術,這也是巫術最基本的文化功能。這種解釋也適合黑苗初民社會巫術信仰的基本理由。至于鬼師如何施展巫術魔法降妖除怪,這則是苗族巫術最神秘的部分,通常凡人是無法知曉的。從石朝江在其《中國苗學》一書中介紹的鬼師的“招魂”和“指路”兩種巫術的施術全過程來看,除了巫師“單哼”、“打卦”等儀式之外,更重要的是請求施法的主人家必須按照巫師的要求,備好錢財物,如雞鴨魚肉等犧牲品、香蠟紙燭、米酒、谷物等一樣都不能缺。至于巫術是否靈驗,誠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這主要取決于巫師個人的聲望,巫術奇跡的神話能夠強化人們的信賴感,而且只要一次成功,就能夠遮蓋多次失敗,而失敗又可以用“反巫術”來掩飾,這種詮釋無疑是經典的。但歸根結底,巫術被初民社會廣泛采用,還是由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思維方式及認識能力之局限。“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發展,原始思維的邏輯方式的增強,巫術也就一點一點喪失其固有的文化功能而開始了緩慢消失的歷程。概言之,巫術的可信度和巫師的神圣權威,最終要面臨人類認識水平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嚴峻挑戰,“鬼神巫術一旦被攻破,信仰的危機就為新宗教的侵入開了缺口。在早期乃至今天的黑苗社會,絕大多數基督教信徒普遍承認放棄對鬼神巫術崇拜的主要理由之一,完全是基于一種對經濟成本核算后的考慮,“苗中以做鬼為事,或一年三年一次,費至百金或數十金,貧無力者,賣產質衣為之。確實,當黑苗民眾的人間苦難并不能依靠鬼神巫術得以解救、反而會因巫術法事耗費大量難以承受的錢財時,“萬能的上帝”便款款地來到了他們面前,逐漸走近其中一些人的心中。
綜上所述,對于基督教早期傳入黑苗社會的事實,究其原因,無論是基督教傳教策略的轉變,還是危機四伏的黑苗社會部分苗民主動或是被動地接納,其實質都是基于功利與現實需要的選擇,這才是對這一雙邊行為的合理解釋。
[注釋 ]
①林建曾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貴川地區傳播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 445頁。
②[英]塞繆爾·克拉克:《在中國的西南部落中》,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 75頁。
③吳澤霖,陳國鈞等:《貴州苗夷社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 3-4頁。
④⑤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 (1907-19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32頁,第 2頁。
⑥T.C.Chao,“Can Christianity be the Basi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53 (May 1922),p315.
⑦K.S.Lato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 p389.
⑧中國基督教協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9頁。
K25
A
1003-8353(2011)05-0088-04
莊勇,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貴州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