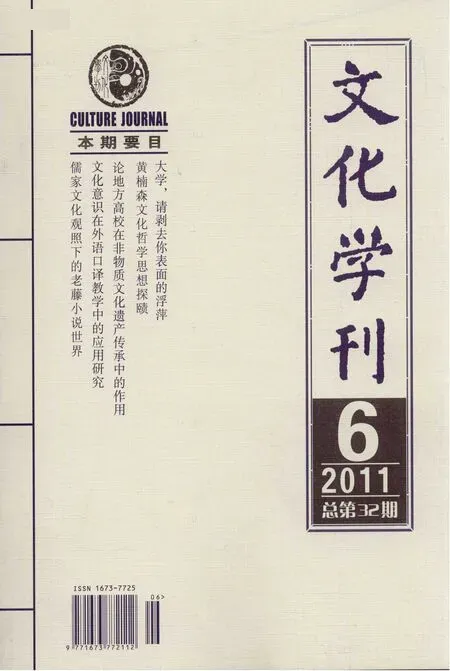南宋佛教水陸畫及其商業(yè)化進程
申小紅 郭燕冰
(佛山市博物館歷史研究部,廣東 佛山 528000)
一、前言
近年學術(shù)界有不少關(guān)于水陸畫的研究論文和專著,例如,《山西省博物館.寶寧寺明代水陸畫》,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黃河《元明清水陸畫淺說》上、中、下,載于《佛教文化》2006 年 2-4 期;姚雅欣《旨一韻殊——京、晉博物館藏水陸畫比較研究初論》,載于《中國博物館》2010年第一期;白萬榮《西來寺明代水陸畫‘天龍八部’詮釋》,載于《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第五期;白萬榮《青海樂都西來寺明水陸畫析》,載于《文物》1993年第10期;柳建新《泰山岱廟館藏水陸畫初探》,載于《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蘇金成《水陸法會與水陸畫研究》載于《南京藝術(shù)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葉削堅《水陸畫及水陸法會儀式》,載于《絲綢之路》2004年;王國建《水陸畫研究的“圖像學”意義》,載于《中原文物》2010年第五期;李德仁《山西右玉寶寧寺元代水陸畫論略》,載于 《美術(shù)觀察》,2000第8期;趙慶生《水陸畫造型藝木再認識》,載于《文物世界》2007年第2期;李欣苗《毗盧寺壁畫引路菩薩與水陸畫的關(guān)系》載于《美術(shù)觀案》,2005年第6期;趙燕翼《古浪收藏的水陸畫》,載于《絲綢之路》,1994年第3期;謝生保,謝靜《敦煌文獻與水陸法會》載于《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謝生保《甘肅河西水陸畫簡介——兼談水陸法會的起源和發(fā)展》,載于《絲綢之路》2004年;謝生保 《河西水陸畫與敦煌學——甘肅河西水陸畫調(diào)查研究簡述》,載于《隴右文博》,2004年第2期;徐建中 《懷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陸畫》,《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圣凱《漢傳佛教水陸法會大觀》,載于《中國宗教》,2003年第 9期;戴曉云《公主寺水陸畫新釋》,載于 《佛教文化》,2010第3期;戴曉云《北水陸法會修齋儀軌考》載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一期;戴曉云 《佛教水陸畫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09年5月版;周雅非《從水陸畫看清末四川民間的十王信仰》,載《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1期等等。
即便研究成果頗豐,但是水陸畫的研究一直難以走進深層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是有其自身原因的:第一,它屬于工匠作品,甚至是流水線商業(yè)作品,作者其名不彰,水平參差不齊,歷來不受繪畫研究者重視,因此缺乏文獻資料的記載;第二,出于其實用性,作品流散各地,損耗時有發(fā)生,導致現(xiàn)存水陸畫處于散亂狀態(tài),無法進行系統(tǒng)研究。
關(guān)于水陸法會,在一些論文、論著中已形成共識,“水陸法會曾經(jīng)是風行中國朝野,歷時最長,規(guī)模最大,法事最多,儀式最隆重的一種經(jīng)懺法事活動。它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歷史。它始于南北朝,歷經(jīng)隋唐、五代,到宋代形成規(guī)模,元明時期達到鼎盛,清代晚期逐漸衰落,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內(nèi)已基本上消亡。近年來,港臺地區(qū)和南方等地的一些寺院又有舉辦,但已不完全按照古代儀軌。”[1]港臺和南方一些寺院的水陸法會仍然舉辦得相當隆重,而且以皇家禮儀來操辦,為整個國家祈求祥和,是佛門盛事。
對于水陸畫的歷史、內(nèi)容、功能,已有不少論著進行了研討,并大有成效。如今國內(nèi)流傳的水陸畫大部分為明清制品,李德仁《山西右玉寶寧寺元代水陸畫論略》認為山西寶寧寺的水陸畫是元代作品,如得到有力實證,這批水陸畫已經(jīng)是現(xiàn)存最早的水陸畫實物了,但是早在宋代已有關(guān)于水陸畫的記載,學者謝生保考據(jù)敦煌文獻,證明南北朝時期已出現(xiàn)“水陸法會”的字眼。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評價南宋的宗教生活時說:“沒有比十三世紀中國人的宗教生活更多采多姿的了,即使冒過分草率簡略的危險,我們亦須首先將這種鼓舞熱烈宗教生活的精神加以解釋一番。”[2]而王伯敏的研究從側(cè)面印證了宋代民間繪畫的熱情:“宋代民間繪畫的活動,隨著農(nóng)村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高漲,顯得比較活躍。”[3]
在本文,我們將對水陸畫在宋代特別是南宋的發(fā)展及商業(yè)化進行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二、水陸畫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關(guān)于“水陸畫”的概念及范圍定義。
目前,一些研究者將宗教繪畫籠統(tǒng)歸入水陸畫,其實水陸畫與水陸法會一樣,是有其科儀的,現(xiàn)行的《水陸儀軌會本》中就有所記載,附錄中專辟一章《重訂水陸畫式引》,文后的落款年代為道光甲申七月,稱舊時 “水陸之有畫像,由來舊矣……各處道場,隨意造作,從無畫一……隨畫師所傳,頗不的當,知其泯失,由來已久”[4],于是“依照儀軌中所列名類,每位分為三軸,庠序安列,譜為定式,復各為之說,以申明之,自今以往,畫師可以按譜而繪,一改從前混淆之作。”[5]所以后期成熟的水陸畫一般成套出現(xiàn),稱一堂,在裝幀、尺寸、構(gòu)圖上均有統(tǒng)一樣式,但水陸畫發(fā)展成熟的過程是長期和曲折的,地域跨度較大也導致區(qū)域差異的產(chǎn)生,所以統(tǒng)一的形制在不同的地區(qū)和時期有不同的體現(xiàn)。
我們留意到大部分在水陸畫研究中沒有重視裝幀方面,甚至很少提及尺寸。還有一些將壁畫歸入水陸畫中,如《公主寺水陸畫新釋》、《懷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陸畫》等,謝生保曾指出水陸畫與壁畫有著深厚的淵源:“河西水陸畫可以說是敦煌藝術(shù)的延續(xù)”[6],但并非所有宗教壁畫都可以歸入水陸畫類別,水陸畫在功能和場地方面都有所特指,是在舉辦水陸法會時使用的圖像,而非日常裝飾廟堂的圖像。
關(guān)于水陸畫的形制,有研究者認為“我國在宋代已盛行在水陸法會上供奉水陸畫。水陸畫原為軸幅,長方形,以后寺院根據(jù)水陸畫軸幅粉本繪制為壁畫。”[7]壁畫和軸幅之間的關(guān)系除了同時并存的可能性外,從不可移動的壁畫形式向可移動的卷軸發(fā)展,于保存及使用兩方面來說均有所改進。進而言之,并非所有的卷軸宗教繪畫都屬于水陸畫,僅僅在佛山,與宗教有關(guān)的神相、門神、年畫、文人畫就不勝枚舉,都不屬于水陸畫。因此,我們認為,水陸畫是一種用于水陸法會的宗教畫像,有其統(tǒng)一的儀軌。
關(guān)于水陸法會緣起以及水陸畫在水陸法會中的使用方式,研究者已經(jīng)考察得非常清楚:“水陸畫是佛教寺院舉行水陸法會(又稱水陸道場、水陸齋會)時專門懸掛的宗教畫。水陸法會是一種宗教儀式。據(jù)佛教經(jīng)籍載,釋迎牟尼弟子阿難夜夢餓鬼面然,佛遂授阿難以經(jīng)咒,誦以超度。現(xiàn)傳佛藏中有《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jīng)》一卷。中國的水陸法會起于南朝梁武帝時代。“梁武帝制作‘水陸’的年代,各典籍記載不一,《事物紀原》認為是天監(jiān)七年(508),而《佛祖統(tǒng)紀》認為是天監(jiān)四年(505)。 ”[8]
《佛祖統(tǒng)記》卷三十三載:“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日: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chuàng)立儀文,三年而后成。……天監(jiān)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修設(shè)。帝親臨地席,詔(僧)佑律師宣文……此齋流行天下。”水陸法會所請的佛菩薩眾神諸鬼無所不包,其中有諸佛、眾菩薩、明王、金剛、羅漢及婆羅門仙,還有諸天、地獄、山川、河讀神靈以及社會各階層,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或正寢或屈死的鬼魂,這些都要畫在水陸畫上。無論是阿難夢面然餓鬼的傳說,還是梁武帝夢神僧告以六道四生受苦無量,都說明水陸法會的主要著眼點是撫慰超度那些受無量之苦的餓鬼冤魂。由于封建社會政治腐敗,統(tǒng)治殘暴,戰(zhàn)爭頻繁,災禍不斷,人民深受苦難,積怨很深,社會矛盾激化,這對于皇朝的統(tǒng)治極為不利。“水陸法會的舉行,正是通過對死者的安撫,給生者以慰藉,從而緩解社會矛盾,消除社會積怨,以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因此作為水陸道場重要設(shè)施的水陸畫的意義,并非一般寺廟雕塑壁畫所能替代,這就是水陸畫歷代一直流行的原因。 ”[9]
水陸法會規(guī)模一般較大,通常做7天,有的多至49天。寶寧寺地處邊防,故其水陸道場時間較短,定為三天。儀式時將諸佛菩薩神鬼畫像按序列懸掛,一卜設(shè)靈牌,上書各自名號,焚香并供以精美飲食。設(shè)壇誦經(jīng),請諸佛神仙餓鬼冤魂到位,每夜放焰口—施食。施食時“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凈地”,故稱“水陸”。最后夜“送圣”,即將所請諸佛神鬼全部送走,儀式結(jié)束。
三、宋代的“水陸法會”
“水陸法會”的最早實施應該在宋代熙寧年間(1068-1077),東川楊鍔所撰水陸儀軌(又稱為“楊推官儀文”),流行于四川,這是較早的水陸儀軌的完整形態(tài)。
元祐八年(1093),蘇軾為亡妻宋氏設(shè)水陸道場[11],并且撰《水陸法像贊》16 篇。 蘇東坡在《水陸法像贊序》中說,水陸道場隨后世而增廣,惟有四川保存有古法,而且各種畫像及設(shè)施仍然保持著原來的風格。因為他本是四川眉山人,所以他作的《水陸法像贊》就被稱為“眉山水陸”。宋元豐七、八年間(1084-1085),佛印(了元)住金山時,有海賈到寺設(shè)水陸法會,佛印親自主持,蔚為壯觀,遂以“金山水陸”馳名,“金山水陸”又稱為“北水陸”。
紹圣三年(1096),宗賾刪補詳定諸家所集,完成《水陸儀文》4卷,普勸四眾,依法崇修。現(xiàn)在,《水陸儀文》已經(jīng)失傳,僅從其所撰《水陸緣起》一文,可知其內(nèi)容之一斑。
南宋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曾經(jīng)經(jīng)過鎮(zhèn)江金山寺,慕水陸齋會的盛況,于是布施田地百畝,在四明東湖月波山專建四時水陸,用來報答四恩,并且親制疏辭,撰集儀文。宋孝宗聽到這個消息,特別頒賜以“水陸無礙道場”寺額。
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師徒道俗3000人,布施財產(chǎn),購買田地,遵奉月波山四時普度之法。大眾又誠心請志磐大師續(xù)成《水陸新儀》6卷,大力推廣齋法,并且勸十方寺院,重視齋法,大興普度之道。
水陸法會自從宋代流行以后,很快普及于全國,特別是每次戰(zhàn)爭后,朝廷上下經(jīng)常舉行超度法會。宗賾《水陸緣起》中說,供養(yǎng)一佛、齋一個僧人,尚且有無限功德,何況普同供養(yǎng)十方三寶、六道萬靈,不但能使自己得到利益,而且能夠恩沾九族。所以,在江淮、四川、廣東、福建,水陸佛事自此十分盛行。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如果有人為了祈求保護平安而不施設(shè)水陸,那么就會有人認為他不善;如果追悼懷念長輩而不設(shè)水陸的話,就有人認為他不孝;如果救度卑微、幼小的眾生而不設(shè)水陸,那就是不仁慈。所以,在江南地區(qū),富貴有錢人獨自舉行水陸齋會,貧窮者則共同出錢修設(shè)法會,這也就是后世所謂“獨姓水陸”和“眾姓水陸”的來源。水陸法會儀軌自宋代以來,經(jīng)過不斷的增補,日趨完善。現(xiàn)代水陸法會壇場的布置、念誦經(jīng)典及其人數(shù),牌軸的規(guī)定和進行的程序等,參照《雞園水陸通論》等典籍。[11]
水陸畫隨著水陸法會的興盛而發(fā)展,繪制的軸數(shù)越來越多。蘇東坡為亡妻修設(shè)水陸道場,并作《水陸道場法像贊》16篇,當時可能懸掛水陸畫16軸。南宋末年,志磐法師所著《水陸新儀》六卷中,規(guī)定懸掛水陸畫26軸。到了明、清之時基本定型,一堂水陸畫一般為120幅,主要依據(jù)水陸法會的規(guī)模大小來定。私人家庭修設(shè)的水陸法會,少者36軸,多者72軸。地方大型寺廟修設(shè)的水陸法會,一般為120軸左右,朝廷修設(shè)的水陸法會,多達200余軸。“最初水陸畫以佛教諸佛、諸菩薩、諸神為主,唐宋之后,隨著儒、釋、道三教融合,道教諸神、儒家諸神、民間諸神逐步進入水陸畫,水陸畫中所繪的內(nèi)容也變得十分龐雜。”[12]
至明清時期,水陸法會已成為一種寺廟文化活動,廣泛流行于社會。每年農(nóng)歷七月十五日,全國各地的大型寺院、道觀都要舉行水陸法會。“今天,人們在七月十五日上墳,給死者燒紙上香,供獻食物,半月食齋,以及正月初八拜閻王,也都是水陸法會的遺風。 ”[13]
四、宋代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最初由印度傳來,進入中原后在敦煌莫高窟創(chuàng)造了璀璨的石窟藝術(shù),后沿著河西走廊逐漸南移和東移,在北宋時期來到了四川一帶,后東移至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一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南方佛教造像體系。
宋代開創(chuàng)了繼南北朝、唐朝之后中原佛教藝術(shù)的又一高峰,宋太祖在建國之初改變了后周的滅佛政策,重修寺廟,廣納僧尼,大造佛像。除徽宗外,歷代皇帝對佛教皆持扶植態(tài)度,民間也廣為呼應。
五代及宋,禪宗獨盛,佛教繪畫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嚴謹整飭的佛傳圖、經(jīng)變故事畫衰落了,開始流行羅漢圖及禪僧的頂相 (祖?zhèn)鞣◣熜は?圖等。
自南宋,佛教石窟藝術(shù)的重心已經(jīng)轉(zhuǎn)移至南方,敦煌雖然仍在建造,但日益衰減,究其原因,有研究者作出了解釋:“敦煌石窟藝術(shù)在元代終止的原因:一是宋代之后,南方沿海水上絲綢之路開通,北方內(nèi)陸絲綢之路衰敗。敦煌石窟藝術(shù)的營造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二是明王朝雖然推翻了元王朝,但無力收復河西走廊全境和新疆地區(qū),便以嘉峪關(guān)為界,盡遷敦煌、安西、玉門地區(qū)的居民入關(guān),致使敦煌成為域外之地。那些創(chuàng)造敦煌藝術(shù)的畫師、工匠便回到了家鄉(xiāng),或流落到了酒泉、張掖、武威等河西諸縣。為了謀生,便為河西諸縣寺院繪制壁畫和水陸畫。”[14]這段話同時解釋了河西有大量元、明、清水陸畫出現(xiàn)的原因。
南方佛教造像藝術(shù)的出現(xiàn)表明中國佛教藝術(shù)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漢化時期。
宋代尤其是南宋,繪畫崇尚寫實,線描藝術(shù)達到了成熟期,這時的佛教繪畫尤其是水陸畫也染上了濃郁的時代風格。即使流傳到元、明、清以及日本、朝鮮等地,這些特點仍如影隨形地出現(xiàn)在畫面上,這方面包括宋代的服飾、場景等。由于追求寫實,由印度傳來的異域之風一掃而光,人物形象完全依照宋代中原人民的形象來塑造;因為技藝的精湛和成熟,全用本土的技術(shù)(線描、賦色)進行描繪,且惟肖惟妙,纖毫畢現(xiàn),這些作品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隨著佛教向東亞的傳播,逐漸流傳到地區(qū),在該地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本土化,但其中的漢化因素,特別是宋代風格,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五、南宋佛教水陸畫的商業(yè)進程
為了佛教傳播更加方便和更為深遠,宋代佛教造像出現(xiàn)了兩個轉(zhuǎn)變,一個是卷軸形式,一個是商業(yè)化。
出于傳播的方便,石窟、壁畫等藝術(shù)形式逐步向卷軸書畫的形式轉(zhuǎn)變。從石窟到壁畫再到卷軸這樣的發(fā)展軌跡,在現(xiàn)存實物中有多方面的體現(xiàn)。從歷代佛教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時間看,敦煌石窟從南北朝開始開鑿直到元代,四川石窟始于唐代而盛于宋,隨后元、明、清、民國年間,較大型的宗教藝術(shù)多是畫軸或木刻印版。從形式上講,佛教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從本來的內(nèi)向自省型轉(zhuǎn)變?yōu)橥庀騻鞑バ停诮趟囆g(shù)品是表達制作者虔誠皈依的媒介,所以早期的石窟造像都在漆黑、狹小的室內(nèi),并不刻意面向觀眾;后來為了宣揚教義,著重其教化作用,才面向更多的人群。因此石窟、壁畫的不可移動性并不利于攜帶和傳播,而紙張的出現(xiàn)、卷軸的形制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
佛教繪畫的大量需求催生了商業(yè)化的手工作坊。在南宋時期的寧波就出現(xiàn)了一批這樣的畫家,最出名的有林庭珪、周季常等。
源自于印度的佛教地獄繪畫形式擅變漢化以后,畫中的十殿閻王以及各殿的情景,均浸淫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官僚府衙的權(quán)階色彩。
我們從現(xiàn)藏于海外的南宋時期有關(guān)十殿閻王及地獄的繪畫中看出,這些出自民間畫師筆下,形象生動,顏色艷麗,融釋、道于一體的宗教觀念的水陸畫,在當時已為海外大量接受,主要原因是南宋時期的朝鮮與日本受我國影響,開始流行漢化佛教地獄的信仰,緊接著對于這類水陸畫的需求也與日俱增,12世紀中期至13世紀,南宋對外商埠的貿(mào)易大港寧波,因其海運傳輸之便,成為當時民間畫師菌集之地,并成了專門繪制水陸畫銷往海外的作坊式的中心,所以,“就我們所知道日前許多流失海外的《十殿閻王圖》,主要自南宋以來,均先后被日本與南朝鮮公私收藏。由此傳播渠道影響了日、高麗有關(guān)地獄經(jīng)變和六道輪回的信仰。 ”[15]
宋朝與日本的商貿(mào)比前代顯著增多。當時中日兩國商品貿(mào)易種類凡多,佛教經(jīng)典亦成為商人貿(mào)易品。被派往宋朝的日本僧人,回國時大多攜帶大批佛經(jīng)、其它典籍、繪畫文物而歸,輸入日本的不僅有佛教經(jīng)典及儒家書籍,而且還有書畫藝術(shù)亦隨同佛典。東初法師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對此有詳細敘述,列舉了數(shù)位禪師帶回的書畫經(jīng)典或高僧寫真畫像。
南宋時期日本僧侶和幕府將軍都非常賞識南宋院體畫風的作品,寧波畫師所繪制的佛教畫像大批量地輸入日本,至今仍數(shù)以百計地保留在那里,主要藏于寺院中。京都國立博物館保存了日本各大寺院的珍品,主要有:北宋《十六羅漢像》(京都清涼寺藏);南宋《無準師范像》(京都東福寺藏);南宋《不空三藏像》(京都東福寺藏);南宋陸信忠《十六羅漢圖》軸(十六幅,京都相國寺藏);南宋林庭珪、周季常《五百羅漢圖》(京都大德寺藏);南宋金處士《閻王圖》軸;元代佚名《十王圖》(京都大德寺藏)等。金大受和陸信忠等寧波佛教畫傳到日本后,大都被日本的畫師所臨摹,其影響不僅發(fā)生于日本的佛教繪畫,而且波及到以后日本繪畫的各個方面。奈良藏《十王圖》的組畫,原本為十幅一套,現(xiàn)在日本存有十余套。此外,在歐美如柏林東亞藝術(shù)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shù)館也有收藏。
奈良藏《十王圖》署款:“慶元府車橋石板巷陸信忠筆”,大都會《十王圖》上的朱砂色署款:“大宋明州車橋西金處士家畫”。明州即今浙江寧波,當時日本僧人或商人渡海來中國,大多在寧波上岸,寧波是當時中國沿海最重要的口岸,這些商品畫的售畫對象也主要是日本或朝鮮的僧人、商人。“金處士”畫史無傳,只知是明州車橋人,當是民間的藝人。他們根據(jù)所傳粉本(有時略為改動),或者在當?shù)厮略褐挟嫳诋嫽蛘弋嬃笋殉删磔S放在市場出售。林庭珪、周季常的《五百羅漢圖》也是如此,畫上多題寫作者姓名、地名,其性質(zhì)與《閻王圖》同,共有一百幅,原為日本京都大德寺收藏,現(xiàn)有82幅藏原處,少數(shù)由美國人購買轉(zhuǎn)贈給波士頓等美術(shù)館。
六、結(jié)論
水陸畫在宋代出現(xiàn)有明確的記載,是蘇東坡為亡妻宋氏修設(shè)水陸道場,并作 《水陸道場法像贊》16篇,是歷史記載上首次出現(xiàn)“水陸畫”,但水陸畫及水陸法會儀軌并非橫空出世,它們是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逐步衍變而來的。
佛山博物館就藏了近百幅這類作品,這些作品尺寸較大,與謝生保提到的河西水陸畫的尺寸相仿:“甘肅河西四縣市博物館所藏的水陸畫,最早年代為明代中、晚期,最遲為民國時期。所有水陸畫全為卷軸裝,繪制裝裱有絹繪絹裱、紙繪紙裱、布繪綾裱等形式。畫幅不計裝裱天地邊飾,一般高120~150厘米,寬70~90厘米。若計裝裱尺寸,一般高 260 厘米,寬 120 厘米。 ”[16]
十王像每王一幅,羅漢既有獨幅的,也有兩人一幅的,似乎不單是用于陳列懸掛,是否也用于法會呢?經(jīng)過實地訪查,答案是肯定的。但十王在后期多出現(xiàn)于道教醮會中。如此看來,這些畫作仍屬于廣義上的“水陸畫”,但它與后期佛教水陸儀軌中的水陸畫相去較遠,相信是水陸法會經(jīng)過歷朝歷代的修改越加完善,而本來的樣式又逐漸流傳并發(fā)生變化。
佛教圖像的實物流傳顯示了宗教繪畫從民間信仰轉(zhuǎn)化為商業(yè)繪畫的歷程,通過它們我們可以更直觀地接觸到普通百姓的民俗文化和生存狀態(tài),即觸及到象征主義中所提的“不在場的中心”。宗教信仰伴隨著人們的觀念在民間不斷衍變,每一個細微的轉(zhuǎn)變均以極其微妙的姿態(tài)在宗教繪畫上呈現(xiàn),人類也因這些宗教產(chǎn)物獲得了救贖和人文的積累。
為什么我們比較關(guān)注南宋水陸畫呢?因為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明清以來,作為全國著名的手工業(yè)城市之一的佛山,在宗教繪畫方面與南宋時期的寧波有許多相似之處:相似的作品,相似的風格,相似的手工業(yè)作坊,相似的店鋪印章。可以說,明、清、民國時期,佛山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了寧波宗教繪畫的手工業(yè)作坊的技法,這些從側(cè)面印證了宗教特別是佛教造像中心在明清時期繼續(xù)南移的事實,而這種轉(zhuǎn)移并不是單單是宗教造像的轉(zhuǎn)變,而是順應了時代局勢的大規(guī)模的文化中心的南移,因為從宋代開始,中原傳統(tǒng)文化的重心南移,[17]明清時期的佛山在宗教繪畫方面與南宋的寧波有驚人的相似,是宗教造像藝術(shù)的南移的結(jié)果,也就不難理解了。北方地區(qū)如山西、河西發(fā)現(xiàn)的水陸畫屬于皇家形制,而佛山的水陸畫則屬于南方民間形制,在明清時期通過外銷途徑傳播到東南亞各國。
[1] [6] [14] 謝生保.河西水陸畫與敦煌學——甘肅河西水陸畫調(diào)查研究簡述[J] .隴右文博,2004,(2):54.
[2] [法] 謝和耐.南宋社會生活史[M] .臺北: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160.
[3] 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M] .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366.
[4] [5] 水陸儀軌會本:據(jù)明代高僧云棲訂本重刻[M] .上海佛學書,2002.145,146.
[7] 徐建中.懷安昭化寺大雄室殿水陸畫[J] .文物春秋,2006,(4):59.
[8] 圣凱.漢傳佛教水陸法會大觀[J] .中國宗教,2003,(9):56.
[9] 李德仁.山西右玉寶寧寺元代水陸畫論略[J] .美術(shù)觀察,2000,(8):62.
[10] 蘇軾.東坡后集:卷十九[A] .東坡七集[C] .北京:中華書局,1936.
[11] 宗凱.漢傳佛教水陸法會大觀[J] .中國宗教,2003,(9):56.
[12] [16] 謝生保.甘肅河西水陸畫簡介——兼談水陸法會的起源和發(fā)展[J] .絲綢之路,2004,(1):10.
[13] 周雅非.從水陸畫看清末四川民間的十王信仰[J] .中華文化論壇,2009,(1):104.
[15] 張縱,趙澄.流失海外的〈十王圖〉之考釋[J] .藝術(shù)百家,2003,(4):140.
[17] 張全明.試析宋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心的南移[J] .江漢論壇,2002,(2):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