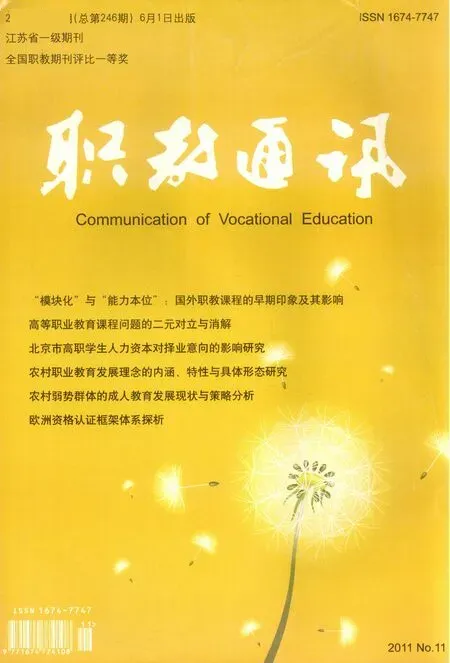“模塊化”與“能力本位”:國外職教課程的早期印象及其影響
張宇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300072)
“模塊化”與“能力本位”:國外職教課程的早期印象及其影響
張宇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300072)
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職業教育的課程領域產生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變革。這些變革無疑受到了外來經驗的啟示,其中與國際課程模式相伴而來的“模塊化”與“能力本位”觀念更是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但是,在本土化的探索過程中,“模塊化”與“能力本位”的最初含義卻又逐漸發生了變化,由此帶來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原型引入”的范圍。
職業教育;課程;模塊;能力本位
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業教育課程的發展變遷,源自國外的影響可以說是一種持續性的誘發因素,特別在相對成熟的本土化探索出現之前,課程改革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一派“拿來主義”的景象。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大致說來始于20世紀80年代,結束于90年代中期,其間德國的“雙元制”、國際勞工組織的“MES”、加拿大的“CBE/DACUM”等各色名目的課程模式①相繼引入國內,每一種模式都伴隨著一定規模的試點,隨之更出現了一批極有價值的經驗總結——某些日后頻繁使用的新概念,例如“模塊化”與“能力本位”,即從這里生發出來,它們所起到的積極抑或消極作用遠遠超出了上述實踐本身。
一、“拿來主義”的實踐與反響
(一)移植“雙元制”的嘗試
對于“雙元制”(Dual System,當年也曾譯作“雙軌制”)的移植,在最初的學習、借鑒過程中堪稱一次典型性的嘗試。“從1983年開始,中國與德國在技術合作的框架內建立了30余個冠以‘雙元制’模式之名的企業培訓中心或職業學校,這些職業教育機構進行的基本上是‘原型’模式的改革試驗。在該類改革模式中,德方提供實驗經費、教學設備、教學文件、并派遣專家;中方則按照德國的培訓條例、教學計劃和課程方案開展教學活動,其教學組織形式及教學方法也基本上采用引進的德國原型”。[1]后來,這方面的探索進一步拓展到涉及蘇州、無錫、常州、蕪湖、沙市、沈陽等六城市的區域性的試點實驗,各地行政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強化校企聯系的措施,取得了不少教學管理上的經驗。然而,直到以上改革紛紛落下帷幕,原汁原味的德國式的職教課程始終沒有在國內流行開來。
(二)引進、推廣“模塊式技能培訓”
差不多在“雙元制”引進的同時,我國勞動部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合作也進入到實施階段。1985年,雙方共同建立了“天津高級職業技術培訓中心”,開始從事“模塊式技能培訓”(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簡稱MES)相關資料的翻譯、出版工作。“MES”是國際勞工組織推出的一種新型職業培訓方法,它基于對每個工種、任務和技能的深刻分析,嚴格按照工作規范,開發出不同的培訓模塊,采用類似于積木(即“模塊”)組合式的教學形式,從而保證用什么學什么。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接受這種模式培訓的骨干已達萬余人,輻射面約百萬人,分布在大陸除西藏外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涵蓋大部分行業和系統。[2]由我國自行編寫的MES教材涉及數百個工種,開發教材數量之多,銷量之大,世所罕見……不過,上述這些進展主要還是發生在職工繼續教育與崗前培訓,而不是正規的學校教育。
(三)學習“能力本位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簡稱CBE)的思想和實踐最初產生于美國,日后為我們熟知則是通過加拿大有關方面的引薦。1989-1996年,加拿大國際開發署(CIDA)資助設立了“中加高中后職業技術教育項目”,作為這個項目的延伸活動,“中加高中后職業技術教育課程設計研討班”于1991年在成都舉辦,加方派出三位專家前來介紹課程開發的“DACUM”方法,引起參加者的極大興趣,接下來便有“中國赴加拿大CBE專家考察組”造訪該國,實地了解CBE/DACUM的運行情況。考察組撰寫的《CBE理論與實踐》印制于1993年,在此前后,又不斷地有中方人員到加拿大作為期三周至半年不等的訪問或業務進修,加方來華講學和交流的專家也絡繹不絕。盡管如此,國內按照DACUM方法進行的課程開發卻鮮有成功的案例,通常試點學校的“教學內容還不敢完全局限在較窄(針對性很強)的范圍內,仍較看重理論基礎課程,存在較大程度的學科模式的影響”。[3]
(四)“拿來”之后的反響
“在改革開放后,職業教育對于國外先進理論與模式的引進不僅動手較早,而且就其深度和廣度而言,在我國整個教育領域都是很突出的”[4],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些前所未見的新事物無疑會給職業學校的課程建設帶來新的變化。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雙元制”、“MES”還是“CBE”,都面臨著如何與國情相適應的問題,各種試點工作也因此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困惑。一些在別國行之有效的做法由于“水土不服”而終究難以實施,就像“雙元制”,它的“核心階梯課程”似乎從未在中國生根,這便使得相關引進項目結束之后,留給大眾的只有一個校企合作、半工半讀的不甚清晰的印象,或者至多是加強了職教課程需要突出實訓的信仰。可是,對于“模塊式技能培訓”和“能力本位教育”的試點來說,雖然它們有的并非針對學校,有的則已被證明是“知易行難”,兩者在研究領域引起的回響卻是怎么也不能忽視的,許許多多的職業教育課程工作者就是從這里看到了變革的希望。
二、從“模塊課程”到“課程模塊化”
在我國,職業教育課程的改革往往局限于學校教學計劃的調整,其中以不變應萬變的則是那種“先基礎、后專業、再實踐”的課程分段排列(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說的“三段式”),如此機械的課程方案與MES“積木組合式”的教學一經比較,后者具有的針對性、靈活性的特色便立即凸顯出來。于是,至遲到90年代中前期,“模塊式技能培訓”中的“模塊”(module)已經迅速成為研究者熱衷使用的詞匯,影響所及甚或超越了職業教育的范圍。然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模塊”的概念在這眾多的論述中不免出現了泛化、引申,直至按照主觀需求加以重新闡釋的傾向。
本來,“模塊”一詞是從建筑、家具、計算機等行業借用來的,其涵義包括三個方面,即:首先,它是一個部件、組件,其大小介于整體與零件之間,是整體的基本組成部分,離開了整體,模塊也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其次,每一個模塊本身是獨立的,可以將其進行不同的組合;最后,每一個模塊都是標準化的,有嚴格的指標要求,否則就無法對模塊進行不同組合。[5]而在MES當中,模塊是指在某一職業領域的工作范圍內,將一項工作劃分為符合實際工作的程序和工作規范,且有清楚的開頭和結尾的若干部分,這樣劃分出來的每一部分即為一個模塊。②由此進一步組合而來的“模塊課程”,必然是一種與長周期的學科課程相比規模較小的、內部相對獨立的單元課程,每一個模塊都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且評價高低只與完成特定的學習或工作任務有關。
那么,對于國內的課程研究者來說,他們是否普遍遵循著這些嚴格的界定呢?不是的!翻檢當年甚至直到今天探討“模塊課程”的相關論著,不難看出,其中突出的多半只是那種能夠自由拆卸、組合的涵義,也就是注意到了“模塊”類似于“積木”的比喻意義,至于什么樣的課程設計可以構成一塊“積木”則往往加入了些“實用主義”的解讀。譬如說,有研究者主張“將職業群中的每一種職業設計為一個大模塊……使學生能根據自己的特長和興趣,選擇相應模塊,以進入更適合自己的職業崗位”[6];還有許多學校把原來的課程重新歸類,冠以一個模塊的名稱,如“公共課模塊”、“技能實習模塊”等。[5]但這樣一來,其中的“模塊”就不再是小于傳統的“一門課”而大致相當于一個課程組成單元的格局③,轉而成了為滿足某方面的教學需要而包含多門課程的一種上位結構。
既然“模塊”的外延可以如愿伸展,那么它的內涵又何嘗不能變得更豐富些呢?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時學者一談到“科學技術加速向前發展”,“社會工作崗位的內涵不斷發生變化”,便一定要將“技術、環境、外語學習、外國文化、企業管理、創業教育、創新教育、休閑等”一股腦地納入“課程內容的模塊化結構”當中,以便能夠“及時刪減陳舊重復的內容,保持課程的最佳適用性”[7]。此時,這種“模塊化”(modularization)也再不是純粹的“模塊”概念的詞形變化,而頗可稱為一種“理念”了。大體上說,它所追求的就是將完成特定職業教育的必要內容按照某一標準(不排除是基于過去劃分學科的標準)進行分割,并使各部分能夠靈活組合,或者再加上課程實施中的“學分制”,等等,從而,“當新內容加入時,只不過是增加了一個課程模塊,而不會對職業教育課程的整體產生重大影響”[7]。
到了這一步,看似新鮮的“模塊”一詞其實已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于原先的認識。而一旦上述“課程模塊化”的闡釋傳播開來,國外模式帶來的沖擊就會基本限制在關于我們熟悉的各類課程,如文化課程與專業課程,或是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學時多少的爭論上面,職業學校常見的改革則不外乎是課程門類與課時數量上的增減,而非按照工作的要求重新選擇與組織課程內容。在這里,真正令人驚詫的反倒是這樣的研究與探索為什么還要偏偏、且一如既往地使用外來的“模塊(化)”的稱謂,而不是換作人們更容易理解的,諸如課程“靈活化”、“多樣化”,乃至“個性化”,等等?由上觀之,個中緣由或許還是“模塊化”本身(無論其怎樣理解)已被認為是一種先進的理念了,人們普遍意識到我國以往的職業教育課程需要做些改變,而國外的經驗當中大約會有值得借鑒的東西——這種心態也恰恰是取得進步的前提,只不過任何新事物剛開始時總歸難以看得透徹。
三、“能力本位”與能力觀的嬗變
類似的境遇也發生在“能力本位”深入人心的過程之中。起初,在中國與加拿大職教合作項目開展之時,其中的“能力”有著非常明確的意思表達,即:“這里所說的能力是由知識、技能,以及根據標準有效地從事某項工作或職業的能力所組成的”,“這種能力常常被稱為專項能力(task),可視為完成一項工作有關的可觀察到并可度量的活動或行為”。[8]如此頗顯狹隘的“行為主義”的界定與國內教育學動輒談論的“綜合技術教育”、“人的全面發展”立刻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然而,上述加方的意見卻也不是“能力”概念的唯一正解。即使同在北美地區,在能力本位運動波及到的一些培養專業性人才的教育領域中(例如培養工商行政管理人才的工商管理學院),人們的能力觀也顯然與之不同④,更不用說世界上還有深受“理性主義”哲學與“格式塔”心理學浸潤的德國職業教育。有學者曾將各國形形色色的能力觀歸納為三種,即“任務本位或行為導向的能力觀”(以CBE/DACUM為代表)、“整體主義或一般素質導向的能力觀”(如德國職業教育非常強調的“關鍵能力”),以及“將一般素質與具體情境聯系起來的整合的能力觀”(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能力本位”中有所體現)。[9]作為一種理論上探討,中國的職業教育專家自可以在各種有關“能力”的表達當中得到啟示。
接下來若干年的發展應當就是“能力本位”的中國化。鑒于人們已經意識到CBE/DACUM只是能力本位的一種體現形式,不能代表能力本位教育的全部,其中的行為主義傾向也就逐漸地被“揚棄”了。研究者或者用一種囊括“一般能力、群集職業能力和崗位職業能力”的“綜合職業能力”取而代之[10],或者進一步將職業能力的形成引申到“以職業技能為重點的全面素質教育或素質培養”[11]這樣的命題中來。盡管“能力本位”通常并沒有被“人格本位”、“素質本位”等更晚出現的概念完全壓倒,但是圍繞著“能力”的討論最終仍然倒向了“具有熟練的職業技能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12],以至要“樹立以全面素質為基礎、以能力為本位的新觀念”,培養“在生產、服務、技術和管理第一線工作的,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高素質勞動者和中初級專門人才”[13],等等,職業教育的目的于是回歸了傳統。
當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職教界談論的“能力本位”,大多還是作為“知識本位”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就像“模塊化”曾經作為“學科化”的對立面一樣。可是既然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需要具有全面素質,特別是適應不斷變換和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所需要的能力,那么教學工作的重點也就必然包括“與純粹的、專門的職業技能和知識無直接關系,或者說是超越某一具體職業技能和知識范疇的能力”[14],必然要“更加注重提高文化程度以增強發展后勁以及繼續學習能力、注重創造性等個性發展素養的培養”[15]。學科化的系統知識盡管不切實用,卻被認為是于此大有裨益,其結果是,“(90年代)那次轟轟烈烈的課程改革似乎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傳統的學科知識在課程中的核心地位堅固如初”[16]……
何以如此?為什么在外來思想如此強烈的沖擊之下,先前的課程方案仍能找到足以(或者經過些許微調后)繼續存在的空間?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四、小結:外來經驗的真正影響
多年以來,課程始終是職業教育微觀研究領域的核心,國際比較則始終是一種主流的研究方法。不過對于國內大多數的課程工作者而言,國外職教課程到底如何或許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限的介紹并不能給他們帶來感性直觀(在大規模的出國考察與網絡等新興傳媒推廣之前更是如此),至為關鍵的影響事實上來自一些翻譯過來的資料留給大家的印象。換句話說,人們學到的事實上只是人們能夠理解或者愿意這樣理解的外國模式。
哪些內容易于留下深刻的印象呢?首要的一點自然是契合當時的改革需求,否則,便無法激起廣泛的共鳴。而另外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引進的課程模式一定還要有極易識別的獨特之處——也就是不僅要迥異于原先的“常模”,且能夠將其特點用最簡潔的詞匯加以概括——就像“模塊化”與“能力本位”。至于早期“雙元制”的引入何以缺乏真正的回響(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甚至還有官方研究機構的理論配合),或許我們還應考慮到“雙元制”一詞本身所揭示的含義,無論工學結合還是加強實習實訓,在國內似乎都是“久已有之”了,多少顯得不夠“新鮮”。
在20世紀80-90年代,一些職業教育工作者已經親身感受到了傳統課程的缺陷,包括過于整齊劃一的課程編排,還有就是通常比照普通教育的學業評價,而更進一步,則前者大抵源自嚴格遵循學科教學,后者又往往被歸結到“知識本位”。只要認識到了這一點,關于職業教育課程新的組織形式與課程改革新的目標取向便已然呼之欲出,高調引進的“模塊化”與“能力本位”恰于此時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印象深刻并不一定意味著能夠“保真”。在某一時期內,介紹國外經驗的資料越多,表述越清晰、越翔實,相關的概念越是能夠保持原義,越少“曲解”的可能。反之,則經常會造成新名詞定義的含混。顯然,“模塊化”與“能力本位”這兩個概念正是在其廣泛傳播的過程中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轉變,以至當形形色色的“(跨)學科模塊”,以及“從事任何職業都需要的能力”這類用詞在當年的研究中一再出現時,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仿佛回到了原點,本應是與傳統格格不入的觀念仿佛更加強了原有模式的合理性。那么,是不是由于“路徑依賴”的緣故,任何職教改革起初都要向我們習以為常的課程靠攏方才合乎國情、方能取得實效?隨著中外交流的深入,其后的課程改革又將朝著何種方向發展?這些疑問仍需進一步的總結、梳理方能解答。
注釋:
①嚴格地說,這幾種所謂“模式”并排起來是有些問題的。因為“雙元制”實為一種校企合作的職業教育體制,“CBE”是以能力為基礎的教育指導思想和教育模式,“MES”則是一種具體的課程方案,彼此絕非同一層次的概括。不過在早些時候,言必稱三者并行大概已經約定成俗,職教界的專家大多也沒有什么異議。
②另外,CBE課程的教學單元也是模塊的典型表現形式,它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例如在幾周而不是幾個月內)完成。
③在英語國家的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出現了所謂“模塊課程”(module curriculum),不過這中間的“模塊”仍是構成某門傳統課程的學習單元,如“計算機”課程可以由“信息系統基礎”、“文字處理”、“計算機制圖”等模塊構成,而像“文字處理”這樣的模塊,也完全可以是“商務”、“語言交際”,甚至是“工藝美術”課程的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普通高中進行的課程改革也推出了類似的模塊。
④這里流行的觀念認為,能力不能等同于操作行為,能力是看不見的個體的內在素質(personal qualities or attributes),作為個體內在素質的能力,它具有整體性,雖然它也可分解為若干要素,但是作為整體性的素質結構的功能遠大于各能力要素的總和。
[1]徐涵.我國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發展歷程與典型模式評價[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8(33):52.
[2]周遠翔.MES在中國大有可為[J].職業教育研究,1995(1):35.
[3]黃克孝等.職業和技術教育課程概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13.
[4]俞啟定,張宇.異軍突起的職業教育[A].顧明遠等.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紀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9.
[5]劉重慶,徐國慶.關于模塊課程的誤解與澄清[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1(2):27.
[6]蔣乃平.集群式模塊課程的理論探索[J].教育與職業,1994(11):9.
[7]劉春生,徐長發.職業教育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159-160.
[8]中國CBE專家考察組.CBE理論與實踐(中加高中后職業技術教育合作項目出版物)[Z].1993:19.
[9]石偉平.比較職業技術教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98-301.
[10]譚移民,錢景舫.綜合職業能力的課程觀[J].職業技術教育,2000(28):9.
[11]解延年.素質本位職業教育——我國職業教育走向21世紀的戰略抉擇[J].天津市教科院學報,1998(2):49.
[1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Z].1999.
[13]教育部.關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深化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意見[Z].2000.
[14]徐國慶,雷正光.德國職業教育能力開發的教育理念研究[A].姜大源等.當代德國職業教育主流教學思想研究——理論、實踐與創新[C].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97.
[15]黃克孝.正確處理職教課程改革中的職業性與時代性特征的關系[J].職教通訊,1998(8):7.
[16]徐國慶.從工作組織到課程組織:職業教育課程設計的組織觀[J].教育科學,2008(6):37.
About the Initial Im pression of Foreig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 w ith Its Influence
Zhang Yu
(School of Marxism,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During the year1980s to 1990s,a seriesofgreatchanges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vocationaleducation courses.Undoubtedly,all these changes related to foreign courses,especially to the concept of“modularization”and“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While assuch Chinese investigation deepened,neither“modularization”nor“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ould keep its initialmeaning.It’sno longer the case thatvocationaleducation courses in Chinawere justone copy from outside.
vocationaleducation;course;module;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張宇,男,副教授,管理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后出站,主要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
G710
A
1674-7747(2011)11-0001-05
[責任編輯 曹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