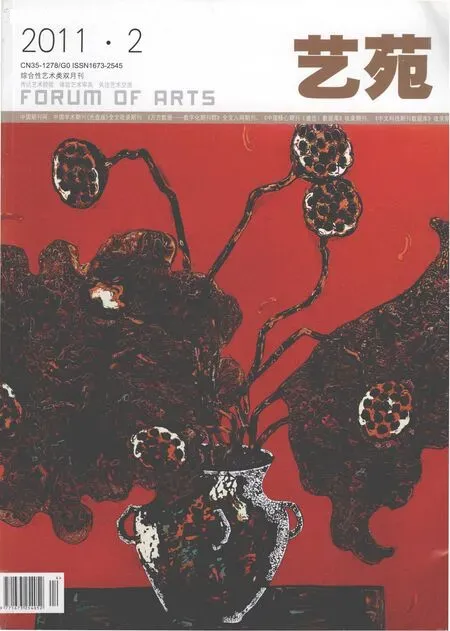古齊國樹木紋瓦當探析
文/葛 濤

圖1 樹木雙獸紋

圖2 樹木單人單獸紋
瓦當是中國古代建筑上的一種構件,是俗稱“茅頭”的建筑材料。它的質地一般為泥質灰陶,個別由磚石雕刻而成,采用鑄鐵、銅、抹金、琉璃等做的瓦當亦有發現。它主要起到保護屋檐椽頭免遭風雨侵蝕,延長建筑物壽命的作用。其始用于西周中晚期,多用于東周時期。除眾多的素面瓦當外,它還逐步發展為花紋及文字瓦當,其形制也由半瓦當發展為圓形瓦當,是實用和藝術的有機統一,也是今人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信息載體。
瓦當可分為秦瓦當、洛陽瓦當和齊瓦當等幾大類型。各地的瓦當紋樣,各有其特色。齊瓦當是指帶有齊國文化色彩的瓦當,包括以齊國故都臨淄為主要集散地的瓦當及受其文化影響的周邊地區所發現的瓦當,其范圍涵蓋今山東境內的廣大地區。東周時期,正值封建社會初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確立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列國日趨繁榮,城市規模日益擴大。其中諸侯國之中的齊國藉工商之流通,漁鹽之獲利,逐步興盛發展成為東方大國,其國都臨淄,是當時人口眾多,工商密集的大城市。《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踏鞠者。臨淄之涂,車轂擊,人肩摩,……。”經濟之強盛、文化之繁榮,造就了齊國建筑藝術的多樣性,這是瓦當裝飾藝術興起的時代。
齊瓦當,無論是從外形、紋飾,還是從題材內容,都與同時代以各式云紋為特色的洛陽半瓦當和以單一動物為題材的秦圓瓦當有著明顯的不同。齊瓦當以務美、開放、創新的齊文化為基礎,自始至終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它經歷了由素面無紋飾到手工刻繪,再到模具制作的整個發展過程。在紋飾特征上,齊瓦當以樹木為母體,以對稱為主要形式,在樹的兩側飾以人、鳥、獸及抽象紋飾和各種活動場面等圖像,從而構成齊瓦當獨特的藝術特色。齊瓦當的圖案、紋飾,雖然內容樸實,但卻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信仰及圖騰崇拜,極具裝飾性和藝術性,方寸之間融入了豐富的社會觀念和審美思想意識,成為探討古代社會的珍貴資料。[1](P263)

圖3 樹木乳丁紋

圖4 變形樹木紋(也有稱之卷云乳丁紋)

圖5 三角冢土社木紋
一、古齊國樹木紋瓦當的類型
齊瓦當分為半圓瓦當和圓瓦當。對于這兩種瓦當的演變關系,李發林先生在《齊故城瓦當》(文物出版社,1990年)中有過分析,他認為臨淄瓦當的演變有兩個方面,一是半圓形瓦當向圓形瓦當的演變;二是半圓形瓦當和圓形瓦當各自紋樣的演變;在兩種瓦當演變的形制中,齊瓦當最大的特點是圖案式生活畫,多以樹木紋為中心進行布局, 樹木紋數量最多,變化豐富,成為齊半瓦當最基本的構圖特征和特點。李發林《齊故城瓦當》一書收集到的臨淄一地所出半瓦當上的樹木紋,即有119例;圓瓦當出現后,合兩個半瓦當的樹木紋為一器的,又有13例。這些大多是采集所得,內容已是如此豐富,齊瓦當樹木紋的盛行與形式的復雜多變,于此也就可見一斑了。
李發林根據其反映的內容將花紋瓦當分為圖案畫、生活畫、圖案式生活畫和神話畫四類[2](P186)。申云艷博士把樹木紋瓦當分為樹、人、鳥獸組合類、樹木獸面組合類、樹木紋類三種形式。本文主要研究樹木紋的形式特征,結合以上兩種分類把樹木紋瓦當分為樹木寫實生活畫類、樹木抽象畫類、變形樹木紋類三大類。
1.樹木寫實生活畫
這類題材的瓦當在臨淄故城是最多的,其中又以半瓦當居多。當面多用寫實手法描繪出社會或自然現實生活的畫面,以現實生活中與人們關系密切的動物、人物為主要形象,這無疑與齊國農業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安適密不可分。圖案均以樹木為母題紋樣,樹木兩旁配以飛禽走獸或騎馬的獵人。常見的有樹木單人單獸、樹木雙獸(圖1)、樹木單人多獸(圖2)、樹木雙馬、樹木雙騎、樹木雙鳥、樹木晰蝎、樹木單人單鳥等。它們均以樹木置于中軸線上,兩邊置以人物、鳥獸,顯得清新活潑。這些紋飾是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其構圖講究對稱,形象生動逼真,充滿了人世間的生活氣息,也展現了自然界的美好景色,是齊瓦當的最大特色所在。
2.樹木與抽象畫
這類題材的瓦當采用抽象的圖案方式來反映社會現實的生活畫面。以在臨淄故城所出瓦當所占比例最大,也最具特色。其紋飾絕大部分還是以樹紋為主體,當面中部飾一樹木紋,但樹木日趨簡化抽象,部分枝條己演變成曲線紋或三角紋的樣式,其周圍多飾以抽象的符號或云紋、乳釘紋、太陽紋、三角紋、箭頭紋等。其中多為常見的有樹木卷云紋、樹木乳丁紋(圖3)、樹木箭頭紋。其中“樹木乳丁紋”瓦當也是學術界為其定名而爭議不休的話題。有人提出“樹木乳丁紋”瓦當是“以樹木乳丁為題材寫意獸面的典型特征”。近年來亦有學者命其為“樹木饕餮紋”瓦當,言其“留著周代饕餮紋的余影”,“這種紋飾與饕餮紋之間有著某種關系”。[3](P729)
3.變形樹木紋
除具象寫實的樹木紋瓦當外,根據申云艷博士的考證,東周齊國還出土一種變形樹木紋瓦當(圖4),它的當面中間一般飾以單線構成的曲線紋等紋飾,組成各類卷云、鉤云紋變形樹木紋,云紋間常配飾有乳釘紋、羊角紋、箭頭紋、樹紋、圓圈紋、連弧紋等輔助圖案。它有半瓦當、圓瓦當兩種類型,當面畫面整體簡潔、抽象。也有文獻稱之為“卷云乳丁紋”。
二、古齊國樹木紋瓦當的造型藝術
齊瓦當紋飾想象豐富,靈活多變,而樹木紋幾乎是東周齊國瓦當的標志物,多數的半圓形瓦當的構圖特點是以樹木為中心進行紋飾布局的。它們通常以半圓瓦當的平邊作為基線,在正中的部位立一直線作為樹干,樹冠的造型有主格形、菱形、傘形等多種。樹枝枝枝向上斜出作左右對稱排列,有的枝上有葉,作短直線或變化為三角形;有的干脆簡化成符號狀和抽象形,將樹兩邊的下枝向下卷曲;有的則簡化為左右各兩枝,作噴泉狀下垂,枝端保留一片矢鏃狀的樹葉。[4]
樹根或有或無,有根的也多變化,有的如象形的木、禾等字的根,分用三歧或作須狀,或簡化為實心的正三角、倒三角、半圓,以及其他簡單的幾何形體。這種基本格式的樹木紋可以獨立存在于瓦當之上,但也經常以此為骨架,左右對稱地排列其他造型,或相向對稱、相背對稱、相互對稱,或上下對稱、兩朵一對、三朵一組,或高或底,等等不一。
齊瓦當當面以線造型,多運用傳統的對稱格式,紋飾的結構、布局、圖案具有多種變體和配置組合方式。樹木紋造型題材取自自然景物,但用抽象寫意方式來展現。紋飾在疏與密、線與面的布局上協調流暢、平衡統一、洗練明快,在厚重、古樸、雄健中求活潑、輕盈、優美,充分發揮了線條藝術的表現力。題材所反映的內容既有現實生活也有神話傳說,抽象與具體并存,形成豐富多彩的造型藝術風格,有時在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當中又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三、齊國瓦當紋飾的樹木崇拜
從齊瓦當的造型特點來看,其紋飾構圖的組合關系躍然目前。無論是半瓦當還是后期的圓瓦當一般都把“樹木紋”看作基本的紋飾“母題”,亦可稱為“主飾”,其他的人與動物及乳丁、卷云、太陽紋等大都作為配飾出現。這證明了生命之樹在齊地受到了極高的尊崇,齊人對樹具有特殊的感情,因而才不厭其煩地反復加以描寫。然而它們又不像是出于純粹的藝術觀賞動機,因為樹木僅僅略筆示意,并未著意加以刻劃,估計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也許人們認為具有神圣性質的樹木,進行崇祀可以使他們受到它的福佑。如圖(圖5)在瓦當樹木紋的根部或周圍,往往有或三角或半圓或四方諸形狀的符號,它們明顯不是樹根,似乎更像是一堆堆“冢土”,也即一座座非常神秘的祭壇,這些祭壇是古代齊國各種各樣的“社”。[5]
劉向《五經通義》說:“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社是原始的土地神,稷為谷物之神。其所在有用石與用樹兩種表現方式。在齊地,祭社活動可能起源更早,距今約六千年的大漢口文化時期的大型陶尊器上,即已發現大墳口人對地母的崇拜,具有“吐生”、“任成”或“化育萬物”之意[6](P9)。
在以農為本的古代齊國,土地神和谷神是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祭社即祭祀土地,報答土地給人類的恩賜。《墨子·明鬼》說:“燕之有祖澤,當齊之有社櫻、宋之桑林、楚之云夢也……。”齊國的社樹在古代記載中,也有相當具體的描寫。《莊子·人間世》便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記載,他說齊國曲轅地方有株櫟社樹,“其大蔽千牛,契之面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為舟者傍十數”,但外出物色樹材的匠師,經過其旁卻不屑一顧,使他的弟子深感詫異,后來匠師告訴他,這是“不材之木”,為舟、為棺、為器、為門戶,都“無所可用”,因此不必考慮。《莊子》之文多寓言,對于古代的神祗、靈怪、各種崇拜對象、祭祀用牲,舉凡帶有神圣性質的事物都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態度,極盡揶揄之能事。他對于齊國的櫟社樹,表面是貶抑,實際上卻是贊揚幸虧它大而無用,因此才能全其天年。齊地崇祀社木,《說苑·奉使》篇中也有蹤跡可尋:齊國郊區有大梧樹,是數百以至上千年的大樹,估計也是社樹,所以才得以保存下來。實際上,櫟樹是山東極為普通而又非常有用的社樹,多被視為神木,得到認真的保護。齊統治者對林木保護也有明確的規定:《管子》卷五《八觀篇》說:“山林雖廣,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管子·五行篇》說:“出國衡慎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晏子春秋》卷二內篇諫下說:“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從齊國的國君到民眾上下,足可以看出樹木在古齊國的重要性,而于社中植以何種樹木,也是有講究的,“太社以松、東社以柏、南社以梓、北社以槐”(《白虎通義·社櫻》)。當面樹木紋底部不同形狀的圖案代表古齊國不同的“冢土”和“社壇”。而冢土上不同的樹木紋樣式則代表不同種類的社樹與不同的社神。
齊瓦當收藏家王也先生也曾提出的“樹神說”,即“樹木為古齊地之圖騰,從大量的出土文物證明,樹木紋,即不含乳丁的樹木紋裝飾曾被廣泛的應用于齊國民眾日常生活的各種用具之中,包括陶盂之上。其手法從模范到刻劃,都可見到樹木的影子。另外,有一種瓦當圖案中,樹木生長在云紋環繞的仙人頭上,反映當時人們對樹木的圖騰崇拜的一些痕跡,更形象地揭示了樹木崇拜在齊地之盛。因此“樹神說”應該也是可以自成一說的。總而言之,樹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成為原始人類的植物圖騰而受到崇拜,這是具有普遍性的”[7](P11),“也是發展為‘社中植以木’的根本原因。在這種觀念意識性的基礎上,巨大的力量在主宰和左右著瓦當藝人的造型意識,對于人們的行為就具有相當微妙而深刻的重要性,我們就不難看出樹木紋作為母題在瓦當上反復出現原本就是導源于人們對于圖騰生命之樹一一社木(即社神)的虔誠崇拜,作為瓦當主紋在齊人心目中的占有重要位置,是具有祈生降福、保國佑民、社翟長存等多重寓意的吉樣紋飾。”[8](P17)由此,用它來裝點堂廡,增加建筑的宗教色彩,是再合適不過了的。
[1]宣兆琦,李金海.齊文化通論(上)[M].北京:新華出版,2000.
[2]李發林.齊故城瓦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傅嘉儀.中國瓦當藝術(下冊)·齊故城篇[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4]董雪,李娜.試論臨淄齊瓦當的裝飾藝術[J]. 管子學刊,2009(1).
[5]安立華.齊國瓦當賞析[J].故宮文物(月刊),總第144期.
[6]王樹明.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G]//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發行,1986.
[7](美)O·V·魏勒.性崇拜[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1988.
[8]安立華.齊國瓦當藝術[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