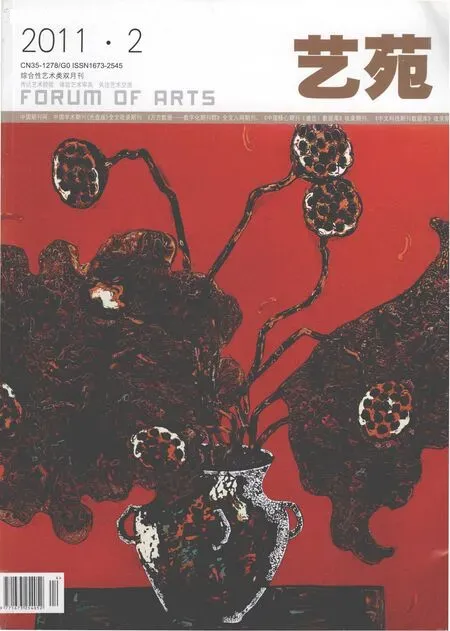略談戲曲民俗研究的成就與學科意義
文/王學鋒
中國戲曲與民俗之關系是在20世紀的中國戲曲研究中越來越凸顯的一個論域。隨著認識方式的日益轉精、文獻檢索手段的不斷強化,戲曲與民俗的互動研究在今天逐漸顯示了較為強勁的學術生長能力。如果說一個學科的成立需要具備較為固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需要一批較為專門的研究機構和研究隊伍的話,那么“戲曲民俗學”已經歷史地、自然地具備了這些條件,并在為促進中國戲曲研究的發展積極貢獻著獨特的學術資源和研究成果了。但今天,筆者在這里提出“戲曲民俗學”的學科建立主張,并非“事后諸葛亮”式地作一些多余的概括,而是希望適時總結以往的研究成果,深化我們的認識,并組建“自己的園地”,集中探討“戲曲民俗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以期為未來有意識、有計劃、有理論地進行“戲曲民俗研究”打下良好基礎,從而積極開掘中國戲曲研究的深層學術意義。
一、20世紀戲曲民俗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1949年之前
自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開創戲曲的現代性研究之始,其中國戲曲“自巫、優二者出”的說法就顯示了從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戲曲的視野,這一點在后來的戲曲起源或發生研究方面都不斷地激發新的思考。鑒于中國現代戲曲研究的初創,研究者大都“異想天開”,很少受到固定、單一模式的戲曲史觀的影響,由此很多研究成果其實蘊涵了多向的研究可能,如許地山的《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聞一多對“《九歌》是巫歌”的研究,孫楷第、顧頡剛、孫作云對傀儡戲、影戲的研究都在一個民俗文化的視野下更寬廣地關注著中國戲曲的起源、形成、形態等各個方面,這些被其后的戲曲史研究逐漸漠視、甚至排除的成果在今天也同樣受到了戲曲民俗研究者的重新審視和借鑒。
“粗陋”、“小道”的民間戲曲在“五四”之后知識分子向下看的“民間情結”中被“發現”了。1918年《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宣告開展的現代民俗學運動為戲曲研究引入了“民俗”視角,雖然這一視角還不免帶有知識分子對“民間”的浪漫想象,但其影響無疑是深遠的。20世紀30年代的李景漢的《定縣秧歌選》關注到了以前被遮蔽的民眾的戲曲、娛樂、生活與想象,這一編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民俗學界回顧自身傳統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我們還可以在周作人的《中國戲劇問題的三條路》一文中看到現在非常熟悉的戲曲民俗研究觀:“依照田家的習慣,演劇不僅是娛樂,還是一種禮節,每年生活上的特點。”[1]這是令人驚訝的。20世紀的中國“俗文學”研究自胡適《白話文學史》之后,于1938年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的出版獲得了廣泛影響。鄭振鐸的“俗文學”定位是包括戲曲在內的,雖然沒有在其《中國俗文學史》中專門論述,但開辟了戲曲作為“俗文學”的研究新視野,大量的戲曲等“俗文學”文獻在這一視野之下得到了收集,在與敦煌變文、寶卷、彈詞、鼓詞、民歌俗曲、諸宮調等相類的“俗文學”文類的比照中,也啟發著研究者重新認識“戲曲”在民俗文化氛圍中與其他演藝形態的共生性。在對俗文藝的研究方面,李家瑞在1931年出版的《北平俗曲略》對說唱鼓書、快書、蹦蹦戲、傀儡戲、湖廣調、福建調、馬頭調、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兒歌、秧歌等大量民間說唱文藝的研究奠定了與戲曲相類的俗文藝研究的基礎。在今天看來,《北平俗曲略》將戲曲民俗研究從戲曲研究擴展到對戲劇形態研究的關照下,其價值無疑是很大的。
在戲曲習俗研究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齊如山的京劇研究可謂頗具代表性。齊如山出版于1935年的《戲班》,分“財東”、“人員”、“規矩”、“信仰”、“款項”、“對外”等方面對京劇戲班習俗作了詳細考察和探討,這一對京劇所作的“外部”研究對僅僅眷顧于簡單的京劇“藝術”的“內部”研究是一個啟發。齊如山“對于現代社會中的文化、風俗、習慣、人情,以至婚喪、慶吊、酬應、來往、買賣、工藝、技術、娛樂、游藝、飲食、游逛等等,都極感興趣,悉心研究”[2](P4),“訪問過國劇的老腳名宿達三四千人”[2](P5),在今天看來,這些方式無疑是頗具抱負的民俗“田野考察”工作。
20世紀4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戲劇簡史》的作者董每戡被認為是“國內最早把民俗學、人類學和戲劇學結合起來研究的著名學者”,在他的戲劇史著作中,確實最早專門性地對戲曲的起源、形成作了民俗學、人類學式的考察和描述。而同樣撰寫于40年代的周貽白的《中國戲劇史》在“系統地吸收了自清末王國維以來到40年代末的學術成果”之后,也在戲曲的起源觀上強調了儺儀、儺舞等“來自民間”的觀念。
(二)1949年之后
20世紀前半葉的戲曲民俗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所開拓,隨著時間的流轉和學術的積累,漸漸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傳統”。1949年之后,歷史唯物主義的戲曲研究范式逐漸成為新的學術潮流,但由于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和介入,戲曲研究范式變得單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戲曲研究范式逐漸非學術化,加之話劇研究思維、成熟的戲曲觀以及歷史研究中的線性發展觀,戲曲民俗研究的領域逐漸縮小,戲曲與民俗關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戲曲俗語方言的考釋,并形成了一個傳統。幾十年間相繼出版了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1953年)、徐嘉瑞的《金元戲曲方言考》(1956年)、陸澹安的《戲曲詞語匯釋》(1981年)、王鎂的《詩詞曲語辭例釋》(1986年)、方齡貴的《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2001年)、王學奇等的《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2002年)等著作,它們從語言學角度對戲曲文本中的俗文化因子作了專門而詳盡的考察,開拓了我們進行戲曲民俗研究的手段和視野。
不過,造就后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戲曲民俗研究的繁榮和成果斐然不是沒有原因的。1949年建國之初的戲曲民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從當時的文藝“采風”活動中獲得了生存空間,20世紀八、九十年代熱鬧的儺戲、儺文化研究在這一時期的儺舞調查中就埋下了伏筆。此外,劉念茲的戲曲文物研究、墨遺萍對鑼鼓雜戲的研究等也都為后來的戲曲民俗研究作出了貢獻。
以《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志》、《中國戲曲通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相繼出版為標志,中國戲曲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張庚先生的“史”、“志”、“論”的戲曲學架構為戲曲民俗學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國戲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戲曲通史》關于戲曲起源于民間歌舞的論述,內在地具有了戲曲與民俗之間密切關聯的理論空間,并在清代戲曲史部分,大量論述了以前戲曲史用力不多的“駁雜不純”的花部地方戲,但是這一戲曲史的架構,“在對戲劇發生的理解上,是以形式的歌舞表演為基點;而在對戲劇史的理解上,則是以內容的文學性為基點”。造成這樣的錯位一方面是時代的認識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田野資料的忽略和缺乏。隨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戲曲研究觀念的拓展和大量田野資料的發掘,對戲曲民俗研究的重視和認識的深化正可對此有所補充,而三十卷《中國戲曲志》中有關戲曲民俗資料的大量保存更是直接為戲曲民俗理論的探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些都可以使我們積極填充張庚先生開拓的理論空間。其實,張庚先生戲曲理論中的戲曲方志學、戲曲文物學思想以及對儺戲、目連戲研究的積極關注,已經緊密勾連了戲曲民俗研究的諸種方向,使得其戲曲研究具備了相當的開放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戲曲民俗研究的潮流之一就是學者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實地考查,其代表即是臺北清華大學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劃。這個研究計劃調查了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新加坡的眾多儀式演劇,研究結果由臺北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為“《民俗曲藝》叢書”八十種(包括調查報告、資料匯編、劇本或科儀本集、專書和研究論文集等)。這一研究計劃囊括了一時的精英,并匯集了大量曾經參與《中國戲曲志》編撰的各地文化部門的學者,將《中國戲曲志》對戲曲民俗的關注引向深入,在田野的“實驗場”上引發了學者們對戲曲與民俗關系乃至中國戲曲民俗文化的進一步思考。
近二十年來,由于對戲曲與民俗兩者的關系重要性的認識逐漸加深,戲曲民俗研究的成果較為豐富多樣,重要如:廖奔的《中國戲曲史》、《中國戲曲發展史》都“試圖從民俗文化的角度剖析中華戲曲,從而展示以往未曾涉及或者探之不深的研究領域”,將戲曲民俗研究積極納入中國戲曲史的總體敘述,雖不十分完滿,但卻作了十分有益的戲曲史整合和重構;劉文峰的《中國戲曲文化圖典》、《中國戲曲文化史》、《戲曲史志研究》在編輯《中國戲曲志》的多年學術積累基礎之上,積極關注戲曲民俗研究,并自覺嘗試著戲曲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努力;以曲六乙為代表的儺戲、儺文化研究,關注儺俗和戲曲民俗生態,出版了《中國儺文化通論》等;劉禎的《民間戲劇與戲劇史學論》,在戲曲文化學的框架下,大量引入戲曲民俗研究視角,他近期出版的《戲曲與民俗文化論》對戲曲與民俗的關系更有深入的思考;以黃竹三、馮俊杰為代表的研究者,以戲曲文物研究為對象,積極吸納戲曲民俗、宗教研究,出版了《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山西戲曲碑刻輯考》等專著;以康保成為代表的研究者,則從宗教、民俗角度關注中國戲劇形態問題;此外,鮑文鋒的《古代戲曲民俗與中國戲劇的淵源——中國藝術和審美意識發生的民俗思考之一》[3]、鄧翔云的《試論民俗文化與中國戲曲的發生》[4]、朱恒夫的《推進與制約:民俗與戲曲關系》[5]、鄭傳寅的《民俗文化與古典戲曲》[6]等都對戲曲與民俗的關系作了直接的探討。成果眾多,這里不一一盡述。
二、戲曲民俗學的對象、方法、意義與中國戲曲研究的發展
(一)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百戲雜陳”與戲曲研究觀念的轉變
中國戲曲民俗極為豐富[7],而現代戲曲學和民俗學分作兩途,在專業分工帶來精細的學術“耕作”之余,也遮蔽了對中國傳統戲曲真實生存狀況的客觀認識。如孫柏所說:“自新文化運動催生出現代戲劇意識之后,‘話劇’——或者說西方主義的戲劇觀念,在極大程度上主導了我們對戲劇文化的整體認識。實際上,綜觀古今中外,戲劇文化的極大豐富遠遠超過了這種建制性規范。由于戲劇學基本上是現代戲劇意識的直接產物,并且內在于現代戲劇文化的總體格局,所以它的課題范圍與治學理路,本身就是對那種建制性規范的實踐和體現。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對于前現代戲劇的許多認識就難免扭曲。”[8]孫柏在這里沒有將中國傳統戲曲與西方戲劇作簡單對比以顯示中國傳統戲曲如何獨具價值,而是將問題的討論引向現代性追求招致的“建制性規范”對戲劇學學科的“擠壓”。這一“規范”和“擠壓”無助于我們清醒地認識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甚至西方戲劇文化在“前現代”時期的豐富性,這一豐富性指的就是:“至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前交,中國和西方的戲劇文化在總體面貌和根本訴求上并沒有什么不同——它們都屬于百戲雜劇。”[8]這一看法并非不承認中西戲劇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但是,它更多地從戲劇形態的組織方式、原則、面貌方面強調了兩者的同構性。對戲劇形態的同構性的強調解放了我們對中西戲劇二元對立的認識的束縛,同時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反思和理解中國傳統戲曲文化中的“百戲雜劇”現象。當然,這一認識是建立在對現代戲劇學科的反思基礎之上的,但是,“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擯棄現代戲劇意識,因為只要其歷史條件沒有終結,它的存在就一定攜帶和履行著某種時代的訴求”[8],我們要做的只是反思反思再反思,力求在時代賦予我們的條件和限制基礎上努力達到時代的最高認識水平。
在中國戲曲形成前的漢代就有涵蓋音樂、舞蹈、雜技、幻術、武術、滑稽表演在內的樂舞雜技表演,可謂“百戲雜陳”。在中國戲曲于元代成熟之后,仍舊并不擅長像話劇那樣的敘事演出,常以“過錦”手法組織戲劇演出。而與成熟戲曲同時的民間戲曲,更為真切地體現了“百戲雜陳”的表演特色,如山西上黨地區發現的明代《禮節傳簿》中顯示的迎神賽社活動中駁雜狂歡的演出形態。歐陽予倩就認為中國戲曲是“雜戲”(1)和“混合”戲劇。中國戲曲中的這一“百戲雜陳”的特點正是在深厚的民俗氛圍中得到清晰的體現的。戲曲民俗學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了全新的價值,它不僅是對傳統的戲曲研究中忽略的部分作一種補遺,而且使我們具有了一種認識中國傳統戲曲的研究理念和視角。于是,中國傳統戲曲研究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方面都應該放在其生成、生存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來考察,
(二)跨學科研究
既然中國傳統戲曲在許多情形下呈現出一種“混合”狀態,那么,僅僅依靠單一的某個學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這里,戲曲學與民俗學的跨學科問題自然就產生了,這就是戲曲民俗學。戲曲民俗學建構的一個學科背景是,藝術學與民俗學的交叉研究越來越多地被實踐著,鐘敬文先生曾在《文藝研究中的藝術欣賞與民俗學方法——1997年10月6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慶祝〈文學評論〉刊行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9]及《民俗學對文藝學發展的作用》[10]等文中提倡從民俗學角度研究文藝學,以便多角度和深入地了解文藝現象。這方面重要的著作還有,陳建勤的《文藝民俗學導論》[11]、紀蘭慰的《舞蹈民俗學的藝術定位》[12]、張士閃的《藝術民俗學》[13]等。鑒于此,戲曲民俗學的提出也是適時的。戲曲學的研究范圍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戲曲學研究是指對戲曲文化以及戲曲藝術本體進行整體綜合研究的學科。廣義的戲曲學指凡是與戲曲有關的學問。”[14](P2)而民俗學是“研究民間風俗習慣的一門科學,它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論證探求它的本質結構、特點與社會功能,揭示其發生、發展、傳承、演變、消亡的規律。”[15](P6)作為交叉學科,我們自然希望民俗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能為戲曲的歷史與現狀提供新的解釋能力。我們關心與戲曲活動相關的民俗事象以及這些民俗事象如何影響戲曲本體的生成。這些與戲曲活動相關的民俗事象包括戲曲演出戲俗,比如演出中的祭臺、跳加官、打通、坐場等儀式,戲班的班規,演員的報酬、食宿,觀眾的看戲習俗等演出程序和演出禁忌;包括歲時節日民俗、人生禮儀民俗、宗教祭祀民俗等活動中的戲曲活動狀況;包括戲曲活動的社會組織民俗;包括戲曲演唱中的方言民俗;包括戲曲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等。我們還關心戲曲與民俗兩者的互動關系。
戲曲民俗學研究的重心應該是戲曲的藝術本體。雖然它是戲曲學與民俗學的交叉學科,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要廣泛借鑒民俗學、民族學與人類學,但是要格外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進行戲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戲曲本體以及戲曲發展史等戲曲自身的問題而不是要解決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或者是民俗學的問題。也許在實際的操作中學科的界限不一定涇渭分明,但是學者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定位還是應該相對準確地存在的。當然,這里需要注意,不必輕易地畫地為牢、束手束腳,過早地將自己局限于一個所謂的“學科范圍”內,保守著“學科范圍”,那是與跨學科方法本來追求的有效解決問題的開放性相背的。
(三)田野考察方法及反思
戲曲民俗學的代表性研究方法當然是田野考察。“田野”在中文里的意思可能會造成誤解,以為這一考察必定是要到孤野村落和窮鄉僻壤。其實,“田野考察”的英文單詞“fieldwork”中的“field”(田野)除了“田野”的意思外還有“場地”和“領域”的意思。我們知道,最初的田野考察興起于早期人類學家對“他者”的關注,這一“他者”的指稱背后是有西方社會的“先進”對“落后”的價值優越感在內的。此后,對這一中心情結的反思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促成了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將田野調查目光轉向了“本土”,直至“家鄉民俗學”更深入和動態地在“故鄉”和“他鄉”間關心調查對象的情感變遷和文化認同的轉移。由此,戲曲民俗學的田野考察對象就不僅僅是鄉村里的戲曲民俗活動,它還應該包括城市里的戲曲民俗活動。更進一步的意義上,戲曲民俗學強調走出文人書齋,到異己的戲曲文化環境中,尋求對話,以反思自己的戲曲認識方式。
田野考察在近二十年的《中國戲曲志》普查和儺戲研究中被大量使用,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在有些時候許多研究者也漠視了田野考察技術和理論的學習和認識,他們認為田野考察不需要任何理論的指導,不能先入為主。但任何人作田野考察都是有其“前理解”在內的,只不過能否自我意識罷了。田野考察應提倡具備“先入為主的問題”,即帶著問題進入考察地點,因此,問題不在于有沒有問題和理論,而在于具有怎樣的問題和理論。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的熱潮,各地“向下看”積極尋找民俗,但要把戲曲活動中的“歷史遺留物”從其生成、生存的民俗語境中抽離出來,戲曲民俗的田野考察一定要歷史化、地域化、語境化。
文獻研究作為傳統的研究方式,仍舊是戲曲民俗研究的有效手段,對田野考察的提倡不等于漠視傳統的文獻研究方式,兩者應該相互補充。把案頭文獻研究和田野考察對立起來看待的方式,其實是一種二元論的思維模式,比如在對劇本的研究中,如果跳出傳統的文學劇本的認識概念,注意到“口傳劇本、文字劇本與符號劇本,場上劇本與案頭劇本,關目本、穿關本與曲譜本,提綱本與綜合本”的這一“泛戲劇劇本”的多樣存在,那么在對這些劇本的考察中,就要兼備文獻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方法,從而進入到劇本生成和激活的民俗環境中。
(四)戲曲民俗學的未來工作與對中國戲曲研究的意義
由于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的問世、頻繁的學術會議的召開以及較多博碩士論文從戲曲民俗角度選題,戲曲民俗學的學科建構有了較為豐厚的學術積累和底蘊,未來的工作仍然可以從三方面加強:
1.資料積累。鑒于戲曲民俗活動的大量資料保存在地方志中,而《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編纂已逾十年,隨著戲曲民俗研究越來越具體和細化,做一份按省分卷的方志戲曲民俗資料的匯編顯得越來越有必要和價值。很多戲曲研究者仍習慣從《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尋找材料,而此書的編纂在當時主要依靠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大量的地方志資料還未涉及。據筆者所知,光是山西歷代各個版本地方志中的戲曲民俗資料就數量很大。
2.理論意識。由于戲曲民俗資料一方面散見于地方志,另一方面又是散落于民間的非文字的“口頭”資料,這些都增加了理論總結的難度。因此,如何借鑒外來的理論成果轉而在零星散漫的戲曲民俗資料中進行概括,既是難點,也是從“中國經驗”中建構自己的理論的機遇。
3.重寫戲曲史。這一想法不是為了挑戰和打倒某個權威,而是通過理論和方法的更新,吸收戲曲民俗學研究的成果,并內化為我們深刻認識中國戲曲發展史的手段和武器,為我們頭腦中那些難以理解的戲曲問題找到最佳答案。20世紀40年代以來,董每戡、周貽白乃至后來的張庚、廖奔的戲曲史都認真處理了戲曲與民俗的關系問題,以期成功整合進中國戲曲史,但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都留下了可探討的余地。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戲曲的發展遭遇了危機,作為進入藝術殿堂的、高雅的、純藝術欣賞性的、純娛樂性的戲曲演出日益減少,而作為民俗活動的廟會戲、集市戲在廣大農村如火如荼。這是集體所有制和民營劇團主要的演出市場,也是戲曲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土壤,戲曲民俗學學科的建立,順應了戲曲發展的這一新局面。戲曲研究應該保持與現實生活積極對話的能力,戲曲民俗學幫助我們重新聚焦對象,也促使我們反省自己的既有研究觀念和研究模式,通過努力,我們一定會做出一個理論研究者應有的貢獻。
注釋:
(1)載于《新青年》第5卷第4號,1918年10月15日。
[1]周作人.中國戲劇問題的三條路[M]//周作人.藝術與生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張其昀.代序[M]//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3]鮑文鋒.古代戲曲民俗與中國戲劇的淵源——中國藝術和審美意識發生的民俗思考之一[J].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3).
[4]鄧翔云.試論民俗文化與中國戲曲的發生[J].學術界,1997(4).
[5]朱恒夫.推進與制約:民俗與戲曲關系[J].藝術百家,1997(2).
[6]鄭傳寅.傳統文化與古典戲曲[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7]劉文峰.中國戲曲與民俗[J].戲友,1997(2、3).
[8]孫柏.清史泰西觀劇錄[J].戲劇,2004(3).
[9]鐘敬文.文藝研究中的藝術欣賞與民俗學方法——1997年10月6 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慶祝《文學評論》刊行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文學評論,1998(1).
[10]鐘敬文.民俗學對文藝學發展的作用.文藝研究,2001(1).
[11]陳建勤.文藝民俗學導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12]紀蘭慰.舞蹈民俗學的藝術定位[J].民族藝術,1998(2).
[13]張士閃.藝術民俗學[M].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
[14]朱文相.中國戲曲學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15]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