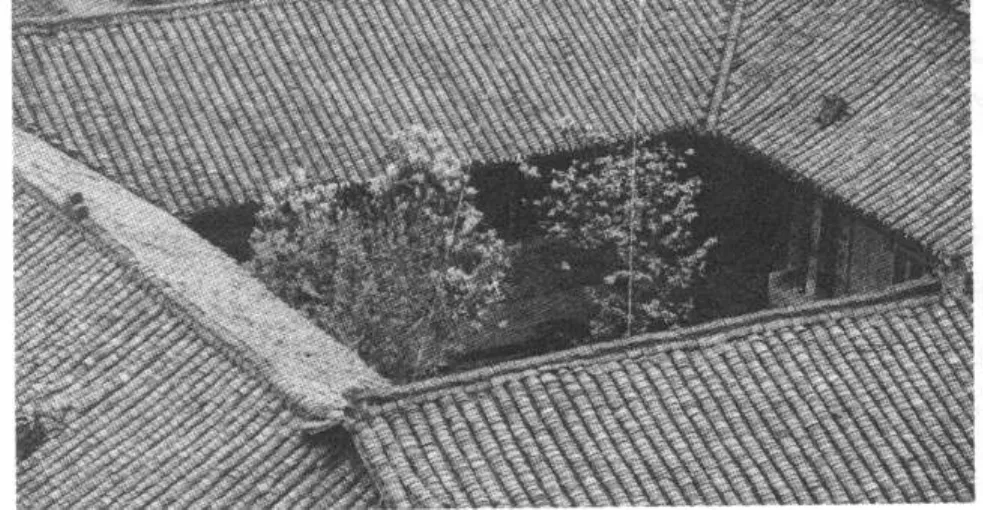紛亂
□許松濤
紛亂
□許松濤
A那個小姜,離開大院也有好幾年了吧。至今,我依然一直在懷念這個小伙子。當時他才十七八歲光景,八月里穿著一件灰白的單衣,正在門衛室忙來忙去,不亦樂乎地布置他的理想色彩很濃的小家。他考慮的不是沒有道理,批發了些醬油、味精、食鹽、肥皂和打火機之類的日雜商品,擺在簡陋得可憐的貨架上。這一切是他從這60戶人家的日用所需考慮的,按理也能多少為他掙點收入。可是這個院里,精打細算的主婦斤斤計較慣了,算計著過日子。久而久之,鮮貨變成了陳貨。小姜的貨賣不動。可能是小姜給人的感覺有殘疾,他的一雙眼睛總是朝天翻白眼,說話雖然入情入理,語速也快,口齒清爽,但有一個不好的面相,讓人們一見就心生恐懼,也許這相貌,把女人們給嚇跑了,雖然他很買力,很誠懇,但時代已經看不上這些。初來時工資微薄,他沒有任何要求。我每次下班回來,都看到他在揮舞著大掃帚清掃甬道,或蹲下單薄的身子細細拔地磚縫、場院上的雜草,尤其是盛夏季節,烈日下,他的薄背心汗濕了貼在背上,可見嶙峋的根根肋骨。小伙子的勤快感染了我,有時與朋友相聚剩了些酒、煙什么的,立即想到他,想著他也該多少嘗一嘗這些男人都喜歡的東西。我這樣做,也就一兩次。每次他接住時,臉都刷的一下紅了,有些羞澀,也有些激動,是被別人尊重的那種快樂。剛來時不愿談吐,人家也很少與他談吐,后來與我有些話說,話不多,人靦腆,心里是透亮的,能過事。冬天他上樓到各家各戶的門前清掃,用抹布擦樓梯扶手上的灰,手凍得裂開一條條血口子。我勸他別擦,擦也等天暖了再擦吧。他搖頭,仍固執地擦完每家每戶的樓梯扶手。現在,很少能見到這樣的忠誠的門衛了。在他呆的兩年時間里,我們院沒有發生過一起治安事件,公共衛生也是一流的,被市政府評為“模范樓院”。現在這塊唯一的招人眼前一亮的牌子,仍掛在院門外墻的一側,雖是已如人心一樣銹跡斑斑。一言難盡,可還是足可追憶,足可給人們一個提醒。
秋天來了,小姜單獨向我吐出一句心里話:“我要走了,親戚介紹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聽到這話心里很酸,覺得我們虧待他了,冷落他了。我早先聽他說過,這里一直不給他漲工資。現有的年薪只管粗茶淡飯,一點剩余也沒有。想想一個才近二十歲的青年,身有殘疾,家在農村,如果這樣耽擱下去有什么奔頭?不能一輩子呆在這里看門護院吧,就是一條狗也未必能做到,主人也不至于這樣款待一條狗吧?
他一邊用蛇皮袋裝揀著醬醋瓶子,一邊幽怨地對我說:我不想呆在這里了,我知道有人故意不給加工資,就想擠走我,搶我的飯碗。這話是有針對性的,聽的人就不好問明,說的人也不必明說。這就是小姜給我的分寸感,只能替他惋惜了。一輛摩托三輪正在一旁場地上等他,也沒有一個人出來送他。或許,他是故意悄悄走的。一個有些心灰的人。這很容易理解,要走,沒有留戀的,倒不如不聲不響地離開,給自己一個體面的臺階下吧。我沒有過多的祝福,握了一把他的瘦削的手,代表了我想說而說不清的一切。如今我常常回想起這個小青年,他的勤勞,他的質樸,他的忠厚,他的不幸,他的殘疾,還有他的不可能被漲工資背后的那一重暗傷……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誰能替他改變這一切?
嗨,到現在我還是稱他為小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清楚他的鄉土在何方。
B也就在眾多的青年小夫妻恩愛得像膠化了似的時候,大院里有一對小夫妻徹夜難眠。他們沒想到自己的煩惱恰是別人期望的。為了趕走煩惱,當然先是請產假,看醫生,找偏方,然后又是服大量的藥,然后還是請長假,甚至不惜找專人陪護。使盡解數,肚皮還是沒動靜,或一有動靜立即就流掉了。恨自己肚子不爭氣,讓家人空歡喜一場,空忙活一場,空嘆息一場,花錢,出力,還揪心。一看別人的小孩,一天天從無到有在院子里哭爹喊娘地滿院亂跑,她就不由自主發抖,怪自己的肚子總不見動靜。原來如花似玉的麗容,日漸在這種渴望而不可得的煩惱中煎熬,枯萎,身體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流產中瘦得弱不禁風。我偶爾見到她在樓底下走動也心生憐憫,大院里的人一見到這情景都想幫一把。可是,別的事還好說,她這個事,有力也使不上。從她家三樓向外搭起的廚房鋁合金窗戶里,常能看見一個八十多歲的頭發花白的老嫗身影顛顛簸簸。老人天天給這位孫媳婦遞茶倒水,或者做些吃的給她滋補。無疑少婦請了長假靜候佳音的。有沒有求過送子觀音很難說,一個病急亂投醫的人尚且如此,更何況關乎子嗣繁衍的大事。寧可信其有的心態,在眾多人心里還是泯滅不掉的。這個女人年紀輕輕,如花似玉,卻被一場生育大仗打得焦頭爛額暈頭轉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還遭人嘲笑白眼,談何幸福美滿?然即便是這樣,仿佛還不是命中的沉重一擊,又一波風浪仍在等著她接受蹂躪的摧殘:弟弟突然患上尿毒癥,急需大把金錢去挽救垂危的性命,這火燒眉毛的錢,又不知從哪里著落。禍不單行的厄運把青春的嬌容霜侵似的打得黃皮寡瘦。百無聊奈中,我看到離小區不足百米外的一處新門店里的主人,正是剛剛流產不久的這個女鄰居。店門口一處醒目的大招牌,寫著鍋貼餃、鴨蛋、稀飯之類的價碼。我走過去,盡量享受這并不給人好心情的早餐。傍晚,我正在人流熙攘的廣場散步,忽見擺著許多兒童玩具地攤的過道上正是她,立即蹲下來去挑選,她立即向我推薦什么最好,什么最讓男孩喜歡。我該買點什么給即將回老家過年的小侄子呢?我也替她難過,是什么使她想去批發玩具擺地攤的,是不是心中的那種原始天性的母愛?她一定無數次幻想過,假若上帝有個寶貝賜給她,她就是這個世上最幸福最富有的女人了,即使沒有了其他,給她個孩子什么不幸都愿意接受。那時她將買許多許多玩具給自己的孩子。只要有孩子,她一定能做到這一點。可憐的女人,剛剛嘗到愛情的甜蜜就陷入災難的重圍,差不多卷入困頓絕望的漩渦,生活的笑臉被污穢苦惱涂滿,被貧窮和死亡的壓力打擊得回不過神來。她還是那樣讓人驚詫地挺住了每一天!這股力量又是怎么誕生在她的心里的?地獄一般的暗無天日,給這個女人帶來的將是什么命運的摧折?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了,我仍不敢想這件事情。鄉風對不懷孩子的女人很無情,素有“養個母雞不下蛋,拎起往下摔”之類的民謠。舌頭底下壓死人,即使別人不說,自己的心理關怎么過得了呢?值得慶幸的是她終于懷上了,分娩了,現在孩子也走路了,能口齒不清地喊她一聲媽了。每每打量這個皮膚白皙路還走不穩當的“小伙子”,心里就有一股陶醉的潮濕涌出來。
真得替他們慶幸,為母子暗暗喝彩!天遂人愿,畢竟想要的來了,雖然來遲了,雖然經歷了無數的曲折和磨難,但畢竟如愿以償了,多少還是個圓滿的結局吧。只要想想,世上還有多少平凡的人,因為一個普通的愿望終生求索而不得,那又該怎樣挺下去呢。“生活,意味一切都得挺住。”這是外國一個哲人所言,也是對無數的不幸者的安慰與歌贊。畢竟走過來了,回看萬水千山,也不免寬慰幾許。
現在這個年輕的媽媽正是給他的孩子買玩具的時候了。我沒有看到她的孩子有玩具。她有了孩子,她賣過玩具,還勸我買過她的玩具,我相信每個媽媽都挖心割股地對自己的孩子真好,那又是什么奪走了媽媽手中已經擁有的那一大堆玩具呢?一個傍晚,我遇見這位年輕的媽媽,問她當初的那些玩具放在哪里,她的回答讓我心涼:早就讓給別人了,廣場上賣不動,占用了資金,冤,就脫手了。當然我沒問虧沒虧,像這樣的倒手買賣不問也可想而知,我何苦再去撕結痂的傷疤呢,太不仁慈了,不地道了。就在這之前,小偷撬開了她家的防盜窗子,并盜走了她的手機、她丈夫褲袋里的幾百元現金。她連報警的想法都沒有,這事就算被“黑下”了。兩口子,不怨也不惱,仿佛已經“神馬都是浮云”了,生活讓她淡定從容多了。不報案的事,在僻遠鄉村很多,能捂的都捂了,這是體諒警察的辛苦,也是為了少折騰自己吧。看起來是對小賊的放任,實則是對小偷的可憐。就這樣的人家還偷,不是沒長眼,就是沒長心!消息傳開,大院里人莫不破口大罵蝥賊。這小偷,要不就是窮得揭不開鍋,順著樓洞爬上去,萬一摔死了怎么辦?理智點的似在替賊想,這樣的“被摔死”的小賊也不是一個兩個,難道他們偏喜歡這樣冒險、這樣玩火,甘做亡命之徒不成?這樣一想,倒也是很后怕的。
C樓道里黑洞洞的。聲控燈用過幾年之后一律不聽話了。一個樓洞五層,門對門一對鄰居,公用一盞樓燈。越往樓上,要過的樓道梯級越多。假若最頂上的一只燈壞了,那么兩扇門的對鄰必有一個先得自覺地買一只燈泡。先買了就買了,不便向未掏一分錢的對門去言說,以免落個表功之嫌,還遭腹誹,公用嘛。一盞燈泡畢竟要不了多少錢,勞神是勞神點,安裝費點心思,氣力,需得找門房,扛鋁梯。上五樓的頂口,是個切切實實的粗活,鋁梯雖是活動的,然而畢竟進進出出,上上下下,確不方便。但自己為自己服務嘛,也兼顧了鄰居,也就懶得計較。說服自己的方法很多,譬如,不妨這樣想,一個人夜里喝酒回來,爬樓梯不慎,摔得鼻青臉腫不說,還摔折一條腿,在醫院花掉幾萬元,找保險公司賠付,轉昏了頭未必就遂愿;又要給手術醫生送紅包,還落個終身殘疾;還得在單位年終考核不合格時扣工資扣獎金,甚至耽誤了早晚接送孩子,多不值呢?你說買個燈泡值,還是損失一大堆值!這家的老婆過去老是罵男人喝得醉醺醺的晚歸,后來突然不罵了。人問其故,她老實坦言:曾看過一篇報道上寫著,一個女人帶著孩子在家,為防賊防盜,每天給自己門外放一雙42碼的男人鞋。這個十分怯懦的行動感動了許多人——被報道的那個寡婦就每天這么戰戰兢兢度日。這哪里像人過的日子啊!聽話的也明白了:這個女人,還算不糊涂。后來這家老婆對男人的罵聲銷聲匿跡了。男人回家也比過去早多了,酒也漸漸被疏遠了。
當然也有人家就是不繳看門護院的費,明知沒理由,辦法就是躲和拖。躲,就是不給你人影看;拖,就是催了也白搭,沒態度,沒言語,沒行動,沒效果,甚至效果更差,攪得院里老崔頭疼,悔不該當初進來時沒一家一戶簽個協議。六十家共居的小區,物業管理費幾乎沒收過一分。當然,這都是由推薦出來的一個七人管理委員會義務代勞的。老崔是委員長,麻煩都交給他終決。為小區安全起見,干脆請了個老頭當門衛,每戶年均出100元作看護報酬,兼算垃圾運送費。院內衛生清掃,樓梯樓道擦抹,甬道野草清除,還有人來人往監視,夜間開門放人,也是一攤子事,并不輕閑。可是,有戶人家,主人就是連年拖欠,到年關就鎖門走人,把責任推給遠在北京做裝潢的男人。男人偶爾進家也像賊一樣,悄悄地來偷偷地走,像是打游擊,生怕被義務物業管理委員會成員逮住了,但還是露出了尾巴。委員會的幾個人進他家,堵門說理。那家女人放風,推托房子已準備轉買給外地人,自己不想在此住了。弄得物業小組成員很為難,好不容易去封門捉鱉,說理就是油鹽不進,打官司得不償失;不打這個官司吧,又讓看門老魏頭三天兩頭喊著要走人,聲音里帶著要挾的味道。就是這樣的老實人也禁不住“橫”了,兔子急還咬人呢!這年頭,若請個保安花費更大,保安若是自盜起來,也許更不安全。大家盤算著還是留住老魏頭要緊,于是妥協,答應決不少老魏頭分毫。可這邊沒給的費用又老懸著,顴骨很高的女人就住在我家樓下,他的老公在樓梯上見到我灰頭土臉,就是為催費用的事,他的承諾被老婆推翻了,狼狽的神態好像陽痿。我可憐他又惡心他。這惡心并非因這一事引起,這一家子總不愿在衛生間里排泄,異味耀武揚威地往上沖,常弄得我家的窗戶形同虛設。夏天悶得慌無法通風。冬天好多了,低溫不再幫那一對兒女三口之家囤積的糞便臭氣囂張。
就在這家女人喊著欲搬家后的日子不久,冷不丁他家猛地又請來了師傅上樓頂通道安裝天線接收器,就是那個微型鍋狀物,直弄得我家的人抱怨放亂了樓頂的太陽能熱水器的水管子。這令我有些心煩。看來,為了逃避電視臺收費,這家人是不打算裝數字電視了,干脆來了個一不做二不休,私下安裝另外一套既便宜又隱蔽的設備。根本就不是要搬家的舉動,不知在其他居戶心里起什么反響?五十九戶人家都對這一戶搖頭,甚至有人把怒氣遷到她的一對兒女身上。“世上這么蠻不講理的人,兒子討媳婦,女兒嫁婆家,人家都會隔二十四條田埂,能找到好人家么。”話是這么說,理是這個理,大家都是從泥田里洗腳上岸的,說出來的話直不楞通的,也不避諱誰。可是,總有較上勁的,吃生米遇上嗑生稻的。這家的女人當家,總把垃圾隨處丟,還是看門老魏過意不去,逢人便說,“真是要不便,把垃圾扔到我門口垃圾車里算了,還能叫你拿下來么?”這個“你”,沒人愿意給她傳話。她的反常行動,反而讓老魏頭更加頭痛,甬道里,過路邊,墻根下,偶有這么一袋,那么一袋,隨手丟的花花綠綠的垃圾袋,自然全是她家的,這給老魏頭找來更多麻煩。按理,一個女人帶兩個孩子,過的日子也不算差,竟然讓自己的垃圾也東躲西藏。受害者是老魏頭,他還得每天撿,每天送,不撿不送就發臭,一發臭老魏頭就覺得對不起人,拿了虧心錢,也給人家留下話柄子,壞了自己的口碑。老魏頭氣得眼珠子發黃臉泛青,又不肯丟下老臉去求她。無處發泄,就打牌。幸好有幾個老太婆閑了無事,每天下午在他的門衛室里陪他玩牌,他才慢慢消了心頭的氣,否則一定堵得慌,說不定還堵出個病來!
畢竟,在這個大雜院,從不同地方聚攏的人,在這里有緣無緣地相見了。出入一個大門,發生過許許多多雜七雜八的事,痛快的,不痛快的,都數不清。小姜的飯碗弄丟了,小夫妻算是苦盡甘來,不給看護費的還是拖欠著,院子里的人們,日子還得照樣往前過,像流水,像落花,各色的夢繼續做著。活著的人,幸與不幸的人,當回事的,不當回事的,就各做各的,理由五花八門,人們評頭論足,說話間,有氣憤,有淡然,習慣了一次又一次將過往心頭的垃圾抹掉,雖然又會沉積新的垃圾,似水流年的雜院,形形色色的亂象,將與人們的恩怨一起,讓時光的塵埃一起卷走。每個時代都是一條滔滔奔騰的大河,順流直下的我們,每個人都是那退潮的河床上的泥沙,或是那寬闊河面上漂零的零葉,尋找的是貌似明確的方向,沉淀的是善良者的恩澤。
責任編輯 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