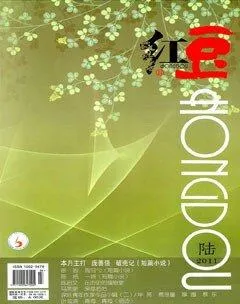高雅的記憶
時間與歷史的—個功效就在于記憶。美好的記憶,深層的記憶,高質的記憶,來自文化,來自修養,來自人生閱歷,來自對生命的負責態度。當那種深刻升華為記憶的魂靈之際,高雅的記憶就會真正地誕生。
楊秀華先生很早以前就想把自己這大半生的“風云生涯點點滴滴”編輯成—本書,好讓記憶在生命宇宙的綠野間生根、發芽、開花。現在,這種愿望變成了現實,因此,在文化的寶庫中便增添了一本《風云生涯拾零:卜書。一種記憶催生另外一種記憶,是這本書的價值之一。他把論文、散文、詩歌、散文詩、新聞報道,甚至工作研究、經驗總結等都匯攏成集,編織自己人生的長河,載著被時間阻隔的心靈,貫穿著一縷愛的光明,這就形成了一種高雅記憶的核心。
于是,我想起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悠悠歲月,人生長河中開始浮起回憶的島嶼。最初是一些隱隱約約的小島,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幾塊零星的巖石。接著,又有新的島嶼開始在陽光下閃耀。茫茫時日,在偉大而單調的擺動中浮沉回轉,令人難以辨認。但漸漸地終于顯出一連串時而喜悅時而憂傷的首尾相銜的歲月,即使有時中斷但無數往事都仍能越過它們而連接在—起。”
是的,甜蜜的回憶,親切的鄉音,宛如諧音幽幽的旋律,不時縈回在作者的心頭。而在那往時的經歷中,縱有名邑大川、碧綠大海、夢中風光、戀人倩影,卻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在故鄉方竹山的竹林下留在幼小心靈上那深深的記憶一吹、拉、彈、唱填滿了小小的腳印。
一條泥濘的小路,敘說著父親楊助庭的勤勞樸實、忠厚坦誠。他所看慣了的也是擁有了的是那小草偷偷地從土地里鉆出來,嫩嫩的,綠綠的。風里帶來新翻的泥土的氣息在濕潤的空氣里醞釀著一個“沉甸”的歲月。
一株古老的大樹,記載著母親黃樹芳是勞動能手,她勤儉持家。享受過了的是那像細絲一樣密密斜織著屋頂上的層層薄煙。
《風云生涯拾零》道出了楊秀華鏗鏘的腳步,心靈的震顫,如訴如泣,無飾無掩,鏡子般真實。許多人曾經不斷地尋找,希望找到一位人生之導游。終了,他們才發現,這位導游正是自己。因為在每扇心靈的大門里,都關著一卷難忘的史詩。
飛翔的日子,掠過作者的眉頭,讓他記錄著才華興盛的歲月:“自1966年起,在陸軍131師直屬文藝演出隊任創作組長、樂隊隊長、文藝演出隊隊長和指導員職務。十多年來主持組織編導了二十多臺文藝節目,以小歌劇、小歌舞、話劇、相聲、數來寶、快板書、三句半、詩朗誦等文藝形式,兵演兵,自編自演,深人海島部隊巡回演出,走遍了海島邊陲軍營、高山哨所。在海南島萬泉河畔,南渡江邊,五指山下,榆林港頭椰鄉漁村都留下了優美動聽的樂曲和威武雄壯的軍歌。”
曾記得,大海在他筆下,是那樣的豪放:“他,一個不規整的酒杯,盛滿了一天星斗,還有一彎月亮;也許,一場暴風會把星月搖散,但杯子里,依然是戰士挺立的身影……”這就印證了美國著名詩人惠特曼的話:“一個人,雖然不是偉大的藝術家,可以與偉大的藝術家同樣神圣和完美。”
《風云生涯拾零》其實是楊秀華先生一半生涯藝術實踐的小結。在有漁燈、有浪花、有小島、有風帆的夢夜已經過去了的時候,1980年解甲還鄉。
葉落草黃,大雁飛去,楊秀華依舊是一個有心的思想家、無言的文藝工作者。早在1992年3月,《中國水利報》就在顯著位置上刊載他的散文《流光溢彩鳳凰湖》。藝術的藝術,表達的光輝和文字的光彩,都在于純真:“道旁花草垂柳錯落,紅動綠揚,湖邊的幾個山巒滿布著荔枝、龍眼、橘子、芒果、山棗、菠蘿蜜樹,新綠默默地打扮著春天。聽濤閣濤聲陣陣,松鶴樓青松掩映,白鶴低旋,令人神思飛揚。”(《流光溢彩鳳凰湖》)好一幅江南水鄉之墨畫,讀來不由讓人想起朱自清的《春》來:“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帶著甜味兒;閉了眼,樹上仿佛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
歷史是記憶的翅膀。在寫這個序言之前,我曾給作者—個承諾:我會如實地讀這本書,然后如實地寫序言。如今,他敲打揚琴的聲韻已經爐火純青,高音的清純剔透,中音的光彩明亮,低音的渾厚圓潤,具有豐富的表現力。愿他在今后的歲月里,揚琴演奏技藝更為精湛,文學方面更加文筆精華。
楊秀華,成功在于才華橫溢,失誤也在于才華橫溢。然而,他是成功的,他有一個神奇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