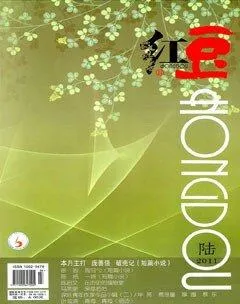青花瓷
我的母親是在我十歲的時候死掉的,她死的時候我只有十歲。
我的母親喜歡一種瓷器,青花瓷。所有青花瓷的東西她都喜歡,仕女圖的瓶、鯉魚的碗、漢隸書的小酒盅都是她的最愛。我的父親是個皮貨商人,她認識我母親的時候我母親還是個學生,據說我母親是校花,父親在南方做生意,他用這些瓶瓶罐罐打動了小他十多歲的母親,跟他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北方。我的外公外婆就她一個女兒,因為母親遠嫁,哭瞎了眼。
有一段時間,在我記憶的那段時間,父親給母親從南方運來了許多許多的青花瓷。許多的青花瓷在日光下閃著清冷的光。那一次,我的父親也回來了。他給我的母親帶來了螃蟹。晚上,母親在餐廳里有滋有味地吃著大個的螃蟹。父親一臉的疲倦。風有些涼,吹進來轉個圈圈,是圓圓的圈,又慢悠悠地蕩了出去。保姆走過來對我的母親說,別吃太多,這個東西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母親笑笑。母親笑起來很好看,她對準新郎和善。我相信我的母親是善良的,是溫柔的。
母親在淡綠色的罩子下欣賞她的那些寶貝,她不能冷淡發著青光的器皿。在母親的世界里,她好像只關心這些冰冷的東西。
那天她坐在燈下欣賞著瓷器,我的父親坐在屋子里聽流行的歌唱和外面河里的蛙鳴。父親滿臉的疲倦。風令人難以察覺地進來,昏乎乎的燈光顯得濕潤而飄忽。母親在燈下仔細地、小心地撫摩著父親為她帶來的那些青花瓷,她小巧玲瓏的鼻尖上滲出鉑金般的汗珠子,碎銀子一樣的。
父親踏著光虛虛的進來,眼屎還粘在眼角。他沒有看我,他不喜歡我這個女兒。
你先看吧,我去睡了。
半夜里,我被母親的尖叫震醒,我看見母親像一只垂死掙扎的貓恐怖地翻滾。母親送進醫院的時候,就死掉了,死的時候剛三十歲。我沒有舅舅,我母親被醫生判成食物中毒后埋葬了。她死的那年我剛剛十歲,上小學四年級。
我覺得那個冬天太長了,長得眼睛里發了霉。
半年后,柳翠翠,我的繼母進了家。我這才知道父親早就有了兒子,也就是說母親還在世的時候父親就有了別的女人,已經給他生了兒子。他的兒子已經三歲,也就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已經三歲了。
于是我在家里成了個多余的人,是我父親多余的孩子。母親死后,我每日每夜地守望著月光,守望著母親留下的一屋青光,守望著母親留下的最愛。它們正在靜靜流動的光中破碎。
守望,成為我的全部生活!
在母親去世的那些寂寞的日子里,各處有一種霉潮的氣息。我長久地坐在這種氣息里。我常常想到那天的螃蟹。一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內里卻似乎含了無限的玄機。我苦苦地糾纏在這些事里。
一切源于父親帶回來的女人,一個比我父親小二十多歲的女人—柳翠翠。
一切源于父親帶來的弟弟,弟弟已會邁著小腳走。
那真是—個多事的季節。那時院子里很空寂,夜氣有些陰涼,院子右邊的楊樹像一口鍋蓋下來,一直蓋下來。而院外的一道道屋脊模糊不清,好像有蝙蝠在那里飛,其間還有許多如墨一樣的樹冠。這個景象我非常熟悉。所有的日子幾乎就是這種情景。
我茫然地看著屋子里的瓶瓶罐罐,青光映在我的臉上。
這個季節,這個日子,與我有關,與我的弟弟有關,與母親留下的青花瓷有關。
這些漂亮的青花瓷,它同我的母親有關,它是我父親從南方運來的。聽母親說那里與我們這里隔了千山萬水,從這么遠的地方運來的青花瓷一個就是我家當餐具用,再者就是供母親欣賞。因了母親的喜歡,以至于我們家里用的碗、碟子都是這種色調,擺在角落里的也是這些瓶瓶灌灌,它們在陽光下閃著青幽幽的光。這種光刺得我常常睜不開眼。這些東西運來不長時間,我的母親就死掉了。看來這些青花瓷在出發的時候就帶來了某種不祥。只是,只是我那個小父親十來歲、喜歡這種東西的母親忽略了這一點。母親死后,這些閃著青光的瓷器依舊放在我家別墅里的角角落落。我的叔叔,我那個年輕十足的叔叔,我那個每天和柳翠翠打麻將的叔叔,經常拿走一些瓷器。不過,叔叔這個拿并不長。有的小東西它真是太獨特,太好玩了,比如一個湯匙,它的上面是個骷髏頭,看上去不可怕很古怪,難怪我的母親會喜歡,難怪她會被這些青花瓷迷找不到自己了。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家里的一切都具有不祥的信息。當時家里的每個人也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是不祥之物的傳聞是在我出事之后才有的,于是我的叔叔,我那個來打麻將的叔叔再也沒有從我家里拿這些好看的青花瓷,并且把偷偷拿去的東西又拿了回來。這是以后的事,在這里我不想說。
在災難發生之前我一直是個膽小怕事、縮手縮腳的女孩。繼母柳翠翠對我還算可以,我和弟弟相處得也很和諧,只是叔叔和父親不喜歡我。可是,無論怎樣,在災難來臨之前的日子里我還有自己的安寧,我還可以自由自在地喜歡母親留下的那些沉靜、飄逸的東西,還可以無拘無束地看柳翠翠晾在升降衣架上的胸罩,我對帶著蕾絲花邊的胸罩有著好感和神秘。
出事的那個日子,天氣暖融融的,空氣中飄著油煙的氣息,散發著刺鼻漚腐氣味的垃圾桶前有許多蒼蠅迷地飛著。
那個時候,繼母柳翠翠在和叔叔他們打麻將,父親去談關于皮貨的銷售問題,我在欣賞母親留下的物件。我越來越喜歡這些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的物件。我真是越來越喜歡。真的。假若沒有這些飄逸的青花瓷,就不會發生以后的事,假若母親不喜歡這些物件,就不會嫁給大她十多歲的父親,就不會有我。可是,可是……沒有了假若,假若那天的日光不是那樣的暖融融,那些物件就不會吸引我,也就不會發生后面的事,但那天的陽光暖融融的,母親留下的仕女圖的嫣然一笑令我著迷。我用盡力氣拿起了桌上的精致瓶,它在日光的照耀下閃著誘人的光澤,瓶上的漢隸書是那樣的飄逸。我癡迷地欣賞著,忽然就看見了跑過來的弟弟。
我的手哆嗦了一下。
瓶落了下去,它發出的不是清脆聲,因為它沒有落在地上,它落在了我弟弟的頭上。
我是無心的,我真的是無心的,我是膽小的,是軟弱的,我和弟弟是和諧的。我是喜歡這個活潑的弟弟的,盡管我拒絕著柳翠翠。真的,我真的是無心的。我怎么知道他會來?我怎么知道他會來呀?但是,他來了。如果我沒有看見他來,如果我的手不哆嗦,那么,我的弟弟就不會死。可是我看見了,我的手哆嗦了,瓶砸在了弟弟小小的頭上。美麗的瓶碎了一地。
從此,活潑的弟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個有著仕女圖的花瓶帶著最后的溫度砸在了弟弟的頭上。血像黃昏下的夕陽一樣染紅了那些碎了的瓷片。生命,是這樣的脆弱!
我呆了,我呆了,很久很久,我才發出尖叫,像狼—樣的尖叫,我抖成一團。
繼母柳翠翠聽見我的尖叫時,她正自摸了白板。她奔過來看見躺在血泊中的弟弟,臉色變得異常蒼白。我的叔叔也跟了過來,他帥氣的臉鐵黑。我看見柳翠翠和叔叔手忙腳亂地把滿頭是血的弟弟抱起來,我看見柳翠翠的臉上,身上全是紅色。在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發現我的時候,我飛快地逃離了事故現場,一路跌跌撞撞地奔,沒有目的。我看見柏油路上的車快速地飛奔。在城區的郊外,我像一條喪家狗一樣趴在一塊冰涼的石頭上,我的汗打濕了石頭。
父親得知弟弟死掉的消息是在黃昏。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正在同客戶談皮貨銷售的父親,把皮子撕了。聽說談貨的客戶見皮貨不結實,也走了。是叔叔給父親打的電話。父親總會知道的,沒有人阻止他知道,他總會知道的。看著老遠走來的兄弟,他的兄弟穿的是西裝革履,我的父親無限悲涼地說,我真是命中無子、命中無子呀。他沒有去看我死去的弟弟。
我是在凍了一天一夜昏迷后,被一個撿破爛的人送到派出所,被叔叔帶回家的。我在夢里總是夢見弟弟滿臉血污地追趕我。當我蘇醒過來時,我聽見繼母柳翠翠摔器皿的聲音。我想坐起來看看,看看是什么被摔碎了,可是我的腿好沉,頭好疼。我聽見柳翠翠說,這些破東西,這些不祥的東西,都是這些鬼東西害死了我的兒子。我聽見柳翠翠鬼樣的哭。
我的眼淚頓時沖眶而出,弟弟死后我第一次流淚。淚水在我的臉上肆意地淌著,悲傷在我的體內升騰。
死氣籠罩在我們全家的頭上,以后我似乎再沒有看見如那日般暖融融的陽光,就算是陽光明媚也不能給我家帶來好氣氛。十月的天漸漸涼了,黃葉落得像金。我的父親老了,他仿佛是一下子老的,頭發全白了,生意也不順利。他經常出錯,經常忘東西,先是把老花鏡放在母親睡的臥室里,找遍了屋中所有的角落也找不到。—件衣服要穿很久。誰也不敢提弟弟的名字,似乎那名字是一枚炸彈,都回避著。柳翠翠在好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打麻將,最后自摸的那塊白板還像英雄一樣豎在房間的桌子上。在她把母親留下的最愛摔碎以后,躺在床上—個月不能動彈!
弟弟以及那些美好都隨著這次意外走了,漂亮和飄逸、溫暖和快樂這些明快的詞語只留在我的記憶里。
我在無意中毀了全家人的希望。
誰都知道,弟弟是父親的命,是父親的心,是父親的唯一,是他身上不可或缺的物件。父親的三個老婆,只有這個柳翠翠給他生了個兒子,他一直把這個孩子當做希望養著,每次回來都給他買好多玩具,陪他玩耍。我永遠忘不了父親把弟弟摟在懷里的情景,他臉上的笑容似乎只是給這個希望的,這個孩子是我們全家、全族的希望。叔叔一生無正經職業,娶了老婆都沒有過一年的,沒有哪個女人甘心為他生子。幾個本家生的也都是千金。我真是把父親的希望毀了。
是我用一個瓷瓶把生活毀掉了。是它改變了許多人。誰也無法想象,要是我的弟弟活著,我們全家是一幅怎樣的景象!父親快樂地做著生意,柳翠翠安詳地相夫教子,我也自由自在地上學。弟弟死前,柳翠翠對我還是可以的,她給我買的一雙帶有動物圖案的襪子我至今還沒舍得穿。弟弟呢,他是那樣的天真可愛,無論是家人還是來串門的都非常非常喜歡他。那時我真有點嫉妒他,可是我真是無意的,現在我寧愿死掉的是我。
在這以后,柳翠翠變成了另外的一個女人,她成了個惡氣十足的女人,用難聽的話罵我,罵我那死去的母親,罵被她弄碎的物件。她對父親兇得就像一只母老虎。她邪火越發越大,就如同年夜里燃放的煙火,早在點燃之前就憋足了勁,把我們炸得灰飛煙滅。
叔叔在柳翠翠打碎所有的青花瓷后,就把從我家偷偷拿走的物件搬了回來,放在了那堆碎了的瓷片上,還從家里帶了個黑塑料布,用它蓋了蓋。從破洞里露出的一道道青光,它帶著讓人不可名狀的色彩。
我的叔叔再也不喜歡這些破東西了,他說我的母親就是因為喜歡這些不祥的瓷器才死得那么早。父親為母親運來的青花瓷徹底在我家的角落里消失了,沒有了青花瓷就像沒有了母親一樣。
我的淚水簌簌地飄著,我知道這僅僅是我生活的開始。柳翠翠,一個被仇恨點燃的女人是不會輕易放過我的。我也不清楚,我在這么多的仇恨里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終于下雪了,我一個人縮在角落里。透過窗戶我看見父親站在院子里,輕飄飄的雪花使院子里顯現出銀白色的世界,墻角里那些碎裂的物件披上了銀裝。我再想找一點母親留給我的美好,哪怕一點,一點點也沒有了。停留在上面的雪花分解成珍珠滾下來。天真冷呀,供暖的煤還沒有到。我聽見父親的聲音里有著太多的無奈和蒼涼。對他這種蒼涼的聲音我感到驚俱。我想,父親的衰老與我有一定的關系!
斷斷續續的幾場雪之后,房屋愈加素白起來。在重疊的廊檐和黑紅的院墻中,與漸漸變得虛弱的陽光有些相似。風狠狠地把雪甩下來,不斷有輕飄飄的小白花飛進來,裸露的碎片看起來有些憂傷。柳翠翠的胸罩我再也沒看見過。自從弟弟死后,柳翠翠再也沒有逛過商場,她沒有買新的有蕾絲邊的胸罩。
柳翠翠看來是發誓要為兒子報仇。有一次她把貓拉的屎讓我吃,我不張嘴。我用哀求的目光望著我的親人。我的叔叔冷冷地看著我,他用力把我的嘴掰開,柳翠翠狠狠地把貓屎塞進我的嘴里。惡心讓我嘔吐起來。柳翠翠撇撇嘴,叔叔也踹了我一腳后離開了。我吐得一塌糊涂。從此以后我吃什么再也沒有了飯的滋味。想到母親,想到母親留下的最愛,我還是淌下淚來。淚水簌簌地落著,如窗外的雪花。
原來美好和愛是這樣易碎的,它改變了母親的命運,它也把我的一切都改變了。它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風是脆弱的,是沒有理想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父親如天邊的黃昏,他的生意也在漸入冬季。他的背明顯地駝了下去,看上去比柳翠翠要大三十多歲。年輕的柳翠翠看他的目光是厭惡的。
沒有了兒子的父親是孤獨的,沒有了兒子的父親是寂寞的,沒有了兒子的父親沒有了斗志。
冬天的夜太長了,父親自言自語地說,他似乎是想談別的卻沒有找到,就這樣說了出來。
來打麻將的叔叔有些鄙夷地看著他,說,你的夜是太長了。父親沒有理他。
在這件事發生以后,沒有了兒子的柳翠翠變得喜怒無常,一會兒哈哈大笑,一會兒又大發雷霆。沒有了兒子的柳翠翠讓我恐懼。
日光和以前一樣,風還是有些脆弱。院里的長椅,屋子里的吊蘭以及幸福樹都在遠去,使得我在空曠中平添了幾分憂傷。我預料中該發生的事,或許本來是細微的變化,都沒有如期來臨。我茫然地看著飄過來的光,那是我家院里楊樹枝漏下來的細光。我一直都不喜歡院里的楊樹,它籠蓋四野的虬枝讓人覺得陰森,透著某種不祥。
柳翠翠和叔叔的笑聲從遠處飄來。隨著消失的笑聲,她出現在我的房間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柳翠翠來到我的身邊,穿著高跟鞋的腳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腰上,我疼得摔在地上。我禁不住呻吟起來。
地上的陽光逐漸弱了下去,白得格外刺眼。我的父親陰沉著臉站在虛假的影子里,他用一種不確定的聲音說,翠翠,別再這樣了,好歹她是一條命啊。柳翠翠撇了撇嘴,她是一條命,我兒子的命就不是命了?說完,柳翠翠踏著細細的光離開了我的房間。
我聽見父親重重地嘆氣,帶著無奈。這無奈在嘆氣之前就已散開。這一聲嘆息似乎傳遍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
我看見我的父親打了個寒戰。他站起來,在那堆破爛的碎片中撿起一片,報應啊,報應。聲音在虛虛的光影里很快消失了。
日子漸漸地長起來,天氣也變得柔和了些。叔叔天天來打麻將,他的皮鞋發出噔噔噔的聲音。頭發上噴的發膠有種糊焦味,就像我吃東西的味道那樣惡心。
冬末的空氣里開始有了點春的氣息,叔叔和柳翠翠都守著自己眼前的牌,柳翠翠一手托腮,另一只手輕輕地用麻將敲著大理石的桌子。這種聲響時常地把她帶到一個她自己也說不清的地方,從嫩葉里漏下來的光照在他們的臉上。柳翠翠自摸了一下,白板,她夸張地把這張牌舉過頭頂。
柳翠翠抬起眼,她看了看打牌的其他三人,她覺得他們都像得了麻風病的人。她忽然哭了起來,臉上的胭脂、嘴角的口紅讓她變得花花綠綠如鬼。其他的牌友見此,悄無聲息地走了。只留下叔叔在勸說,你是不是想起了那日?你是不是又想起了兒子?
柳翠翠抬起頭,惡狠狠地說,是,是,我在夢里已殺了她幾千回,我還要生兒子。
叔叔拿過毛巾,生吧,我讓你生三個兒子,我會讓你生。
柳翠翠這次的改變更加瘋狂,我愈發地恐懼。我一直在害怕她對我的仇恨會一直無休止地持續下去,我一直害怕她還會對我做出什么。我整日惴惴不安。
這個日子還是來了,柳翠翠現在脾氣變得格外暴躁,那個還有著一絲溫柔的女人不見了。她是在春天到來之前對我動的手。春天來了,蛙在剛化凍的河里嘶啞地叫著,有種絕望的意境。我擦地板擦得精疲力竭,走出我的房間時我覺得格外冷。我穿了一件厚的衣服,這件衣服讓我還是情不自禁地打寒戰。
冬天,這個該死的冬天不肯離去,春的跡象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我靜靜地坐在屋子里,我像狗一樣地擦著地板。我每天就是把地板擦干凈,擦不干凈柳翠翠就會讓我舔。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了小蟲子,有了小蟲子說明季節還是在按規律走。
那個日子跟平常沒有兩樣,沒有風,那些被柳翠翠摔碎的瓷片爬進柳翠翠的手里,它們閃著冷冷的青光。
我像狗—樣爬到客廳里,直到柳翠翠到來。我看見紅拖鞋的時候,我才感到一股陰冷襲來。我看見她手里拿著破瓷片,我看見魚在裂片上的煎熬。我的心懼怕到了極點。我轉身想往外面爬,但我還是被柳翠翠抓住了。她用帶著我所鐘愛的魚的瓷片,深深地、深深地在我的臉上劃過。我沒有感覺到疼痛,只是有一股咸咸的液體滾進我的嘴里。我跑了出去,我看見父親驚愕的表情。我晃了晃,昏了過去。
這一天是我面目變得猙獰的開始。
我被父親送進醫院里,臉上的傷很深。醫生說我再也不可能恢復到以前了。從這一刻起,美麗離我遠去。在我入院的這些日子里,沒有—個親人在我身邊,父親花錢請了個護工。護工是個五十多歲的鄉下婦人,她對我的態度惡劣,說我本來就不該做人,該托生成豬。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覺得她的嘴里有股酸腐味。
她和醫生說我像只老鼠,她說她從小就討厭老鼠。因為小時候她的母親只顧著去和父親粘在一起,根本沒有時間照看她,夜晚來臨的時候老鼠總是來咬她,她的一只眼是瞎的。她說我的樣子就像一只老鼠。
她給我拿來的飯是別人吃剩下的。我捧著小米粥,眼淚嘩的一下子全落下來。
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走到外面,外面真好。醫院里的味道讓我只想嘔吐。站在樹下,我嗅到了甜甜的氣息,嫩芽在枝頭悄悄地綻放。朝遠處看去,四野一片春的景象,有些模糊,有些希望,更多的是憂郁和寂靜。筆直的柏油路伸向天的盡頭。一切看起來是這樣的迷茫。野外的河水已經化了凍,在輕輕地流淌。看來季節是真的到了春天。
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臉上的傷疤開始疼。它的疼是在我有了知覺之后。天色變成了灰白,遠方一切灰蒙蒙的。我忽然感到一種空蕩蕩的恐慌。我無目的地向南走著,一直向南走著。在一個小村一個城市里過著夜,躺在小村的破屋下。我非常餓,我非常渴望有一碗熱熱的粥,然而黑糊糊的夜只有天上的星星如影隨形。躺在城市的霓虹里,我非常疲憊,非常渴望有一張舒服的床,然而閃閃爍爍的霓虹里,只有汽車的鳴笛聲。
不知走了多久,我來到一個小鎮,我看見了母親所喜歡的物件。我倒了下去。醒來,我看見一個白發老人。
老人說,你吃了兩盤餃子。
老人說,你睡了整整兩天。
老人說,你的口袋里有我們的東西。
我的眼里流下淚,我聽見遠處傳來好聽的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你隱藏在窖燒里千年的秘密,在潑墨山水畫里,你在墨色深處被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