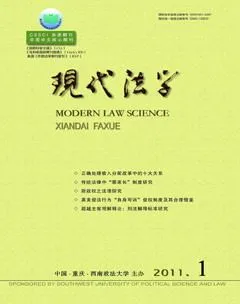刑法之靈活性及其意義
摘 要:與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強調自身的確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強調確定性的刑法,也不能總是以維護自身的確定性為由,全然無視變化的需要。從實質正義的要求出發(f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同樣也是實現(xiàn)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則。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實踐中,靈活性的機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始終都是存在的。靈活性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克服法律在尋求自身確定性過程中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使法律適用的結果更加符合正義要求。但是,基于對人權保障功能的重視,刑法的制度設計在總體上是以確定性來限制靈活性的,確定性雖然不是絕對的價值,但它一定是優(yōu)先性的價值,因此,靈活性最終不能拆毀確定性。
關鍵詞: 刑法之確定性;刑法之靈活性;法治;罪刑法定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10
一、刑法之靈活性:一種可欲的追求
在人類社會法律實踐的歷史中,確定性始終是維護法律之社會價值的一種力量。要求法律具有確定性,是為了使法律的正義目標得到可靠的保障,法律維持秩序的功能正是由此產生。因此,法律之確定性乃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前提,而罪刑法定原則作為法治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表達,其理所當然地包含著確定性的要求。然而,由于社會生活總是會產生新的問題,使得法律經常無法在堅持其確定性的前提下滿足社會的需要,確定性本身有時反而會成為走向正義目標的障礙。于是,在追尋正義的歷史中,人們也將“靈活性”的特征帶入到法律制度之中。正是法律的靈活性,使得法律能夠滿足復雜與多變的社會生活的需要,不斷推動法律向前發(fā)展。基于對安全價值的偏重,刑法比其他法律更加強調自身的確定性。關于“刑法之確定性”,筆者已有專文討論。(參見:周少華刑法之確定性及其法治意義[J]法律科學,2008(2))然而即便是最強調確定性的刑法,也不能總是以維護自身的確定性為由,全然無視變化的需要。固守一種絕對的確定性觀念,只能導致刑法機體的僵化;而承認一種有限度的靈活性,則可以使刑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相對簡單的規(guī)則無論如何不可能圓滿地解決所有問題。有時,當法律以其確定性追求普遍的正義目標時,實際的結果往往與一定的社會目的相違背,在此情況下,不同的正義觀念之間發(fā)生了沖突,人們必須解決這種沖突,而解決沖突的辦法常常是需要靈活地適用規(guī)則。另外,即便在一個以法典為主的體系中,也總是會有許多法律應予規(guī)定,但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而未加規(guī)定的事項。德國的法學家施塔姆勒就指出:法典僅僅陳述一般性的原則,填補罅隙則是法官的工作;在法律沉默的情況下,還必須求助于法律自身的基本理念——公正,這實際上是等于將道德規(guī)范引入了法律判斷之中。參見: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法律科學的悖論[M]董炯,彭冰,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103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法官在面對“疑難案件”時,如果法律“不夠用”,就必須根據正義觀念靈活地處理問題。在刑法中,人們將目的論的解釋應用于構成要件的解釋,將人格因素導入犯罪的評價機制中,這使得刑法的適用擺脫了僵硬、刻板的形式主義的罪刑法定。所以,即使是對于刑法來說,那種絕對的確定性觀念也是虛妄的。在刑法的制度實踐中,靈活性的機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始終是存在的。
二、刑法之靈活性的理論根據
刑法之所以需要有一個靈活性的機制,主要源于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需要:一是為了克服刑法之確定性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二是為了對抗刑法的不確定性。而這兩個需求,歸根結底又是為了解決法治本身的內在矛盾,即法律的形式要求與實質正義之間有時會發(fā)生沖突的問題。
(一)刑法之確定性的相對性
任何社會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達到數學和邏輯學那樣的確定性程度,因此,法律的確定性必然是一種相對的確定性,也就是與相對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相伴生的有限的確定性。如果我們一味追求絕對的確定性,就必然超出我們理性能力的限度,這意味著會大大降低確定性的合理化程度,從而使我們的法律具有某種非理性的神秘主義色彩——確定,但不合理。
參見:鄭成良.論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個問題[J]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5(6)在刑法理論上,雖然“任何相信純粹報應主義刑罰觀或純粹功利主義刑罰觀的人或許會相信對每個犯罪都存在(原則上)惟一正確的刑罰”,但是,“因為理論自身的問題,功利主義理論或報應主義理論不能獲得相關道德法律問題的惟一正確答案”[1]。 所以作為特殊的法律種類,刑法固然有諸多理由擁有最高的確定性;然而,在對刑法的確定性懷有極大期待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即便是刑法的確定性,也只能在相對的意義上得到滿足,也就是說,刑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確定性。而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由于人類理性能力的有限,人類的預見能力還沒有完善到可以可靠地預告一切可能產生的事實的程度,所以沒有任何法律規(guī)范能夠縱覽無遺甚至能夠包括各種各樣的、只是有可能產生的情況。參見:彼得·斯坦,約翰·香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M]王憲平,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5實際上,立法者只能根據人類已有的經驗,并根據對未來生活極其有限的預測來制定法律,如果再加上立法者對社會生活的現(xiàn)狀和未來走向可能產生的誤判,那么法律要想完整和全面地規(guī)范社會生活是絕無可能的。而且,就算人類有能力對今天的社會生活狀況作出全面、準確的把握,并有能力制定出完全適應社會生活需要的法律,我們也無法讓今天制定的法律足以應對未來生活發(fā)展變化的一切可能。犯罪是一種與社會生活條件緊密相聯(lián)的社會現(xiàn)象,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新型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可能不斷產生,如果刑法不能對此作出恰當的反應,社會秩序就不可能繼續(xù)得以維持。而要避免因法律僵化和滯后所導致的規(guī)范缺失和社會失控,我們的法律既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封閉的規(guī)范體系,也不可能總是拒絕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所提出變革要求。因此,絕對意義上的確定性具有某種虛幻性和誤導性,如果存在這樣的確定性的話,它也只能使刑法趨于僵化,并最終難以適應社會變化。
第二,法律是用語言來表達的,但是人類所使用的語言并沒有完善到可以絕對精確地表達一切立法意圖的地步。法律的語言大多來自于日常語言,而日常語言與數理邏輯及科學性語言不同,其意義通常并不是十分明確的、清晰的,這是因為“任何詞(語言)都已經是在概括”[2]。通常,一個詞語所能擁有的只是一個意義范圍,而不是惟一確定的含義,而且,即使是這個“意義范圍”,也并不存在一個可以準確把握的邊界,我們理解的一般只是它的核心含義。在核心含義之外,語言的意義趨于模糊,這就可能出現(xiàn)多重理解。“可能的意義在一定的波段寬度之間搖擺不定,端視該當的情況、指涉的事物、言說的脈絡,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語的強調,而可能有不同的含義。即使是較為明確的概念,仍然經常包含一些本身缺欠明確界限的要素。”[3]當語言帶著這些特征進入到法律中,便可能使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未必總是十分明確,“特別是當法律規(guī)范所使用的概念與日常用語分離的程度較低時,法律概念就會產生擁有多重含義、即它與日常用語的含義區(qū)別不分明的現(xiàn)象。不僅如此,而且要使現(xiàn)存的法律對可能在未來發(fā)生的所有問題做出包羅萬象的規(guī)定,不使用相當程度的抽象概念是絕對不可能的。” [4]然而,除了數字概念可以被絕對精確化之外,抽象化的概念和專業(yè)術語并不能完全消除由語言特性本身所導致的歧義,以至于只要有理解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現(xiàn)誤解。比如我國《刑法》第152條走私淫穢物品罪中的“淫穢物品”、第246條侮辱罪中的“侮辱”等詞語,就沒有清晰的意義界限,它們是需要通過一定的思想觀念來理解的概念。雖然在一定的社會范圍內,語言共同體成員對大部分語言都能得到大致相同的理解,但是也不排除分享共同文化的人們可能會對同一詞語產生大相徑庭的感受。比如,一本裸體畫冊達到怎樣的程度就算是“淫穢物品”而不是“人體藝術”,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可見,文字意義的客觀性具有相對性,它對信息及價值的傳遞不是絕對“保真”的,在傳遞過程中,存在信息畸變和價值損耗的可能。一方面,在不同的價值觀的支配下,人們對同一詞匯的意義會有不同的感知;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語言的意義可能發(fā)生變化。因此,用語言表達的法律只能具有相對的確定性,永恒不變的立法者的“意圖”是不存在的。
第三,某些人類事務不具有適宜被精確描述的性質,當語言勉為其難地描述它們時,只能以一種模糊的、不精確的方式來表達。比如“侮辱”這種行為,就很難被精確地描繪。在我國《刑法》中,第237條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第246條侮辱罪,第250條出版歧視、侮辱少數民族作品罪,第299條侮辱國旗、國徽罪,第302條盜竊、侮辱尸體罪等條款中,都有“侮辱”一詞出現(xiàn)。但是,由于上述行為的犯罪對象、行為方式均不同,每一條法律規(guī)范保護的法益也不同,所以同一個“侮辱”在每一個條款中的意義并不相同,其具體的內涵必須根據每一條法律規(guī)范的調整目的來加以界定,并根據具體犯罪行為的具體表現(xiàn)進行“在場性”的解釋。另外,由于文本語言不具有對話處境的那種當下性,因此,文本指稱就不像口頭的指稱那么確定。“在文本中,直指指稱實際上被懸置起來。文本的指稱不再是直指指稱。”[5]比如過失殺人罪中的“人”,似乎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難,但事實上,具體的“張三”或“李四”可能更容易被精確描述,而要對抽象的“人”的概念進行精確描述卻是困難重重。于是在下列情況下,對“人”的理解就會產生爭議:當一個人的大腦已經死亡,但是血液還在循環(huán)流動時,他是人或者已經是尸體?當一個人在分娩陣痛開始后的一個確定的時間里,待產的孩子仍然僅僅是一個胎兒或者已經是一個人?這樣的問題是無法通過法律條文來預先準確地加以規(guī)定的。
參見: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5由于規(guī)則的一般性特征,法律只能在抽象的層次上使用概念,而抽象的概念過多地舍棄了事物的具體特征,因而其意義只能具有相對的確定性。
第四,如果我們所說的法律不只是紙面上的法律,而是生活中的法律,那么就不能只是在立法的意義上來談論法律的確定性或不確定性。在司法活動中,司法行為可以塑造法律的確定性,也可以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一般來說,司法所導致的刑法的不確定性主要有兩種致因:一是司法過程本身的性質,二是司法權力被濫用——后者屬于非正常的情況,所以我們這里只討論前一種致因。司法的基本職能在于按照法律的一般規(guī)定解決具體案件中的法律問題,并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判決。司法者所處理的是規(guī)范與事實之間的關系。由于規(guī)范是抽象的和概括的,而事實卻是具體的和生動的,要將一般性的法律規(guī)定適用于具體案件并得出妥當的結論,法官必須從事將抽象的法律加以具體化的工作。但是因為法律語言本身具有哈特所說的那種“開放結構”,而且案件事實總是千差萬別,法律具體化的道路就不可能只有一條。在多種可選擇的道路中,法官享有選擇的權力。因此儒攀基奇認為,貝卡里亞所謂“完美無缺的三段論”對許多案件是不適用的,因為刑法規(guī)則的運用,從來都不僅是簡單生活情境的抽象規(guī)則之下的一個小前提,而總是涉及至少兩個規(guī)則并且通常多于兩個規(guī)則。如果我們考慮到,現(xiàn)代刑法典中都有一些不同而且不協(xié)調的基本規(guī)定,例如,在一起不會重現(xiàn)的謀殺案中,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是不協(xié)調的,所施加的懲罰顯然是兩者的折中,并且允許法官運用其直覺;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每一條文通常包含兩個以上的要件,我們基于上述考慮將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防止司法專斷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參見:卜思天·M·儒攀基奇刑法——刑罰理念批判[M]何慧新,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05-206在司法活動中,對法律規(guī)則的解釋是無可避免的,“嚴格解釋法律”僅是程度問題,實際上無法做到真正的“嚴格”。比如,我國《刑法》第246條對侮辱罪的規(guī)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在此,“暴力”方法無論如何都不應擴大解釋到包括精英話語中的“語言暴力”。但是,“語言暴力”是否可以包括在該條所規(guī)定的“其他方法”中,則要看“語言暴力”的具體內容是否帶有強烈的“侮辱”色彩,而是否有“侮辱”色彩以及其強烈程度,則完全取決于法官個人的判斷。在理解法律的過程中,即使法官采取完全客觀的立場,合理的解釋結論也仍然可能不止一個,法官總是會面臨選擇。尤其是對于某些明顯帶有價值意味的概念,法官個人的理解完全有可能被帶入判決中,從而被定格為法律的意義。語言的意義就是在語言的具體運用中才相對地確定下來的,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語言才能被真正理解。但是由于立法者不可能與司法者獲得一種共時性的存在,總是先有立法,然后才有司法;所以,法律語言的含義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那里,常常是不一致的。對于需要解釋的法律語言,在被法院判決定格之前,它們的意義將始終處在不確定之中。有時,立法者認為他們已經將法律表達得十分清楚,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但是司法者仍然可能會對法律產生不同的、但并非不合理的理解,那么所謂立法者的“意圖”就只不過是法官個人的看法罷了。
第五,法律是社會中的法律,法律的內容是對社會需求的表達。社會生活因技術的進步、革新、傳播而不斷發(fā)生變化,人們的利益關系和利益需求也會隨之變化,旨在確認、保護和協(xié)調人類利益關系的法律則必須反映社會關系的這種變化。再者,社會的變遷也必然導致社會正義觀的變化,而“社會正義觀的改進和變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6],所以在一個變化的社會里,與正義問題密切相關的法律也不可能保持恒久的靜止不變。就刑法而言,社會的變化無論迅疾或緩慢,都會影響社會結構以及社會成員價值觀念的改變,由于此種影響,也足以導致改變社會的犯罪現(xiàn)象,并進而對作為犯罪行為制裁手段的刑法產生影響。參見:廖正豪刑法與社會變遷[G]//蔡墩銘刑法總則論文選輯(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5:48也就是說,社會生活變化的影響必然及于刑法之規(guī)定,導致刑法本身發(fā)生變化。因此,在“穩(wěn)定性”的意義上說,刑法的確定性也不能是絕對的。
由于以上原因,無論我們傾盡怎樣的智慧,我們所塑造的法律的確定性都必定是有限的,絕對的確定性或可預見性是不存在的。任何法律規(guī)定均為了適用于一般情況,當你將法律運用于特殊情況時,不可避免地總會留下一定的爭議余地。何況,語言上的缺陷以及遠見之不足都會在大多數的法律文本中造成曖昧不明的可能,特別是,現(xiàn)實生活中變化永無止境,法律跟不上變化。
參見:亞瑟·瓦茨爵士國際法治[G]//Josef Thesing,Winfried Jung法治法律出版社,2005:105即使是以成文形式存在的刑法,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不確定性。包括刑法在內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達到法治的理想。只有承認這一點,我們才能看到法治所面臨的困境,并進而認識到,再完美的法律也需要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在法律規(guī)定不明確之處,人的因素仍然可能而且有必要發(fā)揮作用。也就是說,法治無法從根本上排除人的主觀方面的影響,法律約束下的權力仍然有被濫用的可能。不過,法律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必須被恰當地估價。在法律的相對確定性與相對不確定性兩者之間,相對確定性是主要方面,相對不確定性則是次要方面,正因如此,理性化的法律制度既難以完全排除司法的自由裁量,又難以把自由裁量限定在一個非常有限的范圍之內。參見:鄭成良論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個問題[J]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5(6)在塑造確定性的同時,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也必須容納一定的靈活性。(二)刑法之確定性的背反性
一般來說,只有當法律具有確定性時,才能實現(xiàn)法治的基本價值。然而,正如美國法學家梅利曼所說的那樣,“確定”是抽象而重要的法學概念,它就像一盤國際象棋中的皇后,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動。梅利曼舉例說,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統(tǒng)治時期,法西斯主義者企圖把法變成集權國家的工具,但是法學家們以保持法的“確定”為由,成功地抵制了這種企圖。法西斯主義倒臺建立了共和國后,許多要求對意大利法律制度進行改革的主張,又一次遭到法學家們的反對,理由也是為了維護法的“確定”。(參見: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49)法律的確定性在維護法治的同時,它也會產生某些與法治精神相悖逆的結果,這是追求法治必須面對的問題。
第一,法治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其主要意義在于保證法律在全社會內的一體適用,以實現(xiàn)公平。但是,法律的普遍性要求意味著,法律規(guī)則必須具有足夠的概括性、抽象性,通常,立法只能考慮同類事物的一般情況,而無法顧及每一事物的特殊情況。雖然每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情況,但是,“法律只能根據具有典型意義的、經常發(fā)生的情況,將案件進行分類。法律規(guī)則中人的分類、由法律規(guī)定其后果的行為的分類,所用的方法,都是從普遍情況中分離出具體的特定因素。這些因素都被視為基本事實。法律只關心基本事實;其他的一切都因與法律規(guī)則的使用無關而被置之不理。”[7]博登海默認為,正是法律的這種一般性規(guī)則的形式結構,使得法律具有僵化性或剛性特征。參見: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05法律必須以少數的、確定的規(guī)則去面對社會生活無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而法治的形式化要求又或多或少強化了法律確定性的價值。于是,當一般性的規(guī)則被機械地適用于具體案件時,勢必造成同一規(guī)則適用于不同案件的情形發(fā)生。因為即使是同類案件之間,也存在千差萬別的情形
,有時,從表面上看兩個案件的情況是一樣的,但實際上兩個違法者的“可罰性”具有很大差異;此外,兩個相同的案件中,違法者的個人情況也可能大不相同。對這種表面上相似或相同的案件,如果以維護法律的確定性為由而作完全相同的處理,反而不能有效地實現(xiàn)公平。尤其是對刑法來說,法律的規(guī)定往往十分明確,刑事法官在法律有授權的情況下才擁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刑法的形式公平與實質正義之間的張力更顯突出。此外,還可能存在一種較為極端的情形,那就是拉茲所說的,“許多形式的專制規(guī)則與法治相符。在沒有違背法治的情況下,統(tǒng)治者可以促成來源于貿然或利己念頭的一般規(guī)則”[8]。若此,則法治無異于專制權力的工具,就連納粹暴政也可以披上法治的外衣。
第二,為了追求法的安定性,人們總是希望法律的語言盡可能精確。但是,對法律而言,精確并非總是好事。相對于日常語言,抽象的專業(yè)詞語可能更加精確。但是,過度抽象化的法律概念由于將它所描述的對象的特征舍棄過多,一方面會使非法律專業(yè)人士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另一方面,其高度的概括性也可能會忽略事物的某些重要特征,反而會削弱自身對對象的解釋能力,難以應對復雜的社會生活。正如考夫曼指出的,語言上的極端精確,其只能以內容及意義上的極端空洞為代價。僅以抽象化的概念形成構成要件,是難以適應規(guī)范社會生活的需要的,司法機關難免要突破那些過分狹隘的概念,那么就會發(fā)生對司法失去控制的危險。參見: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7由于抽象的法律概念需要法官作規(guī)范性評價,這樣,在法律規(guī)范被適用的過程中,就會融入法官個人的價值判斷,如此一來,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界限究竟何在,又成為尖銳的問題。
第三,法治一方面要求法律具有一般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律具有明確性;但是,一般性和明確性嚴格說來是兩種相互矛盾的要求,它們對規(guī)則的形成具有相反的意義。規(guī)則越是抽象和一般,其適用的范圍就越寬,所以一般性要求的目的是使法律規(guī)范能夠適用于更為廣泛的情形;而規(guī)則越是明確和具體,其適用的范圍就越窄,所以明確性要求的目的是為了將法律規(guī)范的效力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因此,這兩種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的特征,當它們被過度強調時,都有可能導致與法治目的相背離的結果:當法律的一般性太強時,其效力邊界將比較模糊,可能導致法律適用范圍過大或者喪失可操作性;而當法律太過具體和明確時,其只能適用于極為狹窄的情形,不符合法律的普遍性要求,甚至產生法律處遇上的不公平對待。第四,無論一種法律的規(guī)范體系多么嚴密,其規(guī)范的數量都是極為有限的,再加上規(guī)范的一般性特征,必然有大量的需要其調整的生活現(xiàn)象不能被現(xiàn)有的規(guī)范所覆蓋。在民法中,民法基本原則以極強的規(guī)范性大大拓展了特定條款適用的空間,類推適用、法律漏洞補充、法律續(xù)造等法律方法被廣泛采用,因此即使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也可以通過靈活的法律技術納入規(guī)范的調整之下,沒有人會覺得這違反了法治原則。但是在刑法中,由于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和處理,都必須依據刑法現(xiàn)有的規(guī)定作出,對于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不得定罪處罰。也就是說,在刑法中,法律的分散性、片段性和不完整性必須被認為是一種合理的現(xiàn)象,司法者無權對刑法的漏洞進行填補。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堅持雖然可以維護刑法的確定性,實現(xiàn)刑法保障人權的價值,但是這也同時意味著,某些值得由刑法保護的社會利益有可能被刑法忽略。當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發(fā)生,而此種行為是立法者所未曾預料到的時,為了維護法治,我們就必須忍受此種行為所帶來的損害。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從其他犯罪人的角度看,可能會產生刑法本身有失公平的看法——因為他自己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而另一個人實施了同等危害程度的行為,卻因為法無明文規(guī)定而免受追究。而如果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在此種情況下,他也可以認為刑法沒有為其提供平等的保護,其報復情感將難以平復,從而懷疑刑法的公正性。可見,刑法要維護自身的確定性,就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社會正義,或者反過來說,刑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社會正義,而這與法治是相矛盾的,因為實現(xiàn)社會正義無疑也是法治的目的之一。
第五,法律一經制定,就應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這是法治的要CHqdGMXERNFCTCOb4GGSXg==求,也是維護法律確定性的需要。博登海默認為,由于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guī)則體系,其本身帶有一種天然的保守傾向。一旦法律制度設定了一種權利和義務的要素,那么為了自由、安全和預見性,就應當盡可能地避免對該制度進行不斷地修改和破壞。但是,當業(yè)已確立的法律同一些易變且重要的社會發(fā)展力量相沖突時,法律就必須對其穩(wěn)定性要求付出代價。參見: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02尤其是對于特別強調確定性的刑法來說,更是不能頻繁和隨意地進行修改,以維護安全價值。但是一如其他法律一樣,刑法也必須面對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尤其是在瞬息萬變的現(xiàn)代社會,新的犯罪類型不斷出現(xiàn),舊的犯罪類型也會呈現(xiàn)新的特征。而法律的穩(wěn)定性要求必然使得刑法無法立刻對此做出反應,相對于其他法律來說,博登海默所說的“時滯”(time lag)問題在刑法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司法者無權將刑罰適用于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情形,立法者也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規(guī)范。所以當新型的危害行為發(fā)生時,由于現(xiàn)行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則無論其危害后果多么嚴重,都無法使其承擔刑事責任。在立法機關修改或補充現(xiàn)行法律之前,社會必須為刑法的穩(wěn)定性付出代價。
基于以上原因,刑法之確定性雖然是法治對刑法的基本要求,但是,它有時卻也會產生與法治要求相悖逆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法治不僅包含著許多形式性的要求,而且也包含著某些實質內容,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并不總是統(tǒng)一的,有時它們是相互矛盾的。刑法之確定性主要是形式法治的要求,刑法之確定性在某些情況下與法治的悖逆實際上反映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的沖突,這是法治本身的悖論,也是當代法治理論所思考的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三)法治的困境與刑法之靈活性的必要性
由于法治是以全社會、特別是政府對法律的遵守為基礎的,而法律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因此,盡管法治被人們描述成一種理想的社會治理模式,但是它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困境:(1)人類的理性無法使法律達到法治所要求的完美程度,法律只能具有相對的確定性,或者說法律中也包含著許多不確定性;因此,法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xiàn),人們難免心存疑慮。人們之所以崇尚法治,是因為相對于人的統(tǒng)治來說,法的統(tǒng)治具有很多優(yōu)越性,它可以避免人的統(tǒng)治的恣意性和不確定性,滿足人們對安寧與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法治必然也不是盡善盡美的。(2)法治追求的首先是形式正義,因此,它要求法律具有確定性;但是,法治的形式性要求卻常常會阻礙實質正義的實現(xiàn),為了維護法治所要求的法律的確定性,人們不得不犧牲某些值得承認和保護的價值。因此,法治究竟是否真的有益于人類,也引起人們的諸多困惑。
或許,正是因為以上兩個原因,法律才不得不在強調確定性的同時,也容納了一定的靈活性。民主制度以及民主制度中的法律必須跟完全不信任抽象原則的人打交道。在處理大量的案件時,法官的許多判決必須在明顯棘手的社會不同意見面前、在廣泛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迅速地做出。因此,運轉良好的法律制度一般都會采用某種特殊的策略,以在社會不同意見和多元化之間得到穩(wěn)定和一致。參見:凱斯.R.孫斯坦律推理與政治沖突[M]金朝武,胡愛萍,高建勛,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90這種“特殊的策略”必然是在規(guī)則與對規(guī)則的變通之間的妥協(xié)。美國現(xiàn)實主義法學代表人物,曾經領導、組織起草《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的盧埃林認為,法律是實現(xiàn)社會目的的手段,其功能在于引導人們的行為。由于社會的變化總是快于法律的變化,因此,為了實現(xiàn)指引和再指引功能,同時維持對社會重新定位做出反應時所必需的靈活性,成文法必須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能適應日益變化的關于正義的社會觀念[9]。即便是對自身的確定性要求很高的刑法,亦無法完全排除靈活性,亦需要在某些情況下進行妥協(xié)。
首先,刑法具有法律的典型特征,即它是以類型化的規(guī)范方式調整社會生活的,所有的刑法規(guī)范,無論其文本表達多么明確,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抽象性和一般性,這決定了其適用不可能依形式邏輯的方法完成。要將抽象、一般的刑法規(guī)范適用于具體案件,法律首先要提供一種可以將規(guī)范加以具體化的途徑。因此,刑法規(guī)范體系終究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它必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拉倫茨認為,一個只依據形式邏輯的標準所形成的體系,其將切斷規(guī)范背后的評價關聯(lián),因此也必然會錯失法秩序固有的意義脈絡,因后者具有目的性,而非形式邏輯所能涵括。對于法學以及“實踐性的哲學”而言,只有“開放”的,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可變”的體系,永遠不會圓滿完成而必須被一再質疑的體系,它們才能清楚地指出法秩序“內在的理性”、其主導性的價值及原則。參見: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9-50既然立法者無法制定出一種可以應對未來一切可能的法律,那么他就必須通過規(guī)范體系的開放結構,為司法者留有靈活適用法律的余地,以便面對具體的案件時,可以在法律的形式正義與個案中的實質正義之間尋求平衡。
其次,面對并非完美無缺的法律,司法者當然不可能只是機械地將法律的規(guī)定適用于具體案件。龐德認為,分權理論的教條試圖將司法判決過程變成自動化的觀念是不能經受今天所有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嚴格審查的。今天,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甚至堅持法律的一些制度定會發(fā)展,法律原則相對于時間和地域不是絕對的,而且司法理念論并不比拜占庭時代的觀念走得更遠,法律注疏僅僅“就是根據既定的真正注疏規(guī)則來確定立法者的實際意圖”的虛構應該被摒棄。無論法學家限制審判職能的準機械理論是多么完美,司法造法的過程在所有的法律體制中總在進行而且會一直進行下去。 參見: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M]唐前宏,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1一方面,法律須經解釋方可適用,而解釋活動的實質就是對僵死的法律條文進行活化處理,這本身就已經是對規(guī)則的靈活運用。雖然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具有明確性,但是即使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在具體適用時也需要進行解釋。正如拉倫茨所說,假使以為只有在法律文字特別“模糊”、“不明確”或“相互矛盾”時才需要解釋,那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則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釋。需要解釋本身并不是一種缺陷,只要法律、法院的判決或契約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號語言來表達,解釋就始終是必要的。參見: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85-86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生活的無限復雜和變動不居,每一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要在個案中實現(xiàn)具體的妥當性,司法者就必須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比如,根據某人的行為,我們或許可以較為確信地認定其構成了故意傷害罪;但是,要認定其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故意傷害罪,卻無法做出精確的評估。法70XU33NyedFaijj3WjVYBg==律上,可以根據“輕傷”、“重傷”、“致人死亡”等認定標準來選擇法定刑,但是“輕傷”、“重傷”這樣的認定標準本身就是一種相對概括的標準,很多時候,難免有兩可的情況出現(xiàn);而且,同樣是“輕傷”,或者同樣是“重傷”,也仍然存在量的差異。此時,就需要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合理的判斷,而且,要在個案中實現(xiàn)罪刑均衡,具體的量刑權也只能賦予法官。
最后,如果我們可以把刑法修改與補充看成是刑法最大限度的靈活性,那么刑法發(fā)展的必要性也可以作為刑法需要靈活性的一個理由。刑法雖然應當保持穩(wěn)定,但是卻不能永遠不變。這是因為,法律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而社會生活處在不斷變化和發(fā)展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原來能夠適應社會生活需要的法律必然呈現(xiàn)出滯后性,不能對變化了的社會關系作出有效的調整。此時,就不能以維護法的安定性為由,拒絕對法律進行必要的變革。雖然司法機關只能根據刑法的明文規(guī)定處理,但是在理論上,立法機關卻始終有權根據社會的需要對刑法進行修改和補充。
法律的靈活性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克服法律的僵化性、剛性及滯后性帶來的消極后果,使法律適用的結果更符合正義要求。“如果一種以充分、公正地審理相標榜的體系不能維護實質正義的那些重要的權利要求,那么公平觀就會遭到侵犯。”[10]所以,致力于維護正義的法律必定要求在某些情況下超越自己的形式邊界,去尋求更具內涵的合理性。從人們關于法治的討論看,法治的觀念常被區(qū)分為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一般來說,形式法治強調要有規(guī)則,并且人們能按規(guī)則行事;實質法治則強調保障個人自由,限制國家權力。顯然,這兩個方面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因為要保障個人自由和限制國家權力,規(guī)則的制定和遵守也是基本的前提。因此,無論是形式法治還是實質法治,都需要法律具有確定性。但是,實質法治的內容似乎又并不僅僅在于保障個人自由和限制國家權力,它還應該致力于實現(xiàn)社會公正,只有為了實現(xiàn)社會公正,法律的靈活性才可能獲得合理的根據,就此而言,法律中的靈活性因素也是符合法治要求的。
在刑法領域,罪刑法定原則的變遷最直接地反映了法治觀念的進步。自19世紀以來,罪刑法定原則經歷了一個由形式(絕對)罪刑法定到實質(相對)罪刑法定的發(fā)展過程,大陸法系的刑法觀念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初的只強調罪刑法定的形式側面,轉變?yōu)椤皩⑿问絺让媾c實質側面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形式側面與實質側面成為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統(tǒng)一要求”[11];從對刑法確定性的絕對強調,轉變?yōu)閷ψ镄谭ǘㄟ@一剛性原則的相對軟化,在確定性中注入了靈活性的基因。由此,罪刑法定不再只是一項致力于保障形式正義的原則,它同樣也是一項追求實質正義的原則;在相對主義的罪刑法定原則之下,刑法不僅需要具有足夠的確定性,而且也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我們今天的刑法制度中,一個靈活性的機制顯然是存在的。
三、刑法之靈活性的內涵:與不確定性的區(qū)別
雖然“刑法之靈活性”和“刑法之不確定性”都是相對于“刑法之確定性”而言的,但是,它們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從表面上看,所有能夠帶來靈活性的制度因素似乎都能夠導致不確定性;然而透過表面的相似性,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刑法之靈活性”和“刑法之不確定性”之間的根本性差別。
人們之所以容易把法律上的靈活性與不確定性混同,是因為二者常常產生于相同的法律生產要素。比如模糊性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是無可避免的事情。由于模糊性是語言固有的一個特征,而立法者又不得不用語言來表達法律,所以當立法者絞盡腦汁想明確地表述規(guī)范時,表達工具本身已經將模糊性帶進了他們的表達。由于這種模糊性,由日常語言所構成的法律概念就會呈現(xiàn)出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不過很多時候,立法者也可能有意識地采用一些模糊性的立法技術和策略,為司法者的價值判斷留下空間,以解決作為一般化標準的法律與社會生活的具體性之間的矛盾。比如規(guī)范性法律概念的使用,以及原則性規(guī)定、概括性規(guī)定、彈性條款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立法技術要素。這樣,負載在法律語言上的模糊性就是一種正常的現(xiàn)象。
然而,由于法律需要確定性,尤其是刑法,對確定性的要求更高,我們仍然有必要對兩種不同的模糊性作出區(qū)分。如果我們把“模糊性”看成是一個中性概念,那么就可以這樣來界分“刑法之靈活性”和“刑法之不確定性”:(1)刑法之靈活性,是指刑法制度要素中“可把握的模糊性”,這種“可把握的模糊性”通常是制度設置中的有意識的產物,它們服務于一定的法律目的,而且法律的目的不會被其模糊性所遮蔽。(2)刑法之不確定性,則是指刑法制度要素中“不可把握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