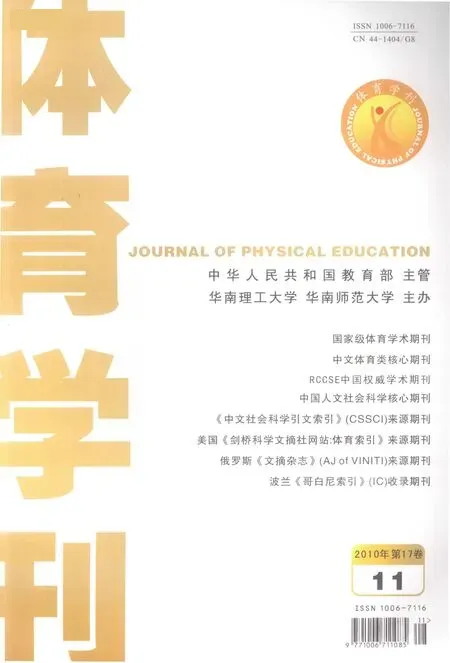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法律性質及其在中國的適用問題
裴洋
(北京師范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5)
·體育社會科學·
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法律性質及其在中國的適用問題
裴洋4
(北京師范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5)
對于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法律性質,國內觀點有國際習慣說、其他國際法淵源說、國際慣例說和合同說等不同觀點。但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因其在實踐中的作用及影響力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世界反興奮劑規則》和“奧運停戰”已成了國際習慣,大多數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屬于國際慣例,《奧林匹克憲章》等其他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則僅具有合同性質。作為國際慣例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可在中國法院得到直接適用,屬于涉外合同性質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則必須由法院依據可適用的法律來判斷其有效性。
體育法;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奧林匹克憲章;世界反興奮劑規則
在競技體育日趨全球化的今天,國際體育組織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它們不僅制定全球統一的體育比賽技術規則,掌握著國家隊、俱樂部或運動員能否參賽的準入資格決定權力,還對不服從其管理者施以各式各樣的處罰措施。國際體育組織行使如此之大的權力,依據的是由其制定的各種規章。國際體育組織的這些規章被它們的成員以及體育運動的參與者所嚴格遵守,就如同一國法律被其全體公民遵守一樣。因此,以下問題引起了體育法學研究者的濃厚興趣: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具有何種法律性質?當它們和國家法律發生沖突時,效力如何?
1 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法律性質
無論是中國或是其他國家的立法中,均未對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法律性質或法律地位,以及當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同國家立法發生沖突時,應以何者為準作出明文規定。而在司法實踐中,各國也存在不小的差異,至今未有較為一致的做法。比如,英國法院曾經在判例中指出,有關國家的足協所引用并認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足聯章程》不能作為自己抗辯的理由;而比利時的一個法院則認為國際體育運動規則的效力高于國內政策和法律[1]。于是學者們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目前國內學者對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法律性質存在4種理論主張:
1)國際習慣說。有學者提出,在國際體育領域中,國際奧委會是核心機構,它的規則與規章和《奧林匹克憲章》一起構成了廣泛被認可的國際體育習慣法[2]。
2)其他國際法淵源說。權威的國際法學著作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不能被認為任何時候必然是國際法淵源的詳盡陳述[3]。國際組織的決議作為首選的“其他國際法淵源”,已得到不少人的強烈支持。有學者提出,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也屬于國際組織的決議,因此構成國際法的淵源。持該主張的學者認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組織體系制定的有關規范和條例,按照其淵源效力的大小,可以分為《奧林匹克憲章》、其他組織的章程、國際奧委會各專門機構的規范或章程、運動技術或競賽規程等4類。這幾類規章在其各自范圍內具有約束力,均構成國際體育法的淵源[4]。
3)國際慣例說。有學者認為,體育組織的規范類似于商事領域的商事慣例,理應屬于國際體育法的淵源。其理由在于:“盡管國際體育組織是屬于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其規范不具有法律的性質,其規范的實施不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但是對有些體育爭議的裁決所適用的則主要是這些體育組織的規范……更主要的是這些規范,尤其是國際體育組織的規范在國際體育界已得到廣泛的認可,對于從事體育運動的人員和體育組織來講,不遵守這些規范有時就不可能參加有關的比賽,故這種強制性的規定又使這些規范具有與法律類似的拘束力。”[5]
4)合同說。該學說認為體育行會的章程是體育行會與其成員之間的契約,是該行會制定并遵守的用來決定并指導其內部構造及運行的規則[6]。體育行會的自治規章應當符合國家法律的規定,即在效力層次上,國家法要優于體育行會的自治規范。體育行會的自治規范要具有法律效力,還需要國家法律或政府決議在事先或事后對它們予以授權或確認,否則只具有當事人之間契約的效力,不具有法律規則的效力。
以上4種理論主張中,筆者首先不能贊同“其他國際法淵源說”。第1,國際組織決議的法律性質確實已在國際法學理論界得到了廣泛討論,但必須說明的是,此處的“國際組織”指的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更明確地說,國際組織決議指的是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國際體育組織作為非政府組織,其決議顯然不在此列。第 2,國際組織決議作為獨立的國際法淵源的地位尚未獲得確認。到目前為止,普遍認為國際組織決議的法律效力只是來自于傳統國際法淵源的,即國際組織決議要么是作為國際公約的初步發展階段,要么是作為形成國際習慣的物質要素或心理要素之一。因此,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也就不能獲得相應的國際法地位。其他3種理論主張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又無法用其中任一理論主張來囊括所有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考慮到《奧林匹克憲章》、《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章程以及其他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在實踐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差異,在對上述3種理論主張進行分析時,還必須注意將這些不同的文件區分開來。
1)作為國際習慣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
國際習慣是國際法主體認為有法律約束力并按其行事的實踐[7]。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規定,“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從該定義分析,傳統上一般認為國家的長期持續或反復的實踐(即物質要素)和國家在主觀上認為有關行為,是出于法律上的強制要求(即心理要素)是習慣國際法規則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如果沒有國家實踐不可能形成習慣;沒有法律確信,國家實踐所形成的不會是習慣而只能是慣例或者國際禮讓等非法律的規則[8]。
(1)《奧林匹克憲章》。
顯然,盡管國際奧委會在國際體育活動中處于中心地位,但國際奧委會目前尚未成為公認的國際法主體,對《奧林匹克憲章》及國際奧委會的其他規章進行實踐的是各國國家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等,而不是國家。因此《奧林匹克憲章》尚不具備國際習慣所必須的物質要素。不僅如此,目前尚無足夠證據表明,世界各國已把《奧林匹克憲章》視為對自己有拘束力的法律來遵守。可見,《奧林匹克憲章》也不具備國際習慣所必須的心理要素。因此,《奧林匹克憲章》目前距離國際習慣還很遠。至于其他國際體育組織的章程就更難成為國際習慣了。
實際上從《奧林匹克憲章》的具體內容來看,除去有關奧林匹克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的簡要敘述外,主要是一部對國際奧委會的內部結構及奧運會舉辦條件進行詳細規定的文件,并無意對整個體育領域內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加以確定。因此在目前,《奧林匹克憲章》還遠遠達不到構成一個跨國體育憲法的要求[9]。
有趣的是,在《奧林匹克憲章》尚未取得國際習慣地位時,并未規定在《奧林匹克憲章》里的“奧林匹克休戰活動”似乎更接近于一項公認的國際習慣法規則。2007年10月31日,第62屆聯合國大會10月31日一致通過由中國提出、186個會員國聯署的《奧林匹克休戰決議》,號召聯合國成員國應單獨或集體地采取積極行動根據國際奧委會的要求遵守自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的7天到奧運會閉幕后的第7天休戰,并應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宗旨、原則,和平解決所有的國際爭端。這是自1993年以來,聯合國大會第8次通過《奧林匹克休戰決議》。
聯合國大會在每屆奧運會前都一致通過《奧林匹克休戰決議》可以表明,世界各國都將奧運會召開期間停止使用武力,作為一項國際法所要求的義務來看待。盡管要在當今世界上實現完全消滅戰爭和不使用武力還只是美好的理想,但這畢竟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實踐。該決議在聯合國大會表決時是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的,在奧運會期間使用武力的國家也從未公然對該決議表示過反對,因此,“奧林匹克休戰”已經構成了一條國際習慣法規則。
(2)《世界反興奮劑條例》。
在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中,《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簡稱《條例》)似乎是特例,因為其制定者是依據瑞士法成立的私法基金會——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而該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一半來自政府間組織、各國政府或公共當局,另一半來自奧林匹克運動系統。
作為一個民間機構,WADA顯然不具備國際立法職能,但從其章程以及《條例》的上述宗旨來看,它成立目的實際上是為了統一世界各國反興奮劑規則。《條例》的第1部分“興奮劑控制”對使用興奮劑的定義、興奮劑違規、使用興奮劑的舉證、禁用清單、參加公正聽證會的權利、對個人的處罰、集體項目發生違規的后果、對體育團體的處罰、上訴、保密等都有非常詳盡、明確的規定,從形式上看已經具備了一部反興奮劑法典的所有要素。因此,可以說《條例》實際上是一部“示范法”。各類國際組織制定示范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建議各國在制定其國內法時予以考慮和適用。有的國際組織也制定為公約所使用的示范條款,以供未來公約或修改現行公約時使用[10]。
然而,《條例》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等示范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其第 3部分“責任與義務”對簽約方施加了制定、實施與《條例》一致的反興奮劑政策和規則的義務。《條例》下的簽約方包括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國家奧委會和殘奧會、重大賽事組織機構和國家反興奮劑組織。此外,《條例》還試圖將尚不在任何政府或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管轄范圍內的職業體育聯盟也納入其版圖。對于簽約方而言,盡管簽約是非強制性的,但不執行《條例》的后果卻是嚴重的,比如喪失國際奧委會對其資格的認可、部分或全部終止奧林匹克資助、無權或被禁止得到在該國家舉辦國際賽事的候選資格、中止國際賽事等。在體育運動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遭受這些后果,對于各類體育組織的運轉和工作幾乎是致命的。因此,事實上世界各大體育組織及作為其成員的各國家體育組織,都已按《條例》的規定簽約并嚴格執行其規定。
更具重要意義的是,《條例》第22條“政府的參與”規定各國政府對本條例的承諾,將通過簽署《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哥本哈根宣言》(簡稱《宣言》),批準、承認、通過或加入《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國際公約》(簡稱《公約》)來實現。如果某國政府未能完成該工作,將招致無權申辦賽事、收回其在 WADA的辦公室和職位、中止國際比賽等后果。《條例》做這樣的規定是由于多數國家的政府不能參與簽署這類非政府協議,因此WADA為了使各國政府也能遵守和執行《條例》,并不要求它們成為《條例》的簽約方,而是要求它們成為《宣言》或《公約》的當事方。而《公約》不僅在多個條款中不厭其煩地提及《條例》,如根據《條例》的內容作出解釋(第2條)、遵照《條例》中確定的原則(第 3條)、違反《條例》的后果(第11條)、鼓勵根據《條例》進行興奮劑控制(第 12條)、依照《條例》為興奮劑檢查提供便利(第16條)等等,更在第4條明確《公約》與《條例》關系:“為了協調各國和國際間開展的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活動,締約國承諾遵守《條例》中確定的原則,并將其作為本公約第5條中提出的各項措施的基礎……”。盡管該條第3款明文規定《條例》并不約束締約國,但這僅僅是說《條例》并非國際條約而已,并非意在強調《條例》不具有國際法上的意義。結合《條例》和《公約》的出臺背景及具體內容,發現《條例》通過和《公約》建立有機聯系,將對國家本無法律約束力《條例》下的義務巧妙地轉化成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下的義務。截至2010年7月,已有多達143個國家批準或加入了《公約》。此外,各國還按照《公約》的要求,在《條例》的指引下頒布或修改本國的反興奮劑法律,以便于在國內具體實施反興奮劑措施,維護體育競賽的公平競爭。
以上事實表明,《條例》的具體規定不僅為世界上體育運動各主體普遍遵守和實施,同時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支持與保障(物質要素),并且各國之所以做出支持與保障是因為它們普遍將其視作一種法律上的義務(心理要素)。據此,研究認為《條例》已不僅僅是一部“示范法”性質的國際慣例,它已經具備了一項國際習慣所必須的物質要素和心理要素,因而已經是一項國際習慣法規則。
2)作為國際慣例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
大多數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都屬于國際慣例(international usages)的范疇。國際慣例和前述國際習慣在日常生活中常被混用,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國際慣例僅指各國長期普遍實踐所形成的尚不被各國認可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通例”或“常例”,換句話說,國際慣例的成立只需“物質要素”而無需“心理要素”。國際慣例主要見于國際商貿實踐,因此又被稱為國際商事慣例。這些商事慣例在國際上被長期反復使用,具有確定的內容,可用以確定交易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構成當事人交易行為的準則。為了便于使用,商人和一些商人組織逐漸把這些慣例規則化,通過編撰制定為明確的系統規則[11],如國際商會制訂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等。盡管這類國際商事慣例純屬“任意性規范”,只有經當事人明確加以采用于有關的交易或合同中,才能起到約束當事人和法院的作用,但是在各國的民商事立法中,乃至在國際民商法條約中,都有大量的任意性規范存在,絕非僅由強制性規范所構成。它們或者在經當事人明確加以采用于有關的交易或合同中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或者只有在當事人未明確排除其適用時才能起約束的效力,它們甚至還允許當事人對法條的規定作出允許的減損或補充[12]。
由此可見,國際慣例具有幾個顯著的特征:第1,專業性。國際慣例一般適用于某些特定的國際經貿活動領域。第 2,自治性。國際慣例并非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而是由從事特定商貿活動的商人或商人組織制定,并且被他們在商貿活動中普遍遵守。第 3,契約性。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拘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于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13]。同樣,從各國普遍實踐來看,國際商事慣例在效力上高于國內法的任意性規范而低于國內法的強制性規范。
通過比較發現,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也有這些特點,只不過其適用的領域是國際體育運動而已。首先,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只規制特定體育項目的組織及規定具體的運動法則。其次,國際體育組織是由從事該特定體育項目的各國體育協會組成的,其規章反映的是對該項目負責任的機構及該項目的參與者的意志,并且在實施過程中得到普遍和嚴格的遵守。再次,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只能約束自愿加入該組織的成員及以“事實契約”方式受其規章管轄的俱樂部、運動員、教練員等體育競賽參與者,未以任何方式接受國際體育組織規章者當然不受其約束。
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國際慣例性質,也可從國際體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在普通仲裁程序和上訴仲裁程序實體問題法律適用的對比中看出來。CAS的《體育仲裁規則》第R45條是關于普通仲裁程序中法律適用的,它規定“仲裁庭將根據當事人選擇的法律規范來裁決爭議,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則適用瑞士法。當事人也可以授權仲裁庭根據公允及善良原則來做出裁決。”《體育仲裁規則》第R58條是關于上訴仲裁程序的,其規定“仲裁庭將根據當事人選擇的可適用的規章和法律規范來裁決爭議。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則適用爭議所涉及的體育聯合會、體育協會、體育組織所在地的國內法或仲裁庭認為應適用的法律規則。”盡管上述兩條都允許當事人選擇法律的適用,但普通仲裁程序中當事人只能選擇法律規范,而上訴仲裁程序中當事人除了可以選擇正式的法律規范,還可以選擇可適用的規章,此處的規章就是指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別就在于,普通仲裁程序解決的一般是商事性糾紛,難以適用國際體育組織的規章,而上訴仲裁程序解決的主要是國際體育組織與其成員或受其管轄者之間的管理性糾紛,其規章自然有了適用的空間。上述CAS對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適用方法同國際商事仲裁中對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是類似的。
3)作為合同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
除了上述符合國際習慣和國際慣例構成要求的國際體育規章外,其他的國際體育規章就應屬于合同范疇了,其中也包括《奧林匹克憲章》。比如,參與奧運會舉辦工作的法律權威人士就曾指出“根據申辦報告和主辦城市合同,北京奧組委有義務遵守《奧林匹克憲章》和奧林匹克慣例。盡管國際奧委會是一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奧林匹克憲章》也不是政府間國際條約,但是,北京奧組委既然做出了承諾,就應當履行相應的義務。”[14]可見,即使在奧運會舉辦方看來,遵守《奧林匹克憲章》并非因為它具有法律效力,而是誠實履行合同的要求。另外,上文中出現的所謂“奧林匹克慣例”只不過是國際奧委會對每屆奧運會主辦方的一些統一要求,亦屬合同義務范疇,并非前述法律意義上的“國際慣例”。因此,實踐當中各奧運會主辦國在遇到本國法律、同《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奧委會有關主辦奧運會的特殊規定沖突時,通常都不會以修改本國法律為代價來滿足國際奧委會的要求,而是在實踐中采取靈活的變通措施在兩者間尋求平衡。
另外,或許有人會提出,對奧林匹克標志給予特殊保護可能已超出合同要求的范疇,構成了更高層次的法律規范,比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1981年通過了《保護奧林匹克標志內羅畢公約》。對此筆者不敢茍同。首先,該公約使各締約國承擔的保護奧林匹克標志的義務僅僅是原則性的,至于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的界定、商業目的的含義、侵權的救濟措施等問題均未涉及,通通留待締約國通過國內措施來解決。其次,該公約的締約國數量到目前僅為47個,且多為發展中國家,總體而言各國對該公約的接受程度不高。再次,典型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表明,同普通商標的法律保護相比,對奧林匹克標志的法律保護并無多少特殊之處,各國司法機關對待奧林匹克標志的態度目前仍處于摸索階段,并未形成較為一致的處理政策或方法[15]。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對奧林匹克標志給予特殊保護,仍主要是奧運會主辦國根據主辦合同承擔的義務,并非是國際慣例,更不構成國際習慣。
2 中國法院對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審查
從收集的資料來看,中國法院迄今未曾受理過有關審查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效力的案件。其原因有:
第 1,大量體育糾紛是在體育行會內部解決的,各方當事人不愿意或自認為不能將糾紛以提交法院訴訟的方式解決,從而法院也沒有機會對體育組織規章(既包括國內體育組織規章,也包括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效力作出判定。例如中國足球協會以往已多次拒絕將涉及其管轄事項的糾紛提交訴訟解決,這種做法雖受到了多方抨擊,但目前適用的2005年版《中國足球協會章程》仍要求其會員協會、俱樂部及其成員保證不得將有關足球行業內的爭議提交法院,而只能向足協內部的仲裁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等機構提出申訴,違反這一規定將受到足協的處罰。
第 2,法院系統受到傳統的司法不介入體育內部糾紛觀念的束縛,不愿受理體育運動當事人(尤其是受到體育組織處罰的當事人)提起的訴訟。特別是 1995年開始施行的《體育法》第33條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直到目前,國務院仍未出臺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中國的體育仲裁制度仍未建立起來。這一狀況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國際體育組織的章程不可能交給仲裁庭來審查,另一方面法院因上述第33條的存在而進一步為自己不對體育糾紛行使管轄權找到了依據。2001年10月,中國足協以長春亞泰俱樂部嚴重違紀為由給予其嚴厲處罰。亞泰俱樂部及其教練員、球員不服中國足協的處罰決定,以其為被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以原告提起的行政訴訟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受理條件為由,裁定不予受理。于是亞泰俱樂部又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上訴中,亞泰俱樂部提出:“《國際足聯章程》屬于國際民間協會規章,不屬于我國人大批準和通過的國際公約和條約。如果與我國法律發生沖突,只能以我國法律為準。”[16]可最終該案不了了之,法院沒能對《國際足聯章程》效力問題作出認定。
雖然中國法院對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審查尚未付諸實施,但既然國際體育組織規章一般來說構成了國際慣例,這可以在考察中國法院適用國際慣例的實踐狀況基礎上,探究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應獲得的待遇。
《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依照本章的規定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結合該法其他條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可得出兩個結論:第 1,國際慣例在中國只起到補充法律漏洞之用。甚至有學者指出,國際慣例只是作為中國涉外民事立法正式淵源之外的“替補淵源”,確言之,是正式法律淵源中的法律漏洞的補充工具[17]。第2,在中國,國際慣例的適用方式有兩種:一是直接由涉外合同當事人選擇作為其合同的準據法;二是在當事人未作法律選擇且國際條約和中國法均無規定的情況下,由法院依職權決定適用國際慣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國際貨物買賣、貨物運輸、貿易支付等合同的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適用有關國際慣例的情況較為普遍,并且這類約定一般都為法院所承認,最終法院也依據當事人約定的國際慣例對案件進行了裁判。
因此,作為國際慣例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在中國法律淵源中的位次要低于條約和法律。但必須說明的是,國際體育組織規章要在中國的法院審判中得到適用,也只能是上述兩種方式之一。由于在涉及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效力問題的糾紛中,通常來說當事人一方就是該國際體育組織,而另一方是受其規章約束者,或者雙方當事人都是受其規章約束者,這就等于實際上雙方已經直接選擇了有關規章作為其合同準據法,則法院應直接適用之。但《民法通則》第150條規定:“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盡管有理由相信國際體育組織規章中的大多數條款的適用,都不會違背中國的社會公共利益,但仍不能排除中國法院運用這一安全閥式的條款拒絕適用國際體育組織規章的情況發生。最典型的如過去《國際足聯章程》要求所有有關糾紛只能通過其內部程序解決而不能訴諸外部解決機制,此類規定因剝奪了當事人的訴權這一最基本人權,將很有可能被中國法院認定為違反了社會公共利益而排除其適用,轉而適用中國法。另外,常常引發爭議的國際足聯《球員地位與轉會條例》中的球員轉會規則因其和中國的《勞動合同法》中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精神有根本沖突,在訴訟中恐怕也有可能被法院運用上述公共秩序保留條款排除適用。
至于純屬合同性質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則必須由法院依據法律來判斷其有效性。不過,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和中國法的規定不同,并不意味著其必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為根據《合同法》第126條的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法律。因此,該準據法既可能是中國法也可能是外國法。
最后,中國法律迄今未對國際習慣的效力與適用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中國一貫聲明并在實踐中堅持按照國際法或國際基本準則來處理有關的國際問題,而這里所稱的“國際法或國際基本準則”無疑包括國際習慣規制[18]。據此推斷,如果某項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屬于國際習慣的范疇,也應得到中國法院的支持,且在適用上優于中國國內法。當然,這一推論尚需得到實踐的檢驗。
體育法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國際體育組織規章具有多樣性,試圖用某一種淵源或范疇來概括它們的法律地位是不明智的。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體育組織規章中,既有少數已構成具有約束力的國際習慣法規則,也有大量屬于國際慣例的任意性規范,還有一部分則仍僅僅是帶有國際因素的合同。明確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國際體育法律秩序的構建,并為中國司法機關將來在實踐中處理與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有關的問題提供有益的幫助。不過,對于國際體育組織規章法律地位的演變仍需密切關注。假以時日,一些影響力較大的規章如《奧林匹克憲章》仍有可能逐步發展成國際習慣法規則,那將是體育法的重大突破。
[1] 黃世席. 論國際奧委會的法律地位:一種國際法學的分析[J]. 法學論壇,2008,23(6):47.
[2] 盧兆民,董天義. 國際奧委會的法律屬性[J]. 體育文化導刊,2008(2):59.
[3] 詹寧斯,瓦茨[英]. 奧本海國際法[M]. 中譯本.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27.
[4] 吳義華,張文聞. 國際體育法調整范圍及淵源分析[J]. 體育文化導刊,2009(3):151.
[5] 黃世席. 國際體育法若干基本問題研究[J]. 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7,22(1):27.
[6] 郭樹理. 體育糾紛的多元化救濟機制探討——比較法與國際法的視野[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76-396.
[7] 蒂莫西?希利爾[英]. 國際公法原理[M]. 2版.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7.
[8] 白桂梅. 國際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40.
[9] Michael Beloff,Tim Kerr,Marie Demetriou. Sports law[M]. London:Hart Pulishing,1999:257.
[10] 程家瑞. 國際條約和習慣法對商事法國際化的影響[J]. 國際商法論叢,1999(1):10-11.
[11] 韓德培. 國際私法[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1.
[12] 李雙元. 國際私法[M]. 2版.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3.
[13] 胡緒雨. 國際商事慣例的作用空間與效力基礎[J].當代法學,2006,20(2):112.
[14] 武樹臣. 在現行法律和奧林匹克國際慣例之間尋求平衡[J]. 河北法學,2009,27(10):47.
[15] 裴洋. 論奧林匹克標志的法律保護——國際法與比較法的角度[J]. 法學評論,2008(2):151-158.
[16] 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律師向北京高級法院提交訴訟代理詞[EB/OL].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sports/tyzq/zqzgxw/200202070247.htm,2010-07-10.
[17] 單文華. 中國有關國際慣例的立法評析——兼論國際慣例的適用[J]. 中國法學,1997(3):52.
[18] 曾令良. 國際法學[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30.
Issues about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hina
PEI Yang
(School of Law,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out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Chines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custom theory, the other sou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ory, and the contract theory. However, since the functions and influences of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practice are different, their legal nature can not be generalized. 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and the Olympic Truce have become international customs; most of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r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ther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Olympic Charter, are provided only with the contract nature. Thos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used a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in courts in China, while the validity of those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a foreign contract attribute must be determined by courts according to applicable laws.
sport law;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regulations;Olympic Charter;World Anti-Doping Code
G80-05
A
1006-7116(2010)11-0020-06
2010-08-23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職業體育聯盟法律規制研究”(07JC820034)。
裴洋(1976-),男,副教授,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體育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