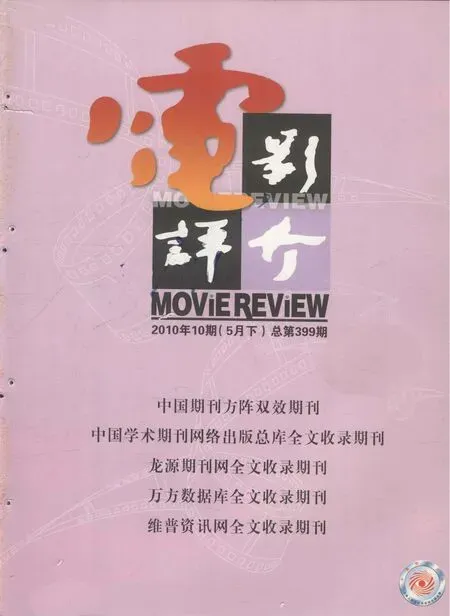意識形態下的英雄形象建構的突圍——淺論《暗算》的人物塑造
在麥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里,離不開對英雄主義情結。在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最受爭議的作品——《暗算》里,另類的英雄形象建構在特殊的稟賦與荒誕的命運的結合上。可以說,麥家的創作理念離不開時代氣息的渲染,離不開人類對神秘的無窮探索,離不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投射。當這些結合在麥家的創作中,英雄形象所表現的人的悲劇性、宿命性和局限性究竟向我們寓示著作家怎樣的人生思考?又傳達了作家怎樣的價值取向?
一、英雄形象特征的“時差”
尼采釋:“我們每個人都有英雄主義的情結。”英雄,是對人性光輝形象的極致崇拜,同時其形象塑造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差異下的意識形態性。若用五六十年代軍事文學中的典型英雄形象與麥家在《暗算》中塑造的英雄相對比,其“時差”尤為明顯。
在戰爭的記憶尚且鮮活的年代,活躍在硝煙滾滾的戰場上的英雄成為五六十年代軍事文學中的典型。魏巍先生在《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用仰視角塑造的“高、大、全”的朝鮮人民志愿軍形象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英雄崇拜類型。那個時代需要為革命無懼犧牲的精神,人民志愿軍的無私與可愛與時代呼喚的主流意識形態契合得天衣無縫。
在《暗算》中,同樣活著為革命奮不顧身的安在天類型的英雄,他們穿梭于沒有硝煙的神秘戰場,懷著同樣沉重的信念“一個真正的軍人應該被世上的最后一場戰爭的最后一顆子彈打死。”但還存在著另類英雄,在這里作者著墨濃重地寄予了荒誕的結合:一者是常人難及的天賦,一者是卑微甚至離奇的死亡方式。
“聽風者”的主角瞎子阿炳為妻子“背叛”后的恥辱難忍而自殺,但其元兇是他性無能的不自知與聽力超常的天賦。“看風者”的主角黃依依擁有天使的美麗與數學天賦,卻命殞于一個潑婦無意之手;另一主角陳二胡因離開密碼而瘋,卻終死于破譯密碼的興奮。“捕風者”的主角鴿子,蘊含著睿智與溫柔的迷人,卻殞命于生產時的夢囈。
英雄葬身于無常,沒有推算的邏輯,沒有橫飛的子彈,看不到掙扎時扭曲的面容,聽不到嘶聲力竭的苦吟,只有不經意間無聲無息的暗算。在這“時差”背景下凸顯的英雄人生比待解的莫爾斯電碼更具神秘氣息。
二、神秘體驗精神結構三維度與英雄形象建構
在文藝心理學上,神秘體驗的精神結構大致包含三個維度:“一是在神秘體驗中必定有一個超越日常經驗與智性邏輯的對象,主體在它面前充滿了敬畏、震驚、信賴、臣服、歸依之感;二是神秘體驗作為通向這個對象的超強心理能力,既不是普通經驗或日常感覺,也不是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理性;三是一旦通過頓悟、啟示等超常心理能力與最高的美(即終極的現實)契合為一,主體將會體驗到一種心醉神迷的同一性體驗。”
在《暗算》中,描述的是一個個破譯密碼的故事,但在作品中,極限密碼是人生的無常與偶然。在這面前,無論天才抑或英雄,都無法按照固定的邏輯去破譯。“最困擾我們人類的密碼還是人自身。這大概是麥家最終要完成的一個主題。人性的善惡,人的情感,人的命運,它們的真實信息多半都以密碼的方式在我們耳邊回響。破譯人的密碼,也就是揭開一個人的真相,有時候真想一旦揭開,也許我們反而失去了生存的勇氣。”作為一個超越日常經驗和智性邏輯的對象,人生的荒誕性,那些無法確認的,那些不可把握的,那些難以解釋的,卻構成了日常與平凡。麥家釋:“世俗生活的貌似平庸、無序,卻隱含著真正的殘忍和殺性。”
“在常人看來,荒誕是正常的。在荒誕主義者看來,正常的卻是荒誕的。”[6]在《暗算》中,破譯密碼的英雄最終都敗給了平常生活里的無常這部終極密碼,這就給讀者一種強烈的對比震撼:人生終能把握的是什么?
韋夫,以靈魂闡述人生的特殊英雄。作者選擇了獨特的闡述視角,用虛構架接出一種向人生荒誕性發問的獨白:“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圖同樣是困難又困難的,上帝有時候似乎讓我們明白了一點什么,但更多時候只是讓我們變得更加迷茫。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這里,上帝同樣常常讓我們拿他沒有辦法。”
筆者認為,上帝在這里并非純粹代表一種宗教信仰,而是對人生那玄而又玄的未知領域的代號。面對人生,可以把握的已知使我們奮進,不可把握的未知誘使著我們緊握著這股“奮勁”去思考,探索,同時為之心醉。麥家塑造的另類英雄形象,正是蘊含著人類自身對于神秘未知的復雜情感與向其發問、追尋的崇高勇氣。
三、意識形態下的光華與突圍
英雄的塑造離不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投射。在當下,《暗算》中的英雄們,帶著神秘心理體驗的精神內涵,闖進了媒體聚焦視野,引發了一場場甚囂塵上的爭議。筆者認為,作品《暗算》中英雄形象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標榜著“時差”特征的時代新英雄和以神秘、懸疑為閱讀賣點的吸引力,也包括其與當下主流意識形態契合度。
“主流意識形態是指在某一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或者具有統治作用的理論體系,是一個社會思想文化的中樞和支柱,是構成一個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礎和載體。”[8]我們時刻在弘揚著一種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而作品中,當安在天面對黃依依的情感糾纏與妻子的“神秘”死亡帶來的沉痛時,“我的理智總是堅定地守護著我。我知道,人世間沒有完美的事情,我們要甘于忍痛和接受煎熬。”安在天的理智宣示著一種磐石般的信仰——組織的絕對權威。
我們明瞭,安在天生活的時代背景并非當代,“開除黨籍可以抵三年罪”等屬于早已塵封的歷史的表述彰顯著一種真實感。安在天的價值觀無疑代表著一定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人的價值取向上的強大投射。當我們企圖尋找這種價值觀確切的歷史坐標時,卻發現這是一種建立在含糊其辭上的虛構的時代背景。
麥家說:“我的小說都是我愿望和想象的混合物。”熱衷于虛構的創作理念,我們更能從其中解讀出作者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和把握。作者無疑是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前提下進行英雄形象的塑造,但是其中凸顯了作者的另類思考。“我雖然用了國家主義這個平臺,但沒有通過這個平臺把英雄抬得更高,甚至一定意義上來說我想用這個平臺折射出中國英雄的悲劇性。”
黃依依與安在天所代表的兩類英雄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因為感情糾葛引發的沖突和情感悲劇,迫人深思;陳二胡的人生與紅墻簽下了生死難離的契約,他的崇高奉獻精神與以瘋狂乃至興奮而落幕的生命歷程,迫人追問——在崇高號召下的價值觀與人性本身自由追求之間抉擇。作者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卻以一個個死亡的沉默向讀者發出最響亮的追問。
“處于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權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會時時受到挑戰。”茅盾文學獎,作為官方對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可,其傳達出的意識形態性毋庸置疑,但當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所傳達出來質問也獲得認可的時候,對波詭云譎的時代變動中的永恒價值尋覓也從一個層面上得到了認可,刻上時代問號的新的英雄形象正在步入文學的舞臺。
四、結語
麥家道:“我知道,時代確實在變,日新月異地變,有些美德變成了迂腐,有些崇高變成了可笑,有些秘密變成了家喻戶曉。但我深信,有些東西,有些價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變的。從理想的角度說,我寫作的意義就是找到,或者建立這些東西,這些價值,這些目光。”人性中英雄情結的永駐性崇拜和神秘心理體驗所寓示的永恒性追尋凸顯了在主流意識形態投射下,關于價值取向的時代性突圍與追問。
[1]麥家.《人生中途》[M].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
[2]麥家.《暗算》[M].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
[3]童慶炳.程正民主編.《文藝心理學教程》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5
[4]賀紹俊.《麥家的密碼意象和密碼思維》[J].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38
[5]王長勝.《“荒誕主義”詩歌實驗小組:自我顛覆后的濕地》[J].中國電子商務.2006年第10期.27.
[6]禹建萍.《加強黨對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領導》[J].學習論壇.2008年第3期.19.
[7]仲余.《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辭及獲獎作家感言》[J].中學語文:寫作新空間.2008年11月.30.
[8]麥家.《我心里的幾片羽毛》[J].當代文壇.2004年第4期.23
[9]洪子成.《當代文學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10]劉小楓.《沉重的肉身》[M].華夏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