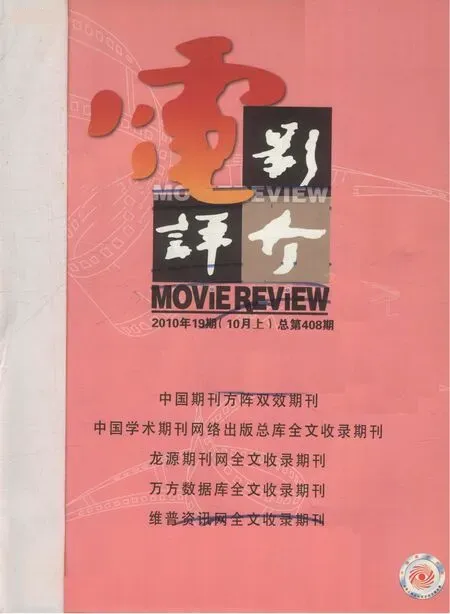淺談藝術對宗法的穿越
引言
中國古代藝術根植于宗法社會,宗法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有深刻的影響。劉道廣先生在《中國藝術思想史綱》前言中指出“……中國藝術思想受制于傳統宗法意志和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藝術思想也在掙脫宗法意識的制約中有所變化。”[1]筆者也認為,藝術雖然受制約于宗法,但是藝術畢竟是藝術,有自身追求獨立尋求自由的渴望,因而穿越宗法顯示自身。中國藝術無疑和宗法有密切的關聯,但不僅僅是受其制約,而是在同宗法思想的博弈中體現獨立性。藝術既在宗法之中,又能穿越宗法。當宗法性增強時,藝術性減弱;當宗法性減弱時,宗法思想強烈。那么,藝術是如何穿越宗法的呢?
一、 藝術與宗法
中國古代藝術在與宗法的交融、對照甚至批判中獲得其合法性。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下藝術與宗法的關系。
何謂宗法?宗法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在家庭、家族這個范圍內,一個人的身份,主要決定于血緣關系。宗法是在血緣關系基礎上衍生出的。“身體流動的血,成了生命的符號,不僅僅是生命的基因,也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基因。它可以繁衍,可以承傳,構成了家族制的最為強大的紐帶。”[2]“宗法制度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的社會組織制度,基本上是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社會經歷了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的演變過程,貫穿這一演變的主線是血緣的脈絡。”[3]可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文明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區別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特色。藝術和宗法的關系主要呈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宗法思想是中國藝術思想的主流。中國古代藝術具有濃重的鄉土意識、家國觀念和情感血脈。歌曲《歌唱祖國》、《我的中國心》、小說《白鹿原》、電視劇《闖關東》、《走西口》等都彌漫著濃重的宗法意識。其次,藝術思想并不等同于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是中國思想的主流但不是唯一。任何藝術思想的發現必然是從藝術形式本身出發,否則便是單純的思想而非藝術思想。
在藝術與宗法思想的關系上,一方面藝術受宗法制度制約,另一方面藝術表現出與宗法思想的對照、疏離與超越,是在規范之中尋找自由。藝術其實是在不斷見證宗法的束縛,同時又不斷擺脫宗法走向自由。中國優秀的藝術既能生存于宗法的土壤,又能穿越于宗法。中國優秀的藝術一方面能對根深蒂固的宗法思想深度展示,另一方面又能穿越宗法,見證生命的魅力。
那么,中國藝術又是怎樣依存于宗法,又擺脫宗法的呢?中國最優秀的藝術能夠在宗法的兩端上深入思考與體驗,創造出藝術的化境。所謂執其兩端即在兩個原點來尋求超越,一個起點,一個是遠點。藝術對宗法的穿越之路也是兩個方向。一條是起點還原,即還原到宗法產生的人性基點上,即回到其來源處和藝術現象相互對照。一個是遠點伸展,即在血緣關系最遠的衍生點上來看,“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遠點即是返回原點。歸結為一點,還原即中國藝術對宗法的穿越之路。藝術的兩端方向的伸展形成了中國藝術的張力和魅力。
這種還原主要體現為情感、自然、空性之維來實現的。
二、情感之維
世界的關系包含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關系。在人與人,人與自身的關系中,最源初的關系其實是血緣關系。血緣正是人與人之間情感關系的原點。
藝術是人的情感的顯現。情感也有多種情感。情感產生于人倫之情。從宗法的角度看,血緣之親情,如母子之愛、舐犢情深,兄弟姐妹之愛等最原初的情感。這種血緣之情是宗法制的原點。宗法制一步步由家到國到天下擴大的過程中,其實是一步步背離血緣之情的,悖于常情的。最初的血緣之情感,在宗法的演變、禮樂的束縛、理學的鉗制中慢慢走向反面。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回家、還鄉等主題即是回歸還原至血緣之情的原點。如“日暮相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還有”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無論還鄉、還是回家,其實都有一種血脈相連的情感存在,這是中國人生命的起點,也是最溫暖的地方。中國似乎更喜歡葉落歸根,余光中的《鄉愁》道出的是一種普遍的鄉土情節。
愛情是處于血緣之情之外的另外一種情感。愛情是基于人之本性的需要而產生,具有普適的價值。人類自始有情根。正如《紅樓夢》中講那塊補天的石頭被置于青埂峰下,青埂即情根是也。補天的石頭具有天地之靈性,不同于世間之濁物。同在天界的絳珠仙草也是如此。情感的萌生來源于天性,或者說具純粹性、無功利性。不同于血緣之情,自然也不同于宗法。《紅樓夢》以愛情穿越宗法,見證了宗法社會的虛偽、渾濁和腐爛。或者說,《紅樓夢》以天緣取代血緣,以情感反思宗法。情與禮的沖突,情與法的沖突,始終是中國藝術一條重要的線索。中國四大民間傳說都是愛情,皆流傳千年,深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愛情是純粹的情感,是人類的情根。純粹愛情的書寫無疑具有人類學的意義,不是簡單的血緣之情。但是,在許多時候,愛情已經彌漫了濃重的宗法氣息,遭受了來自宗法社會的制度、規范以及意識控制的重重障礙。在《紅樓夢》中,寶黛之情逐步剝離了現實功利的金玉良緣,指出了“文死諫,武死戰”的名與利的虛偽。曹雪芹以純粹的愛情穿越宗法的迷障,否定了其對人性的重壓。中國許多愛情詩,其情感之熾熱,之決絕,不是一個宗法所能涵蓋的。“冬雷陣陣夏雨雪,乃敢與君絕。”中國藝術的魅力在于宗法,更在于情感在宗法之中穿行的婉轉之美。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即在婉轉、深情、纏綿悱惻的樂音中讓人感動不已。
三、自然之維
道家讓人回歸于自然之中。道家精神也是最具有藝術氣質的,道家哲學點染了中國藝術精神。中國藝術不僅僅是現實的投身,人心的投射,更是“氣”的產生。“氣”才是藝術的真正本源。“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品序》)。鐘嶸在這里將藝術之源推向物、推向氣。
受道家思想等的深遠影響,中國藝術逐漸在擺脫宗法的規范中,拓展了藝術的宇宙意識與天地境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典型的例子。在那個月夜,彷佛回到了原初,回到最溫暖、最澄澈的家園。人與物皆融化于宇宙之中。就繪畫而言,中國繪畫中人占據的空間很小,即丈山尺樹,寸馬分人。有時候都沒有人,只有山水和花草樹木,人已消散于、融化于自然風景中,但敞開的卻是無邊的心胸。這種思想卻非宗法等所能涵蓋的。
道家的思想在思維方式上也還是一種還原之維。自然一方面是自然界,另一方面即自然而然。自然世界作為宗法社會的來源,作為宗法社會的一面鏡子。以植物之心來映射人倫之心,在生命的起源處尋找意義。《紅樓夢》中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的說法。草木、石頭本是自然之物之常態,而金玉則是人文雕琢之物。詩歌中也有“草木有本心”之說。這里的草木、石頭、本心等皆具有還原的意義,即將人倫之情感還原為自然的草木之情,將宗法之血緣還原為自然之聯系。《紅樓夢》正是作為自然界的頑石被一僧一道帶到了人間,成為玉,又從人間返回自然。石頭的意義穿越了宗法,獲得了生命的本源意義。陶淵明也說“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欣喜于“復得返自然”。從天境與人境之中來因正人倫、宗法的束縛,從而隱含著對宗法的批判之維。自然的另外之意在自然而然。對于人的自然而然來說,那就是保持一顆童心,保持本性。道家思想將宗法之原點往前推了一步,慢慢消解了宗法對藝術的鉗制,獲得了更多的表現空間。
四、空性之維
除了情感的還原,藝術的還原還有一條哲學之路。外來的佛教與中國本土的思想相互融合,形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禪宗,同時也為中國藝術迎來拓展其境界的大智慧。禪宗思維影響了藝術,也使藝術境界、藝術思想穿越宗法,從而獲得更高的境界。
禪宗之于中國藝術的貢獻主要在“空”的呈現。“因此,如果大體而論,說莊子是自然人,儒者是道德人,玄學家是準自然人,那么可以斷言,禪者決不是自然人。不僅如此,以后的中國人中也不再有純然莊子式的自然人了,看空成為中國思維的一種新的質素,它是一種精神品格,也是一種思維方法,這方面,王維、蘇東坡都是絕好的個案。”[4]如果說儒家有所執,道家有所忘的話,那么禪宗更是徹底的消解。消解了宗法的血緣,也消解了道家的自然,還原世界一個空空蕩蕩。禪宗以心為本體,倡導萬有皆空。 在禪宗看來,普通的心,因為有執著,要無念、無相、無住,期望身與心兩空的境界。在日常生活中,“要行而行,要坐即坐,饑來吃飯,困來打眠。”倡導“平常心是道”,“郁郁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總是法身”。在禪宗境界上,則有“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和“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這種意識層面的解放拓寬了藝術境界,直返生命的本源。“靜照的起點在于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著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5]禪宗的澄明之境界讓世界萬物成為自性的存在。禪宗的思維也是徹底的還原之維,“舍棄一切先入之見和一切有意識的目標,中止對某些功利的渴望,向未知、神秘的奇妙世界創造性的開拓,就是禪和藝術散發出的誘人魅力之一。”[6]他消解了宗法的兩端,卻真正敞開了藝術。
中國藝術家總能穿越宗法,尋找到一方自由的天地。如果說宗法是中國藝術家無法擺脫的生存的土壤的話,那么藝術與禪宗則是在這個土壤上為其插上了飛翔的翅膀。中國杰出的詩人、畫家始終在廟堂與江湖之間徘徊。蘇軾是其代表。“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在《前赤壁賦》中,更是獨享清風明月,飲酒賦詩,縱論英雄。在水與月中領悟天地之變。“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在時間、空間的延展和消解中,在生命本源的復現中,顯現了藝術的魅力。
中國古代繪畫匯入了禪宗意識。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提出‘三遠’即高遠、平遠和深遠”。三遠的構圖方式,把視覺轉化到畫面之外,引向遠,引向畫面的虛無。禪宗則通過“遠”來向無限延伸,然后返歸自心。馬遠的《寒江獨釣》表現了那種玄遠的禪宗意趣。在境界的拓展中還原自性。“唐代繪畫實踐的不斷深入,引導著人們的繪畫藝術思想的深入。更由于唐代佛學思想的興盛,般若學思辨方式融入繪畫的思想中,如前述之實相非相之論: 初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參悟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待到要尋個休息處,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這種思辨方式,在山水畫創作中,即畫家在山水面前的‘震動’、‘感悟’和‘立意’的藝術表現,往往有不同尋常的地方。”[7]唐代著名詩人兼畫家王維的雪中芭蕉感受到的不是主體心靈的失落,也不是超越精神的神明,而是一種獨特的心靈領悟。魏晉的“以佛對山水”和唐代的“以法眼觀之”的雪中芭蕉,形與神之間,神才真正成為心靈表現的主體。這也是禪宗中“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禪宗最宗超越于形式,也最終穿越宗法,成為個體心靈自性的表達,最終開拓了藝術的表現空間。
結語
宗法在社會歷史中形成,并滲入中國人的心理深層結構之中,是中國藝術的主脈。這在中國戲曲、年畫、民間文學中表現的尤其明顯。但是,中國藝術作為人最自由的情感形式,在宗法的基點上,尋找騰飛的翅膀。在原點追尋與外來給養的雙重滋潤下,從而穿越宗法,譜寫出光輝而靈動的藝術篇章,生動再現了中國古人的自由精神。
藝術當以生命為依托,中國藝術思想史是藝術與宗法博弈的歷史。在生命的還原、澄明中,藝術成為自由、情性的藝術。
[1][7]劉道廣.中國藝術思想史綱[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1,176.
[2][3]蘇桂寧.宗法倫理精神與中國詩學[M].上海:三聯書店.40.
[4]張節末.禪宗美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4.
[5]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
[6]錢正坤.禪宗與藝術[J].美術研究.1986(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