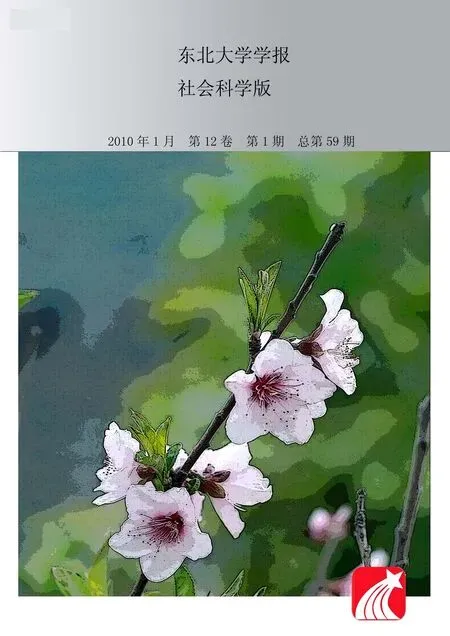電子游戲審美研究的困境與游戲詩學的建構
吳玲玲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 電子游戲審美研究的必要性
美國媒介學家利文森曾以玩具、鏡子(即工具功能)和藝術來比喻媒介發展的三個階段。1958年工程師威廉開發第一個簡單的電子游戲,只是為了讓到他研究所來參觀的訪客玩;之后,游戲走向市場,但在相當長時間之內游戲的開發都只是為了“玩”。隨著技術的進步、電子游戲本身敘述能力的增加以及嚴肅游戲的開發,電子游戲的鏡子即教育工具與文化傳播功能被認可。進入90年代后,尤其是本世紀,開始把電子游戲稱為“第九藝術”。但對于電子游戲來說,玩具、鏡子和藝術不僅是其媒介演進的三個階段,更是其相互依存的三個文化身份----“玩具”是電子游戲的本體存在,“鏡子”是電子游戲的社會存在,藝術與審美功能的發揮則是電子游戲本體存在與社會存在實現的基礎,是電子游戲發展的內驅力之一。但是,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態,電子游戲尚處于與早期電影類似的階段,其藝術形態的成熟有賴于研究者從學術的角度,發展出適合于電子游戲藝術與審美研究的理論話語與批評體系,以挖掘其藝術表現的潛力。
電子游戲經過近50年的發展,已成為了一個可與好萊塢媲美的產業。早在1998年,美國游戲產業就以63億美元的總收入超過了當年美國電影產業的票房收入。2006年,美國的游戲總產值為73億美元。在我國,游戲產業發展也十分迅速。自2002年8月“網絡游戲產業與網絡游戲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之后,我國游戲產業的發展無論是在政策上還是資金上都獲得了國家的強力支持。到2006年我國網絡游戲市場規模已達到65.4億元人民幣,至2009年1月,我國網絡游戲經濟規模上升為207.8億元。但與歐美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由于我國數字技術與電子游戲的后發之勢,電子游戲盡管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但并沒有形成成熟的游戲文化----游戲品種單一(主要是網絡游戲),游戲內容同質化,缺乏對游戲審美發展與可能性的想象。游戲產業的健康發展與游戲文化的成熟,亟須得到游戲藝術、文化與審美理論的回應與支持。
在文化上,電子游戲的產生與發展是當代文化審美化發展的重要動力與表征----電子游戲推動了數字電子的發展和應用,并滲入到當代審美文化的各個方面:以電子游戲情景作為表演場景的“街舞”表演、電子音樂表演,以游戲為原型的游戲文學、服裝、主題公園、玩具、電子競技……,而交互式電影、游戲化電影的產生,基于電子游戲平臺的藝術創作等則是作為觀念的“電子游戲”對當代文化影響的最突出的表征。同時,電子游戲消費者在人口特征上也發生了“主流化”,電子游戲不再是孩子們的”玩意兒”。早在2001年時,在美國已有1.45億人玩電子游戲,平均年齡為28歲,18歲以上的成年人占60%,50歲以上的占13%,女性消費者占43%[1]。我國由于信息產業的相對落后,游戲群體年齡低于美國,50%集中于19~25歲之間。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隨著“數字化土生土長一代”群體的成長與拓展,“電子游戲經驗”將作為數字化時代人們一種基本的生活經驗,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人們的消費方式、思維模式、審美趣味、文化認同以及自我身份的確認。
因此,對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既是電子游戲藝術形態走向成熟和產業發展的理論所需,同時也是深入理解當代文化審美化的一個不可回避的領域。
二、電子游戲文化審美研究的現狀與困境
隨著電子游戲在經濟與文化上的成功,從2002年開始,對電子游戲尤其是網絡游戲的研究一時成為學術熱點,從產業、政策法規、教育等不同角度對電子游戲進行研究;電子游戲的身份也發生了從作為道德批判對象的“魔機”、“精神鴉片”開始向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轉變。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也獲得了一定的學術關注。但在學界對游戲藝術與審美研究投以關注的同時,電子游戲審美研究也走入了困境之中。
首先表現為理論的困惑。我國對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是從通過論證電子游戲的藝術性,為電子游戲正名并確認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開始的。早在1997年就有游戲從業者明確提出電子游戲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2003年以后,一些學者開始從理論的角度論證電子游戲藝術身份的合法性。電子游戲是數字化時代“土生土長”的綜合藝術形態與游戲相結合的產物,是新媒介文化審美形態最為典型的代表。在無論是對數字藝術還是對游戲的研究都缺乏系統的理論建構的情勢下,以康德、席勒、伽達默爾、康拉德·朗格、赫伊津哈等人為代表的“藝術游戲說”成為對電子游戲進行審美探討的基本哲理根據。誠如有的學者所說,電子游戲是“從游戲精神到游戲藝術”的表現,“游戲說”不僅“是游戲作為藝術最有權威的根據”,把電子游戲置于審美話語體系之中,將游戲活動從單純的娛樂活動升華為審美活動,還有利于處理好游戲的藝術性和商品性的關系[2]。
但在以審美精英主義話語的“藝術游戲說”論證電子游戲文化與藝術合法性的同時,也使電子游戲的研究陷入了理論困惑之中----以“游戲說”把電子游戲納入審美話語之后,電子游戲的文本如何建構才能達到這一精英審美標準?這種精英式的話語,與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子游戲如何才能在深層次上“和諧相處”?已有的游戲文本的成功是因其切合了這一精英審美標準,還是因為其建構了一種新的描述和理解生活與世界的文本形式?如果是后者,這一新的文化文本建構特點何在?電子游戲是什么樣的藝術,其藝術性表現在什么地方?與傳統的藝術尤其是與同樣基于數字媒介產生的新媒介藝術如交互電影、數碼戲劇相比,在形式與內在審美機制上有何異同?不同類型電子游戲間有何審美差異?……對這一系列的具體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突破坐而論道的“藝術游戲說”,從抽象回到具體,在多種理論視野下對具體的游戲文本進行分析。
其次是技術主義式的 “概念先行”。電子游戲作為信息媒體技術發展的一個典型成果,數字技術是它存在的基礎。學界在對電子游戲藝術的特點、審美特征進行具體論述時,都把基于數字技術的“交互性、參與性、敘事的開放性、虛擬性”當做了“先在”概念,或者說,把對電子游戲藝術特點、審美特征的論述,變成了對這一系列“先在”概念的證明。這一研究路徑的偏失,往往使研究者忽視了電子游戲的審美特點,不僅是其媒介特性所賦予的,同時也是在長期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形成的。
以互動性為例,曼諾維奇認為“互動”不僅指人與媒介之間的實質性互動,同時也是一種心理上的互動,是一種認知與審美方式;所有的古典形式如文學、戲劇、繪畫等,以不同的方式如敘述的省略、描繪物體時對細節的缺省等策略,要求使用者發揮想象、參與、假設、回憶、認同等心理機制來填充這些缺省的信息以實現互動;現代媒介和現代藝術進一步發展這些互動機制,如產生于上世紀20年代的電影蒙太奇、達達主義和未來主義,通過增強對欣賞者心理認知與身體參與的要求,進一步推動了“互動”的發展。60年代之后產生的新藝術形式,如偶發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則把藝術本身變成一種交互活動[3]。技術主義式“概念先行”忽視了電子游戲審美特點產生的歷史文化語境,不僅限制了電子游戲審美研究的視域和對電子游戲審美發展與文化傳承可能性的想象,也限制了通過對電子游戲審美研究以深入探討當代審美文化的可能性。
三、電子游戲審美研究困境的突破游戲詩學建構

對電子游戲文本的分析,主要圍繞著電子游戲的四個存在層面進行----游戲、大眾文化產品、當代審美文化文本、在游戲者參與過程中最終完成的開放式文本。因此,游戲詩學的建構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切入。
首先是形式主義詩學,“游戲”是電子游戲存在的基本前提,只有電子游戲文本讓游戲者享受到游戲的樂趣,游戲文本才能最終實現其文化承載的意義。“游戲是在某一固定時空中進行的自愿活動或事業,依照自覺接受并完全遵從的規則,有其自身的目標,并伴隨緊張、愉悅的感受和‘有別于’‘平常生活’的意識。”[5]電子游戲的基本特點之一就在于它通過游戲元素與游戲規則,構建起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上都與日常生活相隔離的世界,讓人在游戲的過程中獲得愉悅的感受。但“隔絕”并不等于與現實生活“絕緣”,本質上它“反映了某個特定時期的現實生活以及由這種生活環境所營造的經驗與活動,并以富有趣味的途徑將其表達出來,或者說,它也是文化蘊藏的體現以及人類知識情趣化的表征與新的變異的傳遞方式”[6]。游戲文本這一特征與形式主義美學的基本特征有著諸多相通之處,因此,形式主義詩學的研究方法可以為電子游戲文本分析提供一些啟示。
其次是類型詩學。電子游戲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產品,類型化是基本的生產特點和美學特征之一。當前對電子游戲的分類主要是在游戲產業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較為公認的有以下幾個類型:行動、歷險、角色扮演、模擬、體育、戰略、戰爭。巴贊在論述類型電影時曾指出:“類型影片的‘活力和豐富多彩’是‘來自一種始終與它的公眾保持美妙的和諧一致的藝術演變’結果。”[7]電子游戲的類型發展也同樣是這種“藝術演變”的美學結果。因此,對電子游戲進行類型詩學的研究,就是要在具體、細致的文本分析基礎上,對電子游戲的類型劃分及各類型的美學特征進行總結。目標有兩個,一是把在游戲設計過程中自發形成的游戲慣例與類型改造成更富理論性的自覺的審美類型;二是在不同類型游戲審美標準確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基于游戲文本描述的經典體系,同時催生出新的游戲審美類型。
再次是文化詩學。麥克盧漢說游戲“是集體和社會對任何一種文化的主要趨勢和運轉機制的反應。和制度一樣,游戲是社會人和政體的延伸”[8],作為文化產品的電子游戲,則承擔了比傳統游戲更多的文化意義,它除了是“游戲”以外,更是當代社會一個開放的審美文化文本,這個文本直接與歷史、宗教、社會、道德、經濟、美學理論、工業技術、社會形態等文化范疇相互聯系,對電子游戲的審美探討,只有在把電子游戲文本置于當下和歷史的文化語境時,才能深入地進行。
最后是精神分析詩學,這主要是對游戲者的研究。電子游戲作為一個完整的“文本”是在游戲者游戲的過程中實現的,因此,對在游戲者游戲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文本進行分析,是電子游戲的詩學分析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對電子游戲進行精神詩學層面的分析,就是要通過對游戲者“游戲過程”的分析,把握游戲者在“游戲”過程中的審美體驗。由于“游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游戲的過程與結果具有不可把握性,因此,對電子游戲進行精神分析詩學層面分析的文本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首先是電子游戲系列產品之間的異同。電子游戲作為文化工業產品,系列產品的出現不僅僅是出于對生產成本控制的考慮,也是產品與游戲者之間“協商”的產物。因此,同一系列不同產品之間的異同,往往反映的是游戲者的游戲與審美需求。其次是對游戲者依據自己的游戲體驗寫成的文字進行分析,包括游戲文學、游戲論壇中發表的各類帖子、游戲雜志等圍繞電子游戲文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字現象。在這種意義上說,“電子游戲文本”是一個泛文本概念。
四、 結 語
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在我國才剛剛開始起步,游戲詩學理論的建構不僅是把電子游戲當做一個獨立的審美領域進行研究的前提,也是突破當前研究困境所需。正如Aarseth所說,電子游戲,“是我們所見的最豐富的文化類型”,就其存在的媒介基礎而言,它包括信息技術的各個方面(計算技術、通信技術、信息存貯技術、微電子技術、網絡技術等)并推動了信息技術的發展;就其藝術形態而言,電子游戲融合了以往一切藝術形式的表現手段----小說、戲劇、影視、動漫、服裝、音樂、文學、繪畫、建筑等;就其文本生產與消費而言,文本的消費者同時也是文本的生產者,徹底打破了傳統媒介的傳受關系。電子游戲“以一種傳統大眾媒介如戲劇、電影、電視、小說所不可能的方式,把媒介的審美性與社會性相結合”,并“要求我們尋找適合的研究方法”[9];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須要借鑒多學科的理論,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符號美學、電影理論、文學理論……,但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傳統學科的激發下創立一個專門研究電子游戲的學科。提出從形式主義、類型詩學、文化詩學、精神分析詩學四個層面對電子游戲進行文本分析和詩學建構,采取的是一種“視角主義”態度,并不是以其本已成熟的概念對電子游戲進行框定,更不是說只能從這幾個層面對電子游戲進行研究,目的在于能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望在提供一個基本思路的前提下,能使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電子游戲的審美研究中來。
參考文獻:
[1]雅克·埃諾. 電子游戲[M]. 馬彥華,譯. 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2005:53.
[2]汪代明. 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游戲藝術[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3(12):474-476.
[3]Lev M.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Media[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56.
[4]Pearce C. Into the Labyrinth: Defining Games Research[J]. The Ivory Tower, 2003(4):1.
[5]約翰·赫伊津哈. 游戲的人[M]. 多人,譯. 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6:30.
[6]張胤. 數字化之道與當代課程建構[M]. 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4:104.
[7]托馬斯·沙茲. 舊好萊塢/新好萊塢:儀式、藝術與工業[M]. 周傳基,周歡,譯.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5.
[8]馬歇爾·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M]. 何道寬,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291.
[9]Aarseth E. Computer Game Studies: Year One[J/OL]. Game Studies,2001(1):1[2008-12-05]. http:∥www.gamestudies.org/0101/editoria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