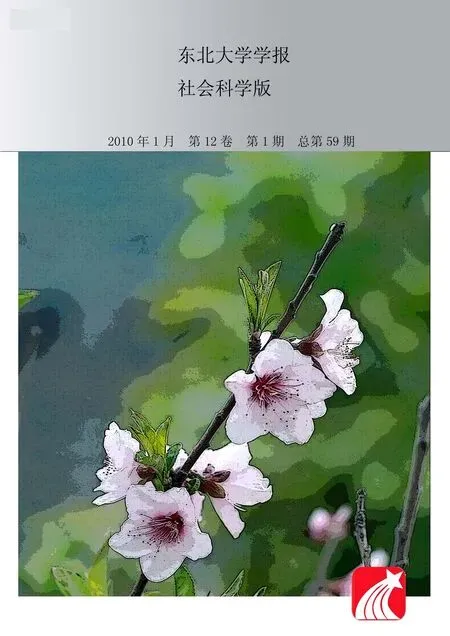三螺旋模式與知識經濟
[荷]勞埃特·雷德斯多夫,[英]馬丁·邁耶爾 周春彥譯
(1.阿姆斯特丹大學交流研究學院,荷蘭阿姆斯特丹 1012 CX; 2.蘇塞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所,英國布萊頓 BN1 9QE;3.拉薩爾大學國際三螺旋研究所,西班牙馬德里 28023)
一、 問題的提出
三螺旋已經研究了大學—產業—政府之間的關系網絡。但這些機構網絡只提供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系統的知識基礎結構。我們將知識基礎結構看做在復雜的相互作用系統中通訊流量的一個進化的保留機理。然而,除機構關系模型外,三螺旋模式還可伸展出三個選擇環境功能相互作用的新進化模型。形成知識經濟所必需的進化功能有三個:經濟財富的生成、有組織的知識生產和標準化控制。
三個選擇機制相互作用可預期生成復雜動力學[1-2]。在達爾文最初的進化論中,選擇被看做是“自然的”,即由自然賦予的。在進化經濟學范式中[3],不同的選擇環境各有不同,如市場和非市場環境等[4]。對跨不同經濟學領域的比較研究[5-6]和對不同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7-8]一直是這一傳統的核心。但如果沒有一個分析模型,我們就不能對不同選擇環境之間如何相互作用進行分析。
在三螺旋模型中的選擇動力是內生的,因為三個組織機構的活動范圍彼此兩兩關聯,而且是分布式的。因而它們對彼此的選擇作出反應。Dosi在1982年注意到兩個選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能形成一條軌道[9]。某一特定軌道可能處于一個可能的軌道空間中。由于增加了一個自由度,三個選擇環境能為整個知識經濟體系建模。
這個相互作用動力進化模型和大學—產業—政府的機構關系模型之間不再有一一對應的關系。然而,財富的創造向來與產業相關,知識生產與大學相關,而公共領域的控制則與政府或私人活動領域的管理相關。相互作用動力模型關注的是分化,而網絡關系模型反映的是整合程度。整合和分化是相伴相隨的:在功能上分化的系統能處理更復雜的事物[10],并且相互作用與交流使改變觀點成為可能[11]。
例如,大學有時能起區域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公司已成為重要的新知識生產者等,但產業、大學和政府機構的主要使命還是照舊保留(并且在一
① 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s”,即對于同一個物體,處于不同的環境的人會對其功能有不同的理解。如金錢對于普通百姓來講可以用來消費和儲蓄,而對于政府官員而言,它是社會福利,是投資,同時也可能是維護政權的基礎。----譯者注
② 對于相對較小的系數值(1 定程度上被法定下來)。因而在界面上可能會發生權衡和出現“邊界物體”①[12]。三者在社會現象中相互交織。例如,專利能在法庭上起作用,因其提供法律保護,但專利也能被用做衡量知識生產和/或經濟價值的指標。 利用這個三螺旋模型,我們能用一個三維圖像來解釋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秩序里的現象。兩個以上環境能彼此相關,因為在社會層次上推論式知識已成為除經濟交換關系和政治控制之外的第三協調機制,并且與前兩者相互作用。在此協同中這個新增自由度能被看做是知識經濟和政治經濟之間的區別性特征[13]。 在知識經濟中,除過去已經存在的政治經濟協調機制----市場交換和政治控制,有組織的知識生產和控制已成為第三協調機制[13]。在網絡節點上的部門必須具有這三個功能,但是我們不能再指望結構與功能之間會一一對應,因為這些功能基于機構之間的網絡安排[14]。有可能發生系統性影響,這些影響不能直接追溯到具體的交換關系,但因功能間相互作用的協同出現在系統的層次上。 就經濟動機推動生產功能的變化或生產功能朝其本源的創新性轉變而言,三個功能中的兩個(技術創新和經濟要素價格的變化)之間的關系能在進化經濟學中被建模[3]。創新傾向于打破經濟平衡。 當兩個功能作為選擇環境相互作用時,這兩個選擇環境間會彼此形成一條軌道[9]。穩定在某個局部最佳點上可以看做是選擇環境之間彼此共同進化的結果。 競爭的穩定性也能被看做二級變化,并且當另一個(解析無關的)選擇機制起作用時,能進一步為超穩化、亞穩化和全球化而選擇。Hayami和Ruttan(1970)[15]已經注意到一個在全球層次上的二級選擇機制。當一個軌道按照權衡結果形成蹤跡時,由環境而來的另外一個(第三個)反饋可能導致全球化或者引起作為超穩態的鎖定。或者相對穩定的軌道會成為亞穩態和分叉成兩支。于是這個控制機制從局部(和潛在穩定軌道)變換到全球的下一個或制度的層次。 讓我們利用這個邏輯方程構造選擇機制相互作用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系統x的發展變化與其過去的狀態相關,但因處于競爭環境中所以要乘上反饋(1-xt): xt+1=axt(1-xt), 0 當x的值隨時間增加時,反饋項(1-xt)阻抑這個系統的進一步發展。在技術—經濟系統的情況下,這個對于歷史性變化和增長的反饋能由作為一個選擇環境的市場來提供②。換句話說,技術發展引起基于該系統過去狀態的變化(在此為axt),但這個變化是由一個具有越來越多選擇性的環境(1-xt)來選擇的。 對于彼此競爭的人口或技術而言,如果把競爭系數(α)加到選擇機制中,那么這個邏輯方程能被推廣為所謂的Lotka-Volterra方程[1,16]。在上述邏輯方程和Lotka-Volterra方程中,選擇被建模為反饋。假定在Lotka-Volterra方程中的參數k和α都是1且沒有失去一般性,那么這個反饋(k-αx)就能被表述為(1-x)。 兩個選擇作用在一個變量v上(在方程(1)中v=axt),所生成的選擇環境能表示為: 這個所生成的選擇環境不再作為均勻場運行,因為它是個曲線。它能被描繪為圖1:包含兩個選擇的一個系統能穩定在二次曲線的最低點。當這個最低點隨著時間維度延展時,系統在其中沿著一條軌道發展,形成一個谷。Sahal稱其為 圖1 軌道形成----f(x)=v(x2-2x+1)(穩定態) “創新大道”[17],并把它們比做生態系統理論中的河床[18]。 另一個選擇的加入將導致復雜動力學(見圖2)。這道風景不再平坦,而是“崎嶇不平”[19]。 圖2 亞穩態和變遷 同理,第三個選擇環境的介入能導致下列公式: 這個三次函數能由圖2中的點線來描述。只要三個選擇機制同時作用在具有相同參數(在此情況下都設為1)的單一變量上,那么全球的和穩定的拐點就會在所謂的馬鞍點上重合。在此特殊情況下,歷史上穩定的系統就能與全球系統保持一致。也許我們能把這樣的一個系統看做包含單一軌道或Nelson和Winter的“天然”軌道[5]的系統:在這個軌道里全球最佳點和局域最佳點相一致。 圖2用帶箭頭的線顯示穩定性和全球化隨不同參數值變化的情況。在這種(更一般的)情況下,曲線會呈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最小值處,技術—經濟系統局部穩定,但在最大值點上它能被看做是亞穩態。結果導致一個分叉:這個系統可能倒退(穩定在局域的最佳點上),也可能前進(全球化進入下一個制度)。 只要系統處于穩定(即在最小值點),那么它就能沿其原來的軌道推進。但不穩定的狀態卻傾向于使系統朝另一個吸引盆移動。這個吸引是由在另一個維度上通訊的可能性引起的----這個通訊能在新出現的結構中處理更復雜的事物。局域最佳點也能被看做一個小生境----在這個小生境中技術能快速發展而沖向將其與下一個吸引盆分開的山頂。后者為局域發展提供全球的環境。 本文將利用反應—擴散動力學建模這個分叉。讓我們先看一下方程(3)的符號。二次項系數是正的,所以圖1中的曲線有最小值。如果這個符號是負的,那么另一個(第三個)子動力必定會在系統層次上起作用。由于形式的緣故,對于共同進化并穩定在最小值處的系統的兩個選擇環境而言,符號的反轉不可能是內因性的。第三個選擇機制可以增強系統原有的穩定性使其處于超穩態,也可能反轉二次項符號使系統處于亞穩態(見圖3)。 圖3 在復雜選擇環境中的技術經濟系統(a)----亞穩態; (b)----超穩態。 換句話說, 亞穩性和超穩性都表明第三個子動力在起作用。 例如, 某一政治經濟系統因兩個協調機制(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而傾向于穩定, 但知識經濟能預期顯示更復雜的動力學, 因為第三個協調機制(知識生產)正日益取代控制功能。 例如,我們能將圖3(a)和圖3(b)之間選擇環境符號的變化理解為在遞減邊際報酬和遞增邊際報酬的市場之間的不同(如Arthur的信息與通訊技術案例[20])。遞增邊際報酬在雙曲線上的亞穩點引起分叉和隨之而來的在任一分支上的鎖定。至于鎖定,即以前的亞穩系統因一個反饋增強了其他兩個子動力之間的共同進化而再次成為超穩態。 上述關于動力系統的思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在主角兒之間看得見的關系?從進化的觀點看,關系網絡為我們提供系統的足跡,或者更抽象地表述為系統動力的表現形式。當仔細研究實際例子時,我們會發現所研究的系統的功能是看不見的。換句話說,相關的選擇機制能用公式表述為假設,但只有變化能被觀察到。用公式表達假設會使實際測量與創建理論相關聯。此外,理論化還使我們能指明事物不易覺察的方面。 三螺旋模式出現在兩種理論競爭的情形下: ① “模式2”(知識生產方式)的概念是1994年由Michael Gibbons等人在TheNewProductionofKnowledge:theDynamicsofScienceandResearchinContemporarySocieties一書中提出的。他們把傳統的研究看做“模式1”,而將20世紀中葉以來出現的知識生產新方式叫做“模式2”。概言之,“模式1”知識生產方式是由研究者選題(investigator-initiated)和以學科為基礎的(discipline-based),而“模式2”則是聚焦于問題(problem-focused)和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譯者注 一是關于(國家)創新系統[8,21-23],二是對“新知識生產”或“模式2”①的推崇[24-25]。“模式2”論點的擁護者們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根本性轉變,已經在本質上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模式:學科知識越來越過時,日益被產生“跨學科”研究課題的技術—科學知識所取代。 然而,“模式2”知識生產方式專門聚焦在轉變上,創新系統的概念則指明現有安排的回復力(彈力),如同在進化經濟學中普遍存在的那樣。對此已有大量的研究,其中絕大部分都基于不同創新環境之間的系統比較[5,7-8,26]。此外有人認為單一民族國家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特殊概念為國家創新系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環境,還有學者認為部門或區域結構也可能為學科知識(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6]。 三螺旋模型利用可能的安排解釋這些不同。當三個動力中有一個保持相對靜止時,另外兩個能穩定在一條軌道上。至于三個子動力中哪一個提供這個穩定點要因具體事例和時間而異。在某項技術沿一條穩定路線引領軌道時有望出現一個部門系統。當政府能提供強有力的規章制度時(如中國政府),國家創新系統會占支配性的地位。在區域層次上,區域政府、地方大學和產業能力之間的權衡可以形成具體的小生境[26]。 大學有時能引領一個區域的發展[27],但每個小生境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比如,某個曾經處于穩定發展的區域在10年后可能因跨國公司能自己花錢進入穩定在區域層次上的創新軌道而處于混亂狀態[28]。規模和范圍的動力學可能導致全球化。 例如,在1991年當前蘇聯解體東歐國家進入轉軌經濟時,它們發展國家創新系統的雄心一方面遇到來自自由市場的阻礙,另一方面受到處于不斷發展中的歐化政治進程的干擾。匈牙利的情況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實例。它在轉型后出現了不止一個創新系統,而是三個。一個在布達佩斯附近的都市區域發展起來,作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機構和跨國公司等的所在地,與維也納、慕尼黑和布拉格等形成競爭之勢。在匈牙利西部的創新系統中,某些特殊的西歐公司的搬進影響了大學的研究議程。例如,德國奧迪汽車制造公司在匈牙利西北部城區創建了汽車產業集群,并在該區域的一所地方大學發展了自己的大學研究所。匈牙利的第三個創新系統則坐落在這個國家的東部,在那里傳統的大學和城市化提供了與舊系統相連的地方基礎設施[29]。 我們可以說,當匈牙利在歐洲出場時已為時太晚,以至于不能發展一個完整的國家創新系統,因為這個假想的系統早已被卷入歐盟體系的形成中。轉型國家同時成為歐盟的新加盟國,這段適應期對于穩定國家創新系統來講太短了。 這種“組織解體”因不同國家和國家內的不同區域而異。在這個案例中,變遷不僅是在軌道層次上的變遷,而且還是在制度層次上的變化;相互作用的選擇環境之間的復雜動力在新出現的系統的層次上被控制。然而,這個“系統”的概念不應該被具體化:相互作用的分布決定了在制度層次上的動力學。我們不能再期望有個獨斷決策的穩定中心,因為在結構和功能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已不再占優勢。 就創新系統的載體之間的反身“重疊”而言,“模式2”主題的這個版本----即過去存在系統描繪的破碎和瓦解----在三螺旋模式中受到重視[14]。這個重疊作為重構子動力反饋在基礎網絡上,生成或阻礙在某一分布模式中小生境形成的機會。這些發展可能需要新的競爭,現有學科的綜合能形成新專業。結果這些動力不再是機構關系的,而是相互作用進化的。這個觀點既是后見之明,又有前瞻性。動力產生適應性:不是以生物適應的形式,而是以意向的社會動力形式[30]。 由此,“模式2”的靈活性和強適應性不再局限于知識生產和控制系統。在產業中的合并和收購越來越受知識驅動。歐盟的情況已經改變了區域的身份地位,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可能如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況那樣變得模糊,或者像在比利時那樣不斷變化。在新體制中,系統保持“無盡的轉變”。然而,這個“無盡的轉變”并不意味著“任何事情都會發生”,恰恰相反,它是在選擇壓力下力量和競爭優勢不斷重組的過程[26]。這個選擇過程是知識密集的。 ① Mirowski和Sent諷刺地用“公司的”、“政府的”和“教育的”(CGE)取代三螺旋(TH)的機構范圍。在他們看來,CGE更適合STS的權威表述,而三螺旋是在用一個“非學術”術語。 ② Bayh-Dole:多譯為“杜拜法案”,這里保持與《三螺旋》一書的譯名一致。譯者注 ③ 在單個吸引盆內產生的動力和根據Kauffman的NK-模式(1993)對崎嶇不平的適合度景觀的預言相一致。參見Frenken, K.AComplexityApproachtoInnovationNetworks:TheCaseoftheAircraftIndustry(1909-1997). Research Policy, 2000,29(2): 257-272; Leydesdorff, L.TheComplexDynamic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AComparisonofModelsUsingCellularAutomata.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2002,19(6):563-575. 盡管三螺旋模式首先確定一個理論研究議程,但三螺旋主題也被新組合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付諸實踐,用于政策制定過程。不過就創新政策而言,新自由主義和新組合主義并不是彼此排斥的。例如瑞典國家創新代理處(Vinnova)已將“三螺旋”作為它的官方戰略[31],因為這個模式與這個國家的新組合主義傳統相一致。按照Mirowski和Sent等人的觀點①,大學的進一步商業化是由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產生的。 交叉網絡的新機構模型可能會讓研究人員認為大學—產業—政府關系的經驗實例能被學習,但新進化模型的重點一直在于找到對以知識為基礎系統的動力學解釋。關系的缺少可能和它們的存在同樣重要;關鍵在于經驗分布,即可觀察到的變化和潛在選擇機制的理論規范說明。正是因為在網絡中載體和功能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不能再被假設,所以這些相關環境必須通過聯網機構所具有的功能起作用。 例如,關于“資本主義的多樣性”的辯論[32]忽視了作為差異的獨立來源的知識生產功能,幾乎只聚焦在政治經濟方面的不同。類似地,由于法律法規條件----政府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大學—產業關系的“最佳實踐”可能不會在區域間轉移。不是兩個而是三個不同的選擇機制被涉及到以知識為基礎的系統中:尋求經濟平衡、知識生產和組織控制。 三螺旋模式鼓勵研究人員在研究設計過程中討論這三個功能,從而使這個解釋更加充實。例如,Van Looy等人(2007)在對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時發現Bayh-Dole②之類的法規的采用對大學申請專利有獨立的影響[33]。增幅由德國的250%或比利時的300%到丹麥的500%。對比利時情況的較細分析顯示:大學必須保證發明活動不會危及到教學與科研。此外,每一所大學都必須設法保證對研究人員和研究小組申請專利的投資獲得公平回報。 三螺旋模式的新進化模型沒有規定人們“應該”在局域網絡和區域發展服務方面進行合作,但它提出一個三維設計分析子動力之間的分化和整合。我們可以希望加上更多的維度進行分析[34-35]。但要進行復雜系統分析,若只利用三個動力中的兩個之間的單一“共同進化”,僅僅聚焦在一個整合軌道上,僅僅關注可能在后續階段分叉的某一階段的結構,就低估了這種復雜性。 當發展在某一小生境中處于超穩定時,系統是鎖定的,沒有足夠的能力為未來的發展吸收新的變體;換句話說,它已達到進化周期的末端。如前文所述,這個結構(必需)基于三個相互作用的選擇機制:第三個選擇機制把生命周期引向這個軌道③。那么怎樣從假定第三個選擇環境的模型的觀點思考出自鎖定的“爆發”? 前面我們說過,可以求助于反應—擴散動力學來理解這個可能性[36-37],[3]182。反應—擴散動力學已在自然科學中被詳細說明。如果兩個系統緊密耦合(共同進化)(見圖4),那么最簡單的耦合機制能由下列微分方程表示: 圖4 兩個系統耦合過程[3]183 讓我們假設x在兩個系統里以恒定的和相等的速率S產生。參量a代表x的衰減;D是透過界面的擴散常數(為求簡單的緣故,假定這些參量在兩邊是相等的)。擴散是不均勻的,取決于x1和x2在兩個系統里的濃度。這個系統方程提供恒穩態的值: (6) 此時兩個環境中x的濃度相等,系統是均勻的。然而,系統運行的穩定性是由方程(5a)和(5b)中x1和x2的系數矩陣的特征值決定的。這個矩陣是: 這個系統的兩個特征值是: λ1=a;λ2=2D-a(7) 盡管第一個特征值λ1總是負的,但如果D>a/2,第二個特征值λ2就能是正的。因而,如果x向另一個系統的擴散比在這個生產過程中的通量(除以2)更重要,那么正的和負的特征值就能同時共存。接著系統就變成不穩定的,因為在這個相圖中產生了一個馬鞍點。任何與這個均勻性的偏離都將被放大,系統會經歷一個相變。 相變不可逆轉地改變系統動力。就兩個先前耦合的動力來說,分叉導致極化,即所有材料都在一個或另一個隔間里的情況。哪一個子動力占優勢將取決于可能由第三個環境提供的對均勻性的最初的(和潛在隨機的)偏離。因而反應—擴散動力學使我們能理解在單一技術和市場動力之間的鎖定怎樣在后來被解除,例如:當市場擴散機制不再與生產機制共同進化時,沿單一軌道的共同進化就會被“解鎖”。 在一個創新型企業或工業區內,生產與銷售可以緊密地共同進化。如果某個較小的生產單位被跨國公司吞并或相反被國際化了,那么在生產和銷售之間的這個緊密耦合就可能限制其進一步發展。于是朝全球擴散的壓力就可能允許對技術—經濟系統進行重新配置的決定,越來越多地改組生產過程。熊彼特本人在1912和1942年分別區分了基于市場低密度的啟動階段和創造性破壞(Mark Ⅰ)與基于市場高密度的退出階段和創造性分配(Mark Ⅱ)之間的不同[5,38-41]。 當另一環境成為與先前鎖定的某一系統相關的選擇環境時,一旦在新界面上的擴散大于沿系統軌道擴散速率的一半(如方程(7),D>a/2),那么這個新配置就開始使系統傾斜。因為經濟生產體系被市場機會所吸引,所以我們期望一個軌道被開發出來以獲取市場份額。為此技術的擴散率有望增加。既然這樣,以前的鎖定會在更長期間里內生地侵蝕它的存在狀況。在上述圖3(a)和圖3(b)之間反饋箭頭是反向的。 例如,VHS視頻錄像機在20世紀90年代是標準的和主導的技術。CD沒有改變這一點,因為視頻資料不能被錄制在它上面。但DVD作為潛在替代品日益與之相關,而這并不意味著鎖定馬上就被中止。現行系統是有彈性的!然而再過一陣子,當DVD的分量因其他原因(如它的超強數據存貯特征等)自行增加時,系統開始傾斜,一個替代作用過程引起一個遠離VHS的小瀑布,朝向一個全新的系統動力學。這個新出現的鎖定遵循替代技術曲線[42]。對于上述圖2和圖3(a)的圖像而言,就是系統移上山頂和流入另一個吸引盆。 總之,系統可能被鎖定到一個非最佳配置,因為適合度景觀可能是崎嶇不平的[19,43]。沿某一特定的軌道,這個技術—經濟系統是抗干擾而相對穩定的。當崎嶇不平的景觀本身作為第三個選擇環境成為動力時,反應—擴散動力學可以打開這個鎖定。這個新形成的系統可能出乎意料地成為對系統先前鎖定的侵蝕的結果,因為系統在進入下一個全球化之前必須是穩定的。 機構安排能比以前更靈活得多地在合作和競爭中被形成和解除。一個新的社會契約在作為實現知識生產功能的主要合作者(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形成了。例如,專利申請已成為大學的合法功能,盡管不是其核心功能,如同“模式2”的擁護者和三螺旋主題的機構關系模型曾經預言的那樣[44]。大學的第三使命仍然是其潛在的使命,包括新的教育形式、孵化和長期為社會盡義務。 我們的模式受Luhmann的新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啟發。這些功能是作為協調機制歷史地形成,或者用Luhmann的話說:社會通訊子系統因所調停的事物和原因而異。可以把這些通訊中的控制系統看做作為通訊代碼起作用的潛在功能[45]。在許多可能的通訊代碼中,有些已更多地被用符號概括。當通訊代碼被用符號概括時可能會有不同的功能。 經濟交換(在市面上的“價值”)和政治控制(“權力”和合法性)在形成19—20世紀的政治經濟中起了主導作用。19世紀的“科學與實用技藝的婚禮”[46]觸發了朝20世紀的知識經濟的逐漸變遷。這個過程只能在冷戰結束后被完成,冷戰在本質上是關于怎樣組織政治經濟的一場戰爭。 在知識經濟中,“權衡”已取代了為獲取支配控制權而進行的競爭。在社會協調機制之間的權衡能通過使它們更加以知識為基礎而得到改善[9]。我們堅持主張:沿三個主軸進行權衡的系統與不能利用第三個軸(即科學與技術)的系統包含不同的結構動力,第三個軸既可以作為資源又可以作為投資起作用。三螺旋的新進化模型使我們能辨別軌道和作為分析結構的制度,也使我們能理解“鎖定”和“爆發”。關于這個模式本身的決定性作用的自反性反過來又提出該模式的功能問題。 三螺旋進化模式考慮大學—產業—政府三維結構關系,不再考慮認知模式,在方法論上作為外部和潛在中立的“觀察者”,或者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上作為外在驅動器,使分析家們能確定在私有財產和利益最大化之間的關系、作為法律法規的公共控制功能和在經驗事例方面的技術—科學創新動力,以此為解決當代社會主要功能界面上的問題做出貢獻。事實上,這是一個跨學科的事業,但分析和經驗性工作要比在“模式2”中更具體。對比Nowotny等人[47]對“強”脈絡化的綱領性強調而言,我們贊成致力于在具體界面上分析和經驗地了解去脈絡化和以知識為基礎的重構。 致謝: 感謝Andrea Scharnhorst和Wilfred Dolfsma在本文發表前所給予的評議。 參考文獻: [1]May R M.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with Very Complicated Dynamics[J]. Nature, 1976,261:459-467. [2]May R M, Leonard W J. Nonlinear Aspect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ree Species[J]. SIAM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975,29(2):243-253. [3]Schumpeter J.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cess[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4. [4]Von Hippel E.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Nelson R R, Winter S 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6]Carlsson B.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J]. Research Policy, 2006,35(1):56-67. [7]Lundvall B.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M]. London: Pinter, 1992. [8]Nelson R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Dosi G.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J]. Research Policy, 1982,11:147-162. [10]Luhmann 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M].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11]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M]. London: Hutchinson, 1976. [12]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48(6):781-795. [13]Leydesdorff L.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odeled, Measured, Simulated[M]. Boca Raton, FL: Universal Publishers, 2006. [14]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29(2):109-123. [15]Hayami Y, Ruttan V 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60(5):895-911. [16]Reggiani A, Nijkamp P.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Technological Systems: A Multi-layer Niche Approach[M]∥Leydesdorff L, van den Besselaar P.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haos 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Technology Studies. London: Pinter, 1994:93-108. [17]Sahal D. Technological Guideposts and Innovation Avenues[J]. Research Policy, 1985,14:61-82. [18]Waddington C H. The Strategy of Gene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7. [19]Kauffman S A. The Origins of Order: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Evolu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M]∥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1988:590-607. [21]Freeman C.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M]. London: Pinter, 1987. [22]Lundvall B-. Innovation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from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 to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M]∥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1988:349-369. [23]Lundvall B-.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M]. London: Pinter, 1992. [24]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4. [25]Nowotny H, Scott P, Gibbons M.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M]. Cambridge: Polity, 2001. [26]Cooke P, Leydesdorff L.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tage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6,31(1):5-15. [27]Etzkowitz H, Webster A, Gebhardt C, et al.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J]. Research Policy, 2000,29(2):313-330. [28]Beccatini G, Bellandi M, Ottati G D, et al. From Industrial Districts to Local Development: An Itinerary of Research[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29]Lengyel B, Leydesdorff 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Hungary: The Failing Synergy at the National Level[EB/OL]. [2009-10-20]. http:∥users.fmg.uva.nl/leydesdorff/hungary-th6/index.htm. [30]Leydesdorff L. The Non-linear Dynamics of Meaning-processing in Social System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9,48(1):5-33. [31]Rothwell R, Zegveld W.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M]. London: Pinter, 1981. [32]Hall P A, Soskice D W.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van Looy B, Du Plessis M, Meyer M, et al. The Impact of Legislative Framework Condition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Triple Helix Conferenc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7. [34]Leydesdorff L, Sun 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Triple Helix in Japan: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Versus International Co-authorship Relatio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60(4):778-788. [35]周春彥,亨利·埃茨科維茲. 雙三螺旋:創新與可持續發展[J].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8(3):170-174. [36]Rashevsky N. An Approach to the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of Biological Self-regulation and of Cell Polarity[J]. Bull Math. Biophys, 1940(1):15-25. [37]Turing A M. The Chemical Basis of Morphogenesis[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Series B, 1952,237:37-72. [38]Rosen R. Anticipatory Systems: Philosophical, Mathema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5:182. [39]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40]Schumpeter J.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3. [41]Malerba F, Orsenigo L. Schumpeterian Patterns of Innovation are Technology-specific[J]. Research Policy, 1996,25(3):451-478. [42]Leydesdorff L, Van den Besselaar P. Competing Technologies: Lock-ins and Lock-outs[M]∥Dubois D M. Computing Anticipatory Systems: CASYS'97. New York: Woodbury, 1998. [43]Frenken K.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Complexity Theory[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5. [44]Leydesdorff L, Meyer M S. The Decline of University Patenting and the End of the Bayh-Dole Effect[EB/OL]. [2009-10-26]. http:∥users.fmg.uva.nl/leydesdorff/Bayh-Dole/index.htm. [45]Maturana H R, Varela F.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M]. Boston: Reidel, 1980. [46]Noble D. America by Design[M]. New York: Knopf, 1977. [47]Nowotny H, Scott P, Gibbons M.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M]. Cambridge: Polity, 2001.二、 分析模型



三、 知識經濟和創新系統
四、 三螺旋模式的規范影響
五、 分叉和進化


六、 結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