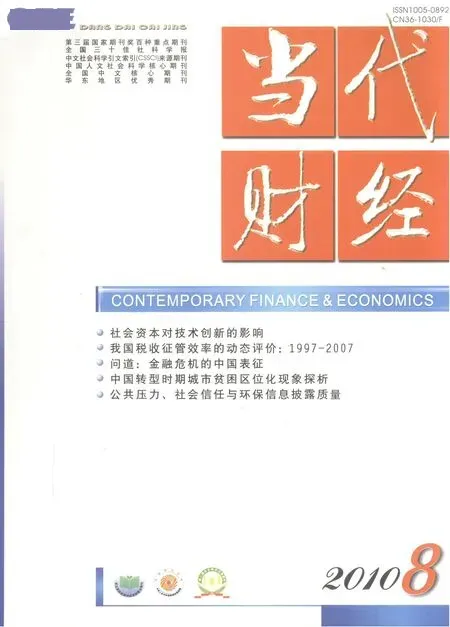學習效應、規模經濟與內生增長
殷德生
(華東師范大學 金融與統計學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
比較優勢理論已從靜態分析發展到了動態分析,這在解釋規模經濟對內生經濟增長的影響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新貿易理論之前,無論是基于勞動生產率差異的比較優勢理論還是基于資源稟賦差異的比較優勢理論,它們都將分工與貿易形成的原因歸于經濟體系的外部條件,或者說比較優勢是靜態的,無法解釋產業動態演進的原因以及貿易與內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種理論的反思直到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出現后才開始有了新的解釋方法。[1]
Dixit和Stiglitz(1977)將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的解決方法歸于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國際貿易正好具有這樣的效應,這也正是Krugman(1979,1980,1981)、Krugman和Helpman(1985)所發現的該模型能運用于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分析中的關鍵。[2-5]新貿易理論就以規模報酬遞增來解釋產業的動態演進以及貿易對內生經濟增長的影響渠道。這種基于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顯然是后天的、動態的;而李嘉圖意義上的先天(外生)比較優勢卻是靜態的。由于靜態的比較優勢不可能演進,而動態的比較優勢隨著時間演進,所以新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可以用來解釋內生經濟增長。
至于如何界定動態比較優勢的問題,Redding(1999)對此做出了解釋:當且僅當一國在時點t上關于i部門生產活動的機會成本增長率比其他國家低時,該國在時點t上關于i部門的生產活動才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該定義是將外部效應與動態比較優勢結合起來考慮的。Redding強調,一國根據當期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自由貿易可能導致福利損失,因為該國可能放棄了在其他部門潛在的學習效應。因此,一國為了避免這種“比較優勢陷阱”,往往是根據自身學習能力來選擇國際分工。也就是說,學習效應(“干中學”效應)是動態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6]
如何利用“干中學”效應和規模效應,將初始劣勢轉變為比較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雖然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韓國的汽車產業、中國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中國的機械行業等后來居上,但缺乏科學的理論解釋。“干中學”效應模型對于理解動態產業選擇和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干中學’模型更有希望幫助我們理解貿易和增長的關系”(盧卡斯,2003)。“我懷疑是否能在一個沒有外部效應的理論模型上,解釋我們觀察到的各國之間增長率的巨大差異”(盧卡斯,2003)。[7]“人類的整個智慧發展史實際上就是外部效應傳播史”(Lucas,1988)。[8]
“干中學”效應不僅加速了要素的集聚,而且強化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Rivera和Romer(1991)分析了經濟一體化(自由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體化不僅避免了研發部門中的重復工作,而且使經濟增長表現為知識溢出引起R&D生產函數中投入規模的上升。[9]“紐約的時裝區、金融區、珠寶區、廣告區以及其他類似區域同哥倫比亞大學或紐約大學一樣,都是知識中心……在外人看來更是如此:一群人做著幾乎相同的事,但每個人都強調自己工作的原創性和獨特性”;“如果人們不是為了與他人更加接近,那么他們支付曼哈頓或芝加哥市中心的租金又是為了什么呢?”(盧卡斯,2003)。對于“亞洲四小龍”“增長奇跡”的解釋,Lucas(1988)指出,“一個強調學習效應的模型可能有助于解釋這些現象”。
本文試圖構建一個邏輯一致的模型,考慮國家規模、產品種類數與產品復雜性等變量,更為細致地解釋市場規模、國家規模和學習效應對產業選擇與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解釋“中國奇跡”提供理論框架。
二、文獻評述
(一)學習效應、規模經濟與產品種類數增加
Krugman(1987)將動態比較優勢和學習效應同時內生化,分析貿易模式的決定問題:部門特定的累積生產經驗決定著比較優勢和貿易模式,而生產經驗的積累是通過“干中學”實現的;學習效應通過貿易品種類數的增加而提高,貿易開放后貿易品種類數增加通過學習效應形成比較優勢。[10]

產品種類數的增加意味著不同產品具有不同學習效應。Krugman(1987) 沒有考慮該情形,Lucas(1988)對此進行了研究。在他看來,單要素(人力資本)假設下的每一產品的生產和技能的積累都取決于該產業中的平均技能水平。生產消費品i所投入的人力資本hi(t)隨著生產商品i的時間份額 ui(t)的上升而上升,即h˙i(t)=hi(t)δiui(t)。當ui(t)=1時,hi(t)達到最大增長率δi,這體現了“干中學”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Lucas強調,當一種商品的學習效應較強時,人力資本水平上升對生產率產生直接的正效應,但同時引起了貿易條件惡化的負效應。為保證開放經濟中存在正的凈效應,需要保證該商品的產出增長率大于另外一種商品,此時對應的正是規模報酬遞增的情形。選擇生產不同的商品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人力資本積累率,比較優勢取決于以前所積累的商品專有的人力資本水平。Lucas(1988)特別強調新產品不斷被引入(產品種類數增加),否則學習效應就無法保證規模報酬遞增。
(二)學習效應、規模經濟與產品質量提升
Stokey(1988)根椐學習效應分析產品結構的內生變化過程,他從靜態角度描述了“干中學”的前向溢出效應大于后向溢出效應的情形,即“干中學”所引起的高質量產品成本的下降程度大于低質量產品的成本下降程度。[11]Stokey(1991)將該模型進行了開放化處理并強調,發達國家因其在生產經驗積累方面具有優勢而在高質量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欠發達國家在低質量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優勢。[12]Stokey(1991)的靜態模型未能將增長納入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該任務由Young(1991,1993) 完成。[13-14]

在Young(1991,1993)模型中,產品的復雜程度隨產品數量的增加而上升,學習效率隨著產品復雜程度的上升而增加,一般技術知識存量的變化要取決于這種學習效率。Young進一步考察了貿易的作用。若本國比外國發達(經濟規模大),則本國專業化生產復雜產品,因為新產品處于產品周期的引入階段,學習效應強;與此相反,欠發達國家專業化生產簡單產品。但Young也預言了窮國趕超富國的可能:當窮國的人口規模擴大產生很強的規模效應時,學習效率的提高使得技術差距消除的可能性存在。在“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下,一國如果能很好地將資源集中于其現有能力所能達到的技術水平,產品的生產就越容易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Lucas(1993)認為,“東亞奇跡”就是這樣發生的,即不同經濟的不同增長速度是源于其勞動力從簡單產品部門轉向復雜產品部門。經濟就是通過不斷生產更優質的產品來獲得進步,因為更優質的產品具有更強的“干中學”效應。[15]
三、學習效應、規模經濟與產業選擇
Redding(1999)繼承了Krugman(1987)的思路,強調比較優勢是由“干中學”效應隨時間演進而內生決定和動態變化的。但Redding分析的側重點在于政策干預的福利效果。雖如此,該模型的基本結構還是給我們分析學習效應下的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選擇提供了分析模式。賈良定(2002)將Redding的思路應用于企業內部專業化分工選擇上,討論了產業均衡問題。[16]殷德生(2006) 在Redding模型和賈良定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引申:一方面將賈良定模型擴展到國家分工領域;另一方面將Redding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延伸到分工模式的選擇上來,以解決按初始比較優勢分工與按潛在比較優勢分工之間的兩難問題。[17]這里進一步擴展殷德生(2006)模型,考慮進國家規模變量,更為細致地解釋市場規模、國家規模和學習效應對產業選擇的影響。
假設“世界”由兩個國家(國家1和國家2)、兩種商品(簡單產品z和復雜產品h)構成。復雜產品的“干中學”效應大于簡單產品。國家i(i=1,2) 關于產品j(j=z,h) 的生產函數取決于國家i投入到產品j上的要素數量(Lij)和勞動生產率(Aij),即Yij=AijLij。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A˙ij(t)=ξij(t)Aij(t),勞動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經驗的積累水平ξij(t),而ξij(t)取決于產品j的要素投入水平和國家i的“干中學”效應大小μij,即ξij(t)=μijLij(t)。根據Redding(1999) 的方法,將動態比較優勢描述為Aij(t)=Aij(t0)eξij(t-t0)。假設在任何時點t上,國家i在產品j的生產上的最優資源配置為Liz(t)=βLi、Lih(t)=(1-β)Li。國家i的總要素為Li,該變量反映的是國家規模。
(1)自給自足情形下的福利
自給自足情形時國家i在產品z和h生產上的經驗積累速度分別為:

“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使得此時國家i在產品z和h生產上的生產率分別為:

代表性消費者將收入的α份額用于z產品的消費,1-α份額用于h產品的消費。根據(1)、(2)式,自給自足時國家i關于其資源的平均跨期福利為:

(2)按初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時的福利
假定國家1專業化生產z,國家2專業化生產h。從靜態意義上看,在完全專業化的情形下,兩國的經驗積累速度分別為:

“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使得此時國家1在生產產品z上的生產率與國家2在生產產品h上的生產率分別為:

根據(4) 和(5)式,按初始比較優勢分工時國家1關于其資源的平均跨期福利為:

(3)按潛在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時的福利
從動態意義上看,勞動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經驗的積累,而生產經驗的積累又取決于學習能力的大小和資源投入量。一國若按初始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于產品z的生產,則意味著放棄了產品h上的學習機會。也就是說,在動態比較優勢下仍按初始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可能會造成福利損失。因此,一國在產業分工選擇上存在著是按初始比較優勢還是按潛在比較優勢進行選擇的難題。
假如國家1按初始劣勢專業化生產產品h,那么國家1在產品h上的生產經驗積累速度為ξ*1h=μ1hL1;在理論上與之相對應的情形是,國家2在另一種產品(假如為產品z)生產上的經驗積累速度為ξ*2z=μ2zL2。類似于vT1(t0)的計算,此時國家1關于其資源的平均跨期福利為:

比較優勢會隨著“干中學”效應的增強而演進,這使得國家1的產業選擇問題顯得復雜。國家1專業化生產產品z,該行為產生三種效應:一是增強了其在產品z上熟能生巧的能力,生產經驗積累速度提高;二是放棄了在產品h上潛在的學習能力,從而可能惡化潛在的比較優勢;三是雖然本國放棄了在產品h上的學習能力,但由于自由貿易,A國享有外國在產品h上因熟能生巧產生的收益。
第一種影響的效應是正的,但第二和第三種影響的凈效應是不確定的。因為,自給自足結構下國家1在產品h上的生產經驗積累速度既有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外國在完全專業化分工結構下在產品h上生產經驗的積累速度,其取決于產品的市場規模、國家規模以及學習能力等參數。因此,本國在按初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可能會導致福利的下降。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如果不按初始比較優勢而是按初始劣勢生產復雜產品,在“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下,其可能會改變初始劣勢而在高技術產品生產上形成比較優勢。

命題1:一國在進行產業選擇時力圖傾向于市場規模份額大的產品生產,至少不愿意放棄市場份額大的產品生產,無論這種產品是具有初始比較優勢還是初始比較劣勢。


命題2:國家規模具有優勢的國家在產業選擇時更看重產品的市場規模效應和“干中學”效應,無論這種產品是具有初始比較優勢還是初始比較劣勢。

復雜產品h的“干中學”效應要強于簡單產品z,顯然,一國傾向選擇“干中學”效應強的產品進行分工。對于自給自足與按初始比較優勢分工的選擇問題,其他條件不變時,只有當具有初始比較優勢的產品的學習效應足夠強時,國家1才會專業化生產它。如果某種產品的“干中學”效應非常強,但不是該國的初始比較優勢,此時的分工選擇應該怎樣呢?
命題3:學習效應對動態比較優勢具有決定性作用。一國總是傾向于選擇“干中學”效應強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無論這種產品是具有初始比較優勢還是初始比較劣勢。
四、學習效應、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
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內生增長模型強調,規模報酬遞增是由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引起的。[18]Barro和Sala-I-Martin(1995)將生產經驗對生產率的正向影響稱為“干中學”效應,而該效應的形成也是通過投資實現的。[19]“一個增加了其物質資本的企業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產”(巴羅、薩拉伊馬丁,2000)。[20]知識的溢出效應不僅自身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而且使物質資本和勞動也具有了規模報酬遞增的特征。Lucas(1988)所闡述的外部性是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這種效應也是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動態比較優勢的源泉。Barro和Sala-I-Martin(1995)刻畫了人力資本外部效應同時使物質生產部門與教育部門產生規模報酬遞增的情形。
我們進一步對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具有物質和人力資本的單部門模型進行引申,分析在熟練勞動(H)和非熟練勞動(L)兩種要素投入的情形下學習效應對規模報酬遞增的影響。
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學習效應會使得非熟練勞動的技能水平上升,同時,學習效應總是要與吸收能力相適應,因此非熟練勞動也需要投資。采用簡單的Cobb-Douglas型生產函數,于是有: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的投資函數分別為:


在(9)式中,IL、IH分別為非熟練勞動和熟練勞動的總投資,ηL、ηH分別為學習效應對非熟練勞動和熟練勞動增加的影響。為分析方便,我們將學習效應對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增加的影響程度視為相等,即 ηL=ηH=η。
經濟體中的代表性消費者面臨著效用最大化的問題,即:

其中,ct為時間t時的人均消費量,ρ為正的不變的時間偏好率。
根據代表性消費者的最大化問題構建 Hamilton方程,由其最優一階條件可得平衡增長路徑上的經濟增長水平,即:

由 (11) 式可得:

根據(12)式,學習效應(η)影響著一國經濟增長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影響著學習效應程度。這兩種影響我們可以總結為推論1:
推論1:學習效應的增強對一國經濟增長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呈正向影響。學習效應引起的規模報酬遞增是比較優勢的一個來源,其作用渠道是一國的人力資本水平。


推論2:自由貿易促進著貿易國學習效應的提高。大國是通過創新產品市場規模擴大實現的,小國是通過知識溢出規模擴大實現的。

推論3:在自由貿易過程中,基于學習效應和規模報酬遞增的動態比較優勢意味著增長的不確定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存在著趕超的可能。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干中學”效應和規模效應,避免陷入“比較優勢陷阱”,這是發展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本文通過一個邏輯一致的理論模型,考慮國家規模、產品種類數與產品復雜性等變量,更為細致地解釋市場規模、國家規模和學習效應對產業選擇與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國在進行產業選擇時力圖專業化于市場規模份額大的產品,至少不愿意放棄市場份額大的產品生產,無論這種產品是否具有初始比較優勢。產業選擇也要受國家規模的影響,國家規模具有優勢的國家在產業選擇時更看重產品的市場規模效應和“干中學”效應,無論這種產品是否具有初始比較優勢。發展中大國如果選擇生產“干中學”效應強的初始劣勢產品,隨著學習能力的增強,就可以在該產品上獲取比較優勢。
學習效應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水平而作用于一國的內生增長。學習效應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形成正向影響的傳導渠道是,通過貿易開放所形成的知識與技術溢出效應,使物質生產部門與教育部門同時產生規模報酬遞增。基于學習效應和規模經濟的內生增長存在著不確定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存在著趕超的可能,這為成功解釋“東亞奇跡”以及“中國奇跡”提供了理論基礎。
本文的結論對中國開放30年來產業不斷升級的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中國日益從廉價最終產品生產國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的生產地。例如,中國所出口的個人計算機和相關組件就已超過了金屬制品。從1990-1994年到2000-2004年,中國的辦公和通信設備在全部出口中的份額從6%增加到22%;電子設備的份額從4%增加到10%;增幅尤以機械產業最大,即從17%增加到41%,其中,發電設備的市場份額翻了一番,工業機械提高了2倍,電力機械是原來的4倍(World Bank,2007)。[27]與出口結構相似,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也在顯著提升,這尤其體現在辦公和通信設備、電力機械、工業機械等中間產品進口份額的快速上升上。難怪Rodrick(2006)直接將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歸結為,中國出口的產品日益傾向于高生產率和高復雜程度的產品,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所反映的收入水平比其實際收入水平高出3倍。[28]或者說,成功的秘訣就是發揮了“干中學”效應,將初始劣勢產業發展成為了比較優勢產業。
[1]Dixit A.K.,Stiglitz J.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67:297-308.
[2]Krugman P.R.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9,(9):469-479.
[3]Krugman P.R.Scale Economic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950-959.
[4]Krugman P.R.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959-973.
[5]Helpman P.R.,Krugman P.R.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The MIT Press,1985.
[6]Redding S.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R].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5-39.
[7]盧卡斯.經濟發展講座[M].羅 漢,應洪基,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8]Lucas R.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9]Rivera-Batiz L.A.,Romer P.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530-555.
[10]Krugman P.The Narrow Moving Band,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7,27:41-55.
[11]Stokey 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Good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6:701-717.
[12]Stokey N.The Volume and Composition of Tra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9,58:63-80.
[13]Young A.Learning by Doing and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106:369-405.
[14]Young A.Invention and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443-472.
[15]Lucas R.Making a Miracle[J].Econometrica,1993,61:251-272.
[16]賈良定.專業化、協調與企業戰略[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7]殷德生.報酬遞增、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內貿易[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18]Romer P.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1002-1037.
[19]Barro R.J.,Sala-I-Martin X.Economic Growth[M].McGraw-Hill Inc,1995.
[20]巴羅,薩拉伊馬丁.經濟增長[M].何 暉,劉明興,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1]Coe D.,Helpman 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859-887.
[22]Coe D.T.,Helpman E.,Hoffmaister.North-South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107:134-149.
[23]Eaton J.,Kortum S.International Patenting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Theory and Measurement[J].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view,1990,40:537-570.
[24]Keller W.Knowledge Spillovers at the World’s Technology Frontier[R].CEPR Working Paper,2000,No.2815.
[25]Keller W.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120-142.
[26]Grossman G.,Helpman E.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1.
[27]World Bank.An EastAsian Renaissance?IdeasforEconomicGrowth[R].TheInternational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