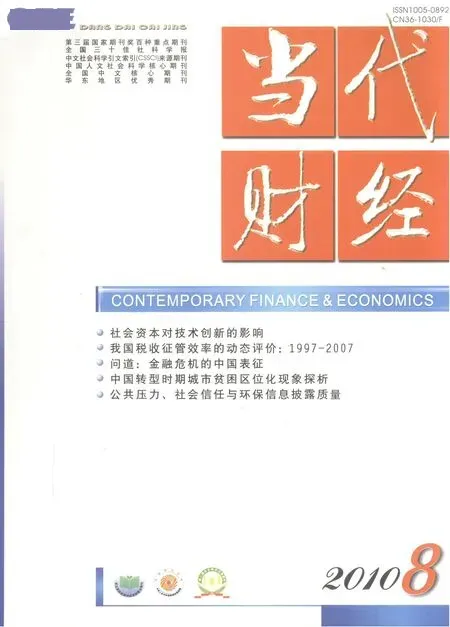中國轉型時期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探析
高云虹
(蘭州商學院經貿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一、問題的提出
所謂“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是指城市社區內的貧困人口在城市生態位置上處于較集中的狀態和發展趨勢。[1]與此有關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即已出現明顯的貧民集中區。城市地理學家厄內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1925)同心圓理論(Concentric Zone Model)中的過渡地帶(Zone of Transition),即是緊鄰中心商務區的混合地帶,以下層階級的居民為主,集中了低級破舊的住宅區、貧民窟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如猶太人區、西西里人區、唐人街等)。[2]霍伊特(Homer Hoyt,1939)通過對住宅租金的研究,指出低級住宅區不完全按照同心圓狀分布,隨著高收入階層的外遷,低收入階層也可能遷入棄置的原高級住宅區,并在地域上形成扇形模式(Sectoral Model)。[3]哈里斯和烏爾曼(Harris和Ulman,1945)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則指出,有些城市具有兩個以上的中心,低收入和貧困階層可能圍繞中心商業區、批發商業區、重工業或輕工業區聚居。[4]
此后,學者們通過不斷修正這三大經典模型,指出在美國的郊區化進程中,城市CBD外緣、中心區內部仍然是低收入和貧困階層的聚居區。[5-6]如懷特(White,1987)在其所構建的21世紀城市模型中指出,貧困階層聚居在CBD周邊的停滯發展地帶,部分與紳士化區域相連,少數民族聚居區呈現扇弧型插入中心區。[7]但是,一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如麥吉(T.McGee,1967)對東南亞港口城市研究后提出的Desakota模型,[8]卻表明城市貧困階層的聚居區主要分布在城市邊緣區或城鄉結合地帶。在佛得(Ford,1993、1996)關于印度尼西亞和拉丁美洲的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那些擅自占地非法建設區(Squatter)往往分布在城市邊緣地區。[9-10]
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在一些大、中城市,隨著城市社會分層現象的加劇,城市社會空間結構也因而出現較為明顯的分異特征,其貧困人口顯現出在特定地理空間的聚居趨勢。[1][11-16]在“城中村”、“城市飛地”、“外來人口聚居區”、“少數民族聚居區”、“危房改造區”等相關問題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城市貧困人口的聚居問題。但是,我國經濟社會雙重轉型背景下的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無論是其表現形式還是形成原因,都有著自身不同于別國的特點。本文將基于我國轉型時期城市貧困人口的兩大主體,即下崗失業職工和進城農民工,分析其在城市特定地域范圍內的聚居趨勢,并探尋促使這一現象形成的根源,以期為緩解或改變此狀況提供理論依據。
二、我國轉型時期城市貧困人口區位化現狀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受到單位福利分房以及收入分配上平均主義的影響,我國各大中城市居民的區位分化并不明顯。但隨著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場因素也正逐步成為影響城市社會空間重構的主要因子,城市貧困人口的區位化現象也因而迅速凸顯出來,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特征:一方面,一些虧損或破產的國有企業職工區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另一方面,貧困人口更多是集中在城市外圍社區基礎建設嚴重不足的地區,如城鄉交界處,并以城中村、棚戶區等形式逐步形成較大的貧困人口聚居區,其中也包括大部分的農民工,他們作為我國大中城市流動人口的主體,“聚居”是其進城后長期的、主要的居住模式,且以籍貫相同的地緣和職業相近的業緣為特征。
《中國轉型時期城鎮貧困的測度與反貧困政策評估》課題組2005年8月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所調查三城市的低收入戶中,廣州市約有91.2%的家庭居住在城區,其中44.6%居住在市中心;武漢市約有78.3%的家庭居住在城區,其中12.9%居住在市中心;蘭州市居住在近郊的低收入家庭所占比重較高,約為53%,另有24%的人口居住在城區。這部分低收入群體主要由一些國有企業的下崗和失業職工構成,居住的也主要是原有單位當時的福利分房,從住宅式樣來看,主要是普通樓房。廣州、武漢和蘭州三市居住在普通樓房的家庭所占比重分別為58.5%、67.7%和53.7%;居住在普通平房的家庭所占比重分別為17.0%、30.8%和29.0%;有少數家庭(廣州市約4.1%、武漢市約1.5%、蘭州市約9.2%)居住在條件更差的地方。
考察廣州市和武漢市的流動人口可知,廣州市約有57.1%的人口居住在郊區,其中45.4%居住在近郊,11.7%居住在遠郊。武漢市的流動人口中,居住在城區的則占多數,約為65.6%,31.3%居住在近郊,住在遠郊的為極少數。造成這種聚居格局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房屋租費和交通費用的對比。此外,兩市的流動人口均以租住私房(包括獨租和合租)或住集體宿舍為其主要居住形式(見表1),生活設施簡陋。

表1 廣州市和武漢市流動人口不同居住類型所占比重(2004年)單位(%)
已有研究中也反映了我國轉型時期的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比如北京市,20世紀末即已在木樨園周圍的浙江村形成一個較大的棚戶區,且已成為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區研究的經典。[14]比如南京市,有學者通過實地走訪調查歸納出其城市貧困階層居住空間的幾種類型,即:退化的混合居住區,其中又包含城市戶籍貧困人口與一般市民的混合居住地區,以及城市戶籍貧困人口與農村戶籍人口的集中居住區;城中村;棚戶區,棚戶區既包括在老城區主要由租住公房的貧困人口在房子前后搭建的棚屋,也包括在城市外圍由居民自行搭建的平房。[16]比如上海市,隨著城市大規模的住宅建設、規模化的舊房改造以及相應而來的居民搬遷,城市空間分異的趨向通過住房消費體現出來:海外、港臺人士和城市最高收入者普遍分布在市區中心的新建豪華社區及城市邊緣的別墅區內,中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干線附近的商品房社區;一般中等收入者多分布在早期以單位分配方式獲得的公房社區;低收入階層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舊城區。[17]其他城市的情況也與之類同,一方面是一些集中在老城區的虧損或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區;另一方面是城鄉結合地帶以城中村、棚戶區等形式出現且以流動人口為主體的較大的貧困人口聚居區。
同時,由于各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貧困人口聚居區居民的軟、硬件居住條件都極差,表現為城市建筑的破敗、空間擁擠、人口密集以及管理混亂。在我們的抽樣調查中,僅就居住面積而言,廣州市和蘭州市分別有68.7%和71.4%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建筑面積在60平方米以下;武漢市的這一比例甚至高達92.5%,其中24.8%的家庭住房面積不足20平方米;面積在80~120平方米的家庭廣州為4.8%、武漢為1.5%、蘭州為9.1%;三城市貧困家庭的人均建筑面積均不足14平方米,低于其平均值。這種表現在物質設施、管理服務、社區文化、住房價格以及空間布局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也使得這些居住在特定地域范圍內的城市貧民們普遍存在著一種恥辱心理,他們感覺被社會所隔離,而且這種卑屈的心態以及區外居民對他們的歧視使其在包括生活、工作和日常活動等方面都被社會所隔離,貧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非常狹小,主要以家和街道作為其活動的主體范圍。而且,由于人們之間缺乏相互的信任感,這種狀態也成為不利于社會團結穩定的隱患。
三、城市貧困人口區位化現象成因
由于我國當前的城市貧困表現為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型所導致的新城市貧困,所以,下崗失業的貧困職工和流入城市的貧困農民工是轉型時期新城市貧困的主體,也是我國城市貧困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現象。無疑,我國經濟社會雙重轉型背景下的下崗失業、產業結構調整、收入差距拉大、住房制度改革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等方面因素,是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產生的客觀原因。(見圖1)

圖1 我國轉型時期城市貧困區位化影響因素
(一)轉型背景下的下崗失業與城市貧困區位化
轉型的過程亦是原有低層次均衡被打破、新均衡逐漸形成的過程。此間,各種摩擦、矛盾和困境也不可避免隨之而來。從微觀角度來看,伴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以及其他相關改革的滯后,一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管理落后,下崗、失業導致一部分職工生活困難。20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我國體制改革的重心開始由體制外轉向體制內、由增量改革轉為存量改革,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亦隨之展開,“減員增效”使國有企業內部的大量富余人員被剝離出來。尤其是1998年以來,大批工人從國有和集體企業下崗和失業。這些人員中的很多人由于各方面原因可能無法實現再就業;即使那部分實現了再就業的人員,也大多就業于非正規部門,工作不穩定、工資水平較低。還有很多在非國有企業就業的城鎮勞動力也是如此,工作很不穩定,一旦失業,甚至得不到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所得到的那些微薄的保護和補貼。另外,還有一部分國有企業提前退休的職工和所謂“買斷工齡”的職工,如若他們積極尋找工作卻無所獲,無疑也是處于失業狀態并且無法被社會保障所覆蓋。
就下崗失業職工的區位聚居而言,開始表現出原有工業區位與現階段貧困空間分布相對應的特點。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市在空間上表現為以工作單位綜合體為基本單元組合而成的細胞狀結構,城市的空間分異主要是基于土地的利用性質而不是社會層化。[18]城市發展的重點是集中有限的資金發展工業,積極建設產業區。政府導向的城市發展,遵循合理布局生產力和土地利用的原則,集中于建設工廠體系和工作單位綜合體。因此,與各大中城市的工業區建設相對應,我國單位分配住房帶來的居住區分布與產業空間基本一致。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住房商品化和社會化進程的逐步推進,我國這部分家庭低下的收入水平使其無法購置位于優勢區位的住房,而只能夠購得原有福利分配住房的產權或繼續租住公房,原有居民的居住區位改變不大,進而表現出工業布局與貧困區位的空間對應。
(二)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與城市貧困區位化
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國內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我國的產業結構也隨之不斷進行著調整和優化。加之鄉鎮企業發展中的各種弊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其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逐漸減弱。于是,在當時較為松動的戶籍制度下,第一產業所釋放出的勞動力便開始源源不斷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但受其自身技術水平等方面條件所限,這些勞動力中的大多數只能就業于城市傳統的餐飲業、運輸業或建筑業等部門,這些部門大多報酬低、不穩定,加之各種歧視政策和缺乏社會保障,從而使他們成為我國目前和今后城市貧困群體的主要部分。我國的城市貧困問題也因此而表現出不同于發達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有現象。
考察這部分流動人口的分布狀況,各大中城市都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向城市邊緣地帶聚居的特點。因為,就這一階段我國大中城市的建設而言,除了舊城的再開發,不斷向外圍擴張成為城市發展的另一個方向。城市向郊區的擴展包圍了許多城郊結合部的村莊并導致城中村的產生。城中村由于具有土地承租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雙重土地使用制度,其土地利用及房屋建設都十分混亂。[19]在一定時期之內,無論是當地村民還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都可以從該區域廉價房屋的出租和租住中受益,進而使得大量農民工在城中村聚集,并使一些城中村成為事實上的農民工集聚區。另一方面,私人出租住房不僅給當地村民帶來穩定可觀的收入,而且當地政府部門也可以從對農民工的管理收費上獲得利益,這進一步加劇了城中村內不合法建筑的建設和居住擁擠的現象。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規劃控制,一些城中村的建筑景觀混亂,基礎設施缺乏,居住環境惡劣,成為現代城市景觀中極不協調的獨特社區。[20]從長期來看,也必將成為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隱患。
當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貧困問題是產業結構調整加之其他各方面改革綜合發生作用的過程。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傳統落后的產業部門及缺乏比較優勢的國有經濟部門不斷萎縮,其所提供的就業崗位也不斷縮減,部分職工因此轉崗或下崗、失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處于貧困境地。與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福利分房制度相結合,原先優勢企業職工居住區與產業空間相一致的現象,轉變為工業區位與貧困空間的對應。
(三)轉型過程中的收入差距拉大與城市貧困區位化
就城市居民而言,轉型過程與其收入水平的變動進而生活狀況的變化息息相關。而且,這種變化也對應著不同群體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不可否認,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化進程中,城市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除了具有其社會大眾認同并接受的合理原因之外,無疑也存在著由于各種非正常因素而帶來的收入差距的過度擴大,并將可能帶來社會的不穩定。比如: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政府官員腐敗與普通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鎮男女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暴富階層與工薪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弱勢群體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擴大,等等。同時,我國居民之間近些年來的收入差距變化和日漸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反映出,經濟社會的轉型成本并非平等地分攤給每個人,各類弱勢群體因此受到的沖擊可能更為直接和強烈。2006年,我國的基尼系數擴大到0.46,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狀況極為突出。而收入不平等的直接結果,則是原來以職業差別為主要分層特征的城市居民間出現了以收入差異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化,低收入(甚至無收入)群體因而陷入各方面的困窘,城市貧困問題也因此不僅顯化而且迅速加劇。
同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必然使這種社會經濟地位分化體現在居住的地域分異上。當然,城市貧困的區位化現象也必然與城市土地本身的區位優劣緊密相關。受交通是否便利、生態環境好壞與否、服務設施是否齊全等因素影響,城市的不同區位存在著顯著差異。一般而言,城市居民對于居住區位的選擇,不僅取決于一般的交通狀況、購物狀況、娛樂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等方面,還往往要考慮是否靠近“大醫院”和“重點學校”等因素。在此前提下,轉型時期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經濟收入的分化為其居住區位的分化提供了經濟基礎。同時,城市住宅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為其居民在現有收入狀態下自由選擇居住區位提供了可能。換言之,正是由于住宅市場的形成,才使得城市居民不同的收入層次與城市土地不同的區位價格有了直接的聯系。但是,對于城市的貧困群體而言,卻由于自身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而不能行使所謂自主擇居的權利。因此,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貧困家庭不得不選擇繼續居住在舊城區未經改造的舊住宅或城市邊緣及近郊工業區周圍的經濟適用住宅中,城市貧困的區位化特征表現明顯。
(四)全面推進的住房制度改革與城市貧困區位化
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住房實行的是福利性供給制。相應地,此時期各大中城市限于財力并沒有對貧困戶集中的舊城進行徹底改造,而是集中力量建設以單位制為特征的新區。自從1980年4月鄧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住宅建筑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并要求改革相應住房制度以來,一場以商品化、市場化為取向的城市(鎮)住房制度改革便拉開了序幕。以此為發端,我國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近30年,并經歷了逐步推進住房商品化和社會化、培育和發展以住宅為主的房地產市場、逐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這樣三個階段。
前已述及,我國轉型背景下的下崗失業職工由于其低收入或無收入,加之當時住房制度的商品化改革,所以無法購置位于優區位的住房,而只能購得原有福利住房的產權或繼續租住公房。因而,下崗失業職工的區位聚居表現出原有工業區位與現階段貧困空間相對應的特點。同時,雖然城市住宅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為其居民在現有收入狀態下自由選擇居住區位提供了可能,但是城市貧困群體卻由于自身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而不能行使所謂自主擇居的權利,進而聚居在老城的衰退居住區和早期建設的工人新村內。總之,是我國城市近幾十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單位制為基礎的社會各階層混居的特點,隨著城市住房體制改革的逐步完成以及住房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深入推進,我國城市的貧困空間已經呈現出相對集中的分布趨勢,貧困人口首先向地價低廉的城郊結合帶集中,并進一步在城市中心區的外圍形成貧困聚居區。
1998年,國務院有關文件明確提出,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單位提供廉租住房;同時,《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建立了職工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制度,為推進住房商品化創造了條件。2007年,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又進一步提出把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項重要責任,對該群體的住房保障范圍、保障標準進一步明確,住房保障制度建設進入建立、完善和有序發展的階段。
雖然,我國新時期的住房制度改革將有助于解決城市貧困人口的住房問題。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供的數據,通過實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至今已累計幫助1790多萬戶城市低收入家庭改善了居住條件,住房公積金累計幫助4700萬職工解決了購房資金問題。多數棚戶區和舊住宅區得到改造整治,農民工的居住條件逐步改善。但是,一方面,現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仍然主要關注的是本地居民以及有能力購房的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而對于進城農民工的住房需求考慮甚少或基本忽略,城中村仍然是其主要的居住場所。另一方面,這種落腳于微觀層面且能夠切實改善低收入群體居住條件的改革措施,仍然無助于從總體上改善我國大中城市的貧困區位化趨勢。
四、結語
改革開放以前的我國城市是以福利制度(包括福利分房)和平均分配為特征的,因而沒有按照收入而進行的階層劃分,城市貧困人口也主要表現為需要救助的傳統“三無”人員,所以不存在貧困人群在城市某個特定區域內的聚居。但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雙重轉型,我國大中城市基于社會經濟階層的居住模式開始逐漸形成,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開始凸顯出來。作為我國轉型時期新城市貧困的兩大主體,下崗失業的貧困職工和流入城市的貧困農民工在各大中城市的聚居表現出相似的特性。就下崗失業職工的區位聚居而言,主要體現為原有工業布局與貧困區位化的空間對應,老城的衰退居住區和早期建設的工人新村成為貧困職工的主要聚居地;貧困農民工的區位聚居,在各大中城市基本都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向地價低廉的城鄉結合帶集中的趨勢。
綜括地說,我國經濟社會雙重轉型背景下的下崗失業、產業結構調整、收入差距拉大、住房制度改革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等方面因素,是其城市貧困區位化現象產生的客觀原因。我國各大中城市的下崗失業職工之所以表現出原有工業區與貧困空間分布相對應的聚居特點,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市人口享受單位的福利分配住房,由此帶來居住區分布與產業空間的基本一致。但是,經濟社會的雙重轉軌不僅使得大量傳統產業和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失業,而且由此而來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城市住房的商品化和社會化推進,致使城市貧困居民只能夠購得原有福利分配住房的產權或繼續租住公房,原有居民的居住區位改變不大。同時,城市貧困群體低下的收入水平使其無法行使住房制度改革中居民自主選擇居住區的權利,并繼續滯留在舊城區未經改造的舊住宅或城市邊緣及近郊工業區周圍的經濟適用住宅中。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流入城市,其中大部分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向城市邊緣地帶聚居的特點。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短時期之內,城中村的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都可以從廉價房屋的出租和租住中受益,當地政府部門也可以從對農民工的管理收費上獲利。但從長遠來看,必將阻礙各大中城市今后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雖然我國新時期的住房制度改革將有助于解決城市貧困人口的住房問題,但這種落腳于微觀層面的改革措施,仍然無助于從總體上改善其大中城市的貧困區位化趨勢。
故此,可以考慮通過總結和借鑒國外清理和改造貧民窟的經驗和教訓,并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通過加強城市規劃的實施力度、完善政府主導下的貧困聚居區土地開發機制、推行城市貧困和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保障政策,以及制定已有貧困聚居區的改造策略等途徑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并避免出現類似于發達國家的“貧民窟”現象。
[1]李瀟,王道勇.中美兩國城市貧困區位化比較研究[J].城市問題,2003,(5):14-18.
[2]Robert E.Park,Ernest W.Burgess.The Cit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5.
[3]Homer Hoyt.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M].Washington DC: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1939.
[4]Harris C.D.,Ulman E.The Natures of Cities[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45,(242):7~17.
[5]Yeates M.H.,Garner B.J.The North American City[M].New York:Harper&Row,1980.
[6]Jerome Donald Fellmann,Arthur Getis,Judith Getis.Human Geography-Landscapes of Human Activities[M].Dubugue,IA:Wm.C.Brown Communications,Inc.,1995.
[7]Michael J.White.American Neighborhoods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7.
[8]Terry McGee.The Southeast Asian City[M].New York:Praeger,1967.
[9]Larry R.Ford.A Model of Indonesian City Structure[J].Geography Review,1993,(4):374-396.
[10]Larry R.Ford.An New Improved Model of Latin American City Structure[J].Geography Review,1996,(3):437-440.
[11]陳涌.城市貧困區位化趨勢及影響[J].城市問題,2000,(6):15-17.
[12]袁媛,許學強.轉型時期我國城市貧困地理的實證研究——以廣州市為例[J].地理科學,2008,(4):457-463.
[13]袁媛,許學強,薛德升.轉型時期廣州城市戶籍人口新貧困的地域類型和分異機制[J].地理研究,2008,(3):672-682.
[14]顧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會極化與空間分異研究[J].地理學報,1997,(5):385-393.
[15]陳果,顧朝林,吳縛龍.南京城市貧困空間調查與分析[J].地理科學,2004,(5):542-549.
[16]劉玉亭.轉型期我國城市貧困的社會空間[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17]李志剛,等.當代我國大都市的社會空間分異——對上海三個社區的實證研究[J].城市規劃,2004,28(6):60-67.
[18]Wu F L.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J].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2002,(34):1591-1615.
[19]Zhang L,Simon X B,Tian J P.Self-help in housing and Chengzhongcun in China’s urbaniz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912-937.
[20]劉玉亭,等.轉型期城市低收入鄰里的類型、特征和產生機制:以南京市為例[J].地理研究,2006,(6):1074-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