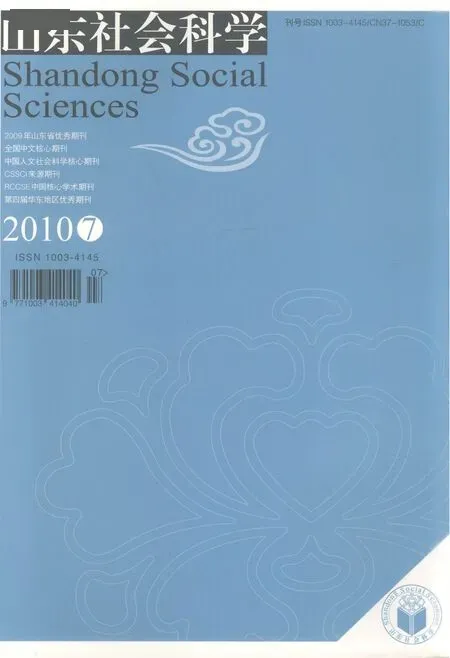從后(后)現代主義視角看歷史學的利與弊*
[美]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 撰 詹霞 譯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
從后(后)現代主義視角看歷史學的利與弊*
[美]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 撰 詹霞 譯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
許多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判強調任何歷史描述都帶有虛構的特點,但這絕不表示,歷史研究拒絕理性的操作方法或者放棄對客觀性的追求。宏觀歷史學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科學考察活動是合理的。在進行科學分析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會是真實的發展變化過程。
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歷史學;利弊分析
最近三、四十年里,西方和非西方的評論界一再聲稱歷史意識是一種工具,西方世界不僅利用它對非西方世界,而且也對自己的民眾,如婦女、少數民族和下層階級實施霸權統治。在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人們一直相信社會進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現在這種信念卻受到質疑。究竟能不能按照客觀標準考察歷史?西方秉承的理性思維被雅克·德里達①參見 AllanMegill,Prophers of Extrem ity:N ietzsche,Jeidegger,Foucault,Derrida(Berkeley,1995)。(JacquesDerrida)、瓊·斯科特②斯科特 (Joan 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1988)。(Joan Scott)和其他人駁斥為邏格斯中心主義。過去,許多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歷史思想家都強調任何歷史描述都帶有虛構的特點。歷史終歸是一種“器”,一種獲取權力或者霸權的工具,它根本不可能要求真實性。本文的要旨就是探討這種批判的合理性究竟有幾分。
對現代歷史意識的批判并不新鮮,其源頭可以往上追溯到 18世紀后期。當時的早期浪漫主義者就開始對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感覺不適,到了 19世紀后期,這種不適在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文化評論家的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浪漫主義者如諾瓦利斯 (Novalis)懷古遁世,緬懷著過去的基督教等級社會,所以他們的批判保留了些許鄉愁的特征。但是這種鄉愁在布克哈特和尼采身上難覓蹤跡,相反,他們要求與基督教斷絕關系,慶賀解脫。雖然布克哈特贊同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替代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但是他和尼采都希望建構一種新的精英式的社會制度,盡可能消除現代社會的解放因素。在這個剛剛開始發展的現代社會里,當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地位平等的時候,布克哈特和尼采卻懼怕所謂的民眾平庸性,認為這將對西方世界的文化財產構成危害。相反,在 20世紀后期的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思想家看來,現代社會還遠遠不夠平等,隨處都帶有壓迫的痕跡,這也正是它一再受到批判的主要方面。然而,像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瓊·斯科特 (Joan Scott)和雅克·德里達 (JacquesDerrida)等一些思想家對理性的批判,竟然與反民主主義者 (如布克哈特和尼采)及海德格爾 (Heidegger)從法西斯主義角度所提出的觀點驚人地一致。③有關法西斯主義,參見懷特 (HaydenWhite),“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發表于 Saul Friedlander主編的Probing the Lim its of the Reopres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Cambrige,Mass.,1992),第51頁。
20世紀后期的解放主義思想家,包括后殖民主義世界的思想家如艾胥司·南迪 (Ashis Nandy)在內,為何一再援引 19世紀后期、20世紀上半葉精英主義甚至是原法西斯主義思想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呢?在第三帝國結束之前,這種文化批判思想均來源于右翼分子的陣營,可是在過去的 30年里,它卻轉到了左翼分子、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思想家的陣營里。這些人雖然很愿意與現代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和統治結構抗爭,但是只繼承了前人的很多非理性主義思想,而不是批判地分析非理性主義的內涵及其政治意義。
不論是對于右翼陣營的文化批判前輩來說,還是對于左翼陣營的文化批判新秀也好,他們主要的問題是爭議,或者說拒絕“啟蒙”。“啟蒙”被理解為“現代時期的核心話題”。對于 19世紀的保守思想家來說,啟蒙運動意味著和基督教分裂,從一個有機相連的社會過渡到殘缺不全的社會。尼采在表明自己和基督教斷絕關系,選擇一條與基督教信仰完全分道揚鑣的道路的時候,仍然沒有徹底擺脫啟蒙運動的宗教批判。不過在批判過程中,他遵循的目標與啟蒙運動的宗旨——即人擺脫他定,實現人人平等——完全不同,而是消滅傳統的、被他稱為“奴隸道德”的倫理制度,因為它限制了天才的嗜權者對大眾的統治。兩次大戰期間的決斷主義者,例如德國的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Os wald Spengler)、海德格爾、卡爾·施米特 (Carl Schmitt)、漢斯·弗賴爾 (Hans Freyer)、阿爾夫雷特·羅森貝格 (Alfred Rosenberg),以及意大利的達南齊奧 (D’Annunzio)、讓蒂勒 (Gentile)和墨索里尼等等,拓展了這種批判,并轉向建立一個專制的元首國家。但是以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 imer)和特奧多爾·阿多諾 (Theodor Adorno)①霍 克海默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 (TheodorAdorno):《啟蒙辯證法 》(Dialektik derAufkl?rung),1944年。見阿多諾 (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第3冊 ,第3版 (Frankfurt/Main,1996)。為首,流亡在美國的學者開始對啟蒙運動進行另一種方式的批判。他們遵循解放運動的目的,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但同時也吸收了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很多思想。啟蒙運動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讓人類從神話里解放出來,啟蒙致力于使人類通過明智的理性行為從“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狀態”(引自康德)中走出來。但是霍克海默(Horkhe imer)和阿多諾 (Adorno)都認為,啟蒙運動導致了新的神話和新的“未成年狀態”。科學原本應該把人類思想從神話中解放出來,可自己卻已變成了神話。就是這同一個科學,原本應該解放人類,可現在在人的眼里卻成了極權主義統治的工具。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霍克海默 (Horkhe imer)和阿多諾 (Adorno)寫道:“理性扮演著適應手段的角色……。它的詭計就在于,讓人變成越來越富有的野獸。”②引自 Arnold Künzl,Aufkl?rung und Dialektik-Politische Philosophie von Hobbes bisAdorno(Freiburg,1971),第171頁。也就是說,理性在他們看來,現在完全等同于一種把不同的現實事物還原為抽象的幾個量的方式。“數字成了啟蒙思想的準則。”③阿多諾 (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第3冊,第23頁。
可是,啟蒙運動究竟意味著什么?一方面它是一個時代概念,代表著 18世紀的各種思想觀點。但 18世紀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時期,各種宗教信仰復興活動 (如虔信派、衛理公會派和哈西德派猶太教運動)和早期浪漫派競相涌現和發展。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常常讓人無法分開,像西奧多·盧梭 (Theodore Rousseau)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在啟蒙運動里面,人們又能看到一種理想典范的意識,這種意識不斷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因此,啟蒙運動的思想特征就是一種認知過程,即人運用理性批判傳統和制度,達到理性行動。但是霍克海默 (Horkhe imer)和阿多諾 (Adorno)認為,啟蒙運動所謂的理性概念其實包含著一個根本矛盾,即理性既含有規范性意義,又有工具性意義。但是啟蒙思想的支持者常常意識不到這種矛盾。理性的規范性意義指的是,如上所述,使人類從“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來,從而能夠按照自己批判的理性標準決定自己的生活。政治上,這就意味著,就像康德和孔多塞 (Condorcet)強調的那樣,一種共和政體的世界聯邦,在這個聯邦里面,人類可以自由地自我發展。孔多塞在 1794年出版的《人類精神進步論》(En 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Darstellung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一書中,極其詳盡地闡述了啟蒙運動的理想典范,即實現人人平等 (包括婦女的兩性平等),取消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消除愚昧和迷信,實現機會均等,消除貧困,以及利用醫藥的發展進步消除疾病等等。幾乎和孔多塞在同一時期,1798年托馬斯·馬爾薩斯④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ThomasMalthus)預言,如果可憐的人類不節制性欲的話,人口數量將呈幾何數量增長,造成巨大的人類災難。與馬爾薩斯的悲觀主義人口論相反,孔多塞堅信,借助科學方法可以提高食品的生產量和控制人口出生率。于是,孔多塞也把理性當作一種控制世界、為人所用的工具,但這種科技進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用來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手段。
與這種解放思想緊密相連的是一種將人類歷史看作獨一無二的進步過程的歷史觀念。其進步理念就和上述“人的理性”這個概念一樣,也包含了兩個互相矛盾的方面。對于孔多塞而言,進步就是實現人人平等和自由,實現科學技術的發展。這兩方面互不排斥,相互補充。孔多塞代表的這種進步理念雖然具有普遍意義,但其核心卻是民族中心主義,因為這種發展進步只發生在世界的局部地區,即西歐和北美地區,從這個角度出發,18世紀及隨后 19世紀的文明只等同于西方文化。言之既此,隱藏在啟蒙思想的世界觀內部的矛盾也就昭然示目。孔多塞理解的進步應該是面向世上大眾的,也就是說,即便在非西方世界也不可以有奴隸和下等的社會階層,因為規范的理性觀念以人人權利平等為前提。對于已經最大化地實現了人權的西方文化來說,其未來目標是幫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擺脫專制統治、消除愚昧和迷信以及擺脫貧困。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其內部對于人類平等和不平等這個主題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新型的經驗人類學,尤其以18世紀后期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克里斯托夫·邁內斯 (Christoph Meiners)所推行的極端形式為代表,試圖根據測量人顱骨的方法制定出一套科學的種族理論。照此理論,白色人種應該是最上等的種族,黃色人種次之,黑人處于最低等的位置,幾乎和動物沒區別。①關于 Meiners,參見 LuigiMarini,Praeceptores Germaniae-G?ttingen 1770-1820(G?ttingen,1995)。
至此,啟蒙運動的理性觀念明顯地透露出了其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規范性地認同人性尊嚴,另一方面卻迫切地希望運用科學武器統治整個世界和人類。到 20世紀下半葉為止,這種進步思想一直是整個西方歷史觀的核心部分。它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根發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幾乎所有當時的政治流派都遵從這種進步思想,其中既包括國家主義思想家如黑格爾,新自由主義學者如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John StuartMill),又包括一些社會主義者如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現在需要嚴格地區分一下文化民眾和自然民眾這兩個概念的含義。后者的生活狀態便是通過自然歷史博物館里陳列的眾多展覽品得以再現。一方面,中國人和印度人在眾人眼中雖然是不同的文化民眾,但是另一方面,德國史學家蘭克 (Ranke)認為中國和印度從文化起源以來便停滯不前,處于“永遠的停頓”狀態,根據他的格言,“只有上帝才知道世界歷史”,即每個歷史時期都是上帝決定的,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歷史,充其量也只是一部自然史。此外,還有一種普遍的觀點,即非洲黑人不可能發展一種獨立的文化。馬克思還指出,亞洲的生產方式拒絕進步,無法擺脫東方特有的專制政體。同時黑格爾贊同馬克思的觀點,認為世界史與西方文明是完全等同的。自從 18世紀以來,這種對待亞洲和中東文化的態度在歐洲思想界發生了極大的轉變。17世紀末,萊比尼茨 (Leibniz)還在大談歐亞大陸上有兩種巨大的勢均力敵的文化,即歐洲和中國,②參見 Jürgen Osterhammel,Die EntzauberungAsiens-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Jahrhundert(München,1998)。然而在 18世紀就出現了一種學術流派,后來的愛德華·薩義德 (Edward Said)③薩義德 (Edward Said),《東方學》(Orientalism)(London,1978)。將其形成歷程稱為“東方學”。那時,西方視角中的東方在誕生之初是一個歷史褪色的國度,中國和印度也就相應而言是沒有歷史的國家。與此同時,西方學者也對古希臘羅馬歷史開始了重新審視。如果說,在此之前西方文化總是試圖在埃及和近東地區的文化里面找到根源,而此刻,古典語文學卻一再強調印度日爾曼及希臘文化的獨立性。④參見 Martin Bernal,Schwarze Athene(München,1992)。
縱觀上述不同時期的西方主流歷史觀點,其根本理念都不約而同地鎖定在現代化這個概念上面。不過,這個術語直到 20世紀很晚的時候才出現。在很多方面,現代化與合理化這兩個概念的含義相互疊合,就像馬克斯·韋伯 (MaxWeber)所描述的那樣:只有在西方世界才存在一種將現實簡化為抽象概念的理性思維,它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正如眾人所知,科學因此是西方世界的一種產物。韋伯把西方歷史看成是一個合理化過程,在它的每個結構中,抽象的理性思維完全不受種族或者宗教觀念的影響,大行其道向前進。這里所謂的合理化我們可以等同為現代化。不管是馬克思、羅斯托 (Rostow)還是福山 (Fukuyama),他們盡管來自不同的政治陣營,卻一致認為,扎根于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將在全世界范圍內發展壯大,因而現代化轉變成全球化。
至此,我們都游離在一定的話語框架中討論什么是啟蒙運動、現代化和合理化。但是這些話語并非純粹地懸浮在空中,它們都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曾幾何時,西方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個領域征服了世界,歸根結底,這些都是現實力量對比的結果。假如沒有資本主義,沒有現代國家和現代科技的出現,歐洲世界要想在歐洲之外的世界擴大影響力便是天方夜談。
對現代主義的后殖民主義批判思潮真正始于 20世紀 70年代。現代主義一直受到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的批判。兩者的觀點在很多方面都一樣,不過前者源自于西方學者的作品,后者則歸屬于非西方學者的作品。這些學者出身于昔日的殖民地國家,其中,尤其是印度的從屬者研究 (Subaltern Studies)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 (Dependencia Theorien)為解釋這些地區的落后提供了很好的依據。在這些批判中,受到質疑的不僅是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比如資本主義起著什么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關于現代主義的討論,因為它從根本上而言涉及到了西方社會的精神實質、真理觀念和歷史哲學。
就像西方學者曾經勾勒出了一幅靜止的東方景象一樣,我們的腦海中現在也極有可能浮現出一幅靜止的、固不可分的西方和現代主義景象。這種做法非常危險。如上所述,批判的核心問題主要集結在啟蒙思想的理性概念。一種源于西方自身視角的批判觀點也將矛頭指向了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概念,其典型代表就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61年出版的早期作品《瘋狂與文明》(Geschichte desWahnsinns),這部書依舊充溢著純粹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調。像霍克海默 (Horkhe imer)和阿多爾諾 (Adorno)一樣,福柯也遵從啟蒙辯證法的思想,即啟蒙根本意旨在于,去除外界的魔咒,解救人類;但事實上,啟蒙身體力行地開拓了一條通往權力歸一并最大化的道路。照這樣看,現代世界和啟蒙的破壞性和非人性集中體現為,它們將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排除在外,希望假借理性之名合理地統治人的生活。因此,不但人的主觀性被摒棄,而且現在還溫順服從地置身于權威和暴政的宰制之下。一個中世紀的農村傻瓜在他的村落里尚能找到一席之地賴以生存,相比之下,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里的人卻會因為違背了社會規范而接受制度化教育,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最初作用只是監禁,隨著精神病學——其奉行的宗旨是治愈一切被歸結為精神病的不服從行為——的出現,它變得越來越危險。換句話說,精神病院就是要剝奪人的個性和特性。業績強迫癥相應地成為社會生活的標準規范。在 17世紀,奉行新教和天主教的社會里百姓生活貧困,犯罪行為肆虐,凡是犯法的人都要被烙上一個烙印以示懲戒。與此同時,人們普遍要求這種以惡治惡的懲戒方式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人性地對待和感化這些罪犯會有助于他們重新回歸社會。這種做法導致的后果卻更具災難性,因為他們被迫將這個社會的各種規范同化到自己的內心世界。
在某些方面,福柯雖然繼承了啟蒙思想中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的觀點,但是他歪曲了這個觀點。原本強烈地渴望創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結果在他身上走到了極端的對立面,即人都喪失了人性。雖然幾乎福柯所有的作品的結構都具有歷史的特點,但是他將這種歷史意識視為超現代社會的優點。在很多方面,福柯的現代主義理論可謂是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典型代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持有與福柯相似的觀點,即歷史意識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優點,“所謂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優越性反而應該更準確有力地讓人信服這一點。”①懷 特 (Hayden V.White),Metahistory-Die historische Einbildungskraft in Europa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Frankfurt/Main,1990),第16頁。
現在,我想深入地探討艾胥司·南迪 (Ashis Nandy)②③④南迪 (AshisNandy),“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in: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34(1995),第44—66頁 ,第53頁 ,第49頁。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后殖民主義批判思潮。在他看來,曾經統治歐洲及后來的歐美世界一時的歷史思想構建了殖民主義的思想基礎。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對歷史科學性的信念是殖民主義世界觀的核心思想。然而,所有其他社會和文化對歷史的理解卻與此信念完全不同。在南迪眼中,從近代早期發展到高度發達的殖民主義時代,西方歷史都未曾中斷,始終得以延續。雖然曾經被統治的殖民地紛紛獲得主權獨立,但是殖民主義并未隨著這種表面上的獨立停止作用,而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繼續統治著非歐美國家。西方人把殖民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其根源從他們對現實的世俗化態度中不難找到。其實這種態度自培根 (Sir Francis Bacon)以來便成了西方思想的特點,它完全打破了神話,只承認歷史的一種形式,即客觀而科學的歷史。傳統啟蒙思想的前提是“歷史是完全等值地、真實地再現過去,即沒有任何過去游離在歷史之外。”③而現代的歷史觀僅僅認識一種歷史進程,它曾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過程推波助瀾,而最終的發展趨勢將是世界歐美化。南迪將批判矛頭不但指向了西方世界這種片面的進步思想,而且還批判了西方人特有的歷史意識。在他看來,這種歷史意識之所以極具西方特色,是因為在其他文化里面,歷史是一幅內容浩瀚、形式多樣的景象,其中還有神話和傳說穿梭的身影。所有為歷史尋找一個科學的基礎的努力最終都導致了極權主義和暴力。南迪宣稱,斯大林假借“科學的歷史思想”之名將兩千萬俄羅斯人送上了死亡之路。④在此,南迪不經心地混淆了兩種事物:一是缺乏任何經驗檢測的目的論歷史哲學;另一個則是歷史學家致力于擺脫神話的影響,使歷史認識不被歪曲。同尼采和海德格爾一樣,南迪也為生命世界受到所謂的“科學世界觀”侵襲而感到惋惜:“今天,本世紀最后的十年里……我們變得年邁,疲憊不堪而又更加睿智,我們能有勇氣斷定,文明的主要問題與理性而又矛盾的迷信毫不相干,與之相關的卻是現代思想的理性概念。”①南 迪 (AshisNandy),“Modern Science andAuthoritarianism:From Objectivity toObjectivation”,in:Bulleti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ety,Bd.7,Nr.1(1997),第11頁。非西方文化中開放的歷史觀,比如印度,既能夠選擇性地重建歷史,又能像尼采所說的那樣,忘記歷史;這樣,歷史給現實生活也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南迪在文章中只字不提神話在維護政治暴力和民族固定觀念的過程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對南迪來說,對科學和進步的信念,是造成 20世紀暴力橫溢的主要元兇。而與兩次世界大戰、種族沖突和種族大屠殺相比較而言,現代化及全球化——他稱之為“現代世界主義”——造成的危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場“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運動中,許多人無形中成為犧牲品和難民,其數量和規模遠遠超過了本世紀所有大規模的血腥沖突。②南迪 (AshisNandy),“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第55頁。同時,南迪卻掩蓋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才被人質疑的印度傳統社會特有的壓迫性。
在此,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充滿矛盾的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上來。除了我們知之甚少的少數幾個與世隔絕的原始社會之外,人類歷史上或許還沒有一個社會和文化不是建立在壓迫群體,尤其是壓迫婦女的基礎之上的。自古希臘羅馬時期以來,不管是在近東、南亞、東亞、歐洲,還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的北美和南美,或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這些地區的所有大型文化都體現了這種等級制度;而且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西方古典哲學和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宗教,如印度教、儒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一一證明了這些壓迫和等級制度的存在。啟蒙運動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聲宣告了人人不僅享有宗教平等權利——正如耶穌在山上對門徒提出的教訓那樣,而且在社會、政治上的地位也完全平等。人人平等也就變成了啟蒙運動的一項原則,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宣告了這一點,卻幾乎從未將它付諸于實踐。比如華盛頓和杰弗遜(Jefferson)就是奴隸主。人們不僅期待著政治權利平等,而且還要求社會和文化權利平等,婦女在這方面的呼吁尤其強烈。從早期的現代主義批評家開始就提出的觀點,即現代世界廢除了人類的自由和個性,雖然被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如福柯再次強調,但卻無法得到眾人的支持。舊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逐漸分崩離析,傳統的標準和制度紛紛被瓦解打破,這一切大大促使了人們獲得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多的機會,來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個性化地生活。但是這種自由也將他們的生存推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即對自己的生活作決策,而這種決策在以往隨大流的社會生活中還前所未有。
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包括亞非地區反殖民主義斗爭,如果沒有啟蒙思想和現代主義的原則作為行動綱領是難以想象的。自 18世紀以來,人人平等的思想逐漸成為現代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沒有現代思想同過去的傳統歷史相互碰撞的過程,也就不可能出現我們眼下所看見的現代印度。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主義也促進了自己的垮臺。反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支持者和倡導者都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他們一方面不懈地努力,讓自己的祖國擺脫西方世界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上的統治;另一方面,考慮著實施西方的一些思想,比如民族國家,這些思想早就不再局限于西方社會,它們在此期間早已遍及全球。
啟蒙思想之所以表現為矛盾不一,正是基于這個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的事實,即它們提出的要求并不只是純粹的話語討論,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反映當時權力關系的社會結構之中。③參見 Arif Dirlik,Postmodernity’s Histories-The Past as Legacy and Project,發表于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Boulder,Colorado,2000)。沒有資本主義,也就不可能有現代社會的存在。資本主義的最高目標是以最為理性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的利潤,而將道德規范或文化規范置之不理,同時,人就成了實現經濟理性化的犧牲品。但是現實中這種純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存在。世界市場的建立實際上就是全球經濟掠奪,這種掠奪一方面如果沒有現代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絕大多數為民族國家的形式,但也有例外——是不可能實現的;另一方面也要求對現實保持理性的態度,正是基于這種理性態度才發展出了后來的現代科學,其規模和形式在其他社會和文化里都屬獨一無二。這些科學、技術和經濟上的進步并不僅屬于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因為它們建立在這個事實基礎之上,即存在一個真實的世界,所以這種進步也就成了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歐美世界與昔日的殖民世界之間的界限完全消退了。難道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后殖民主義時代嗎?隨著舊殖民地的政治獨立,殖民主義表面上結束了;但是至少在經濟領域里我們可以這么說,當然還有在文化領域里,舊殖民世界對這些新興國家的影響與以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談到現代主義時,人們不禁立刻把它等同于“全世界范圍內持續不斷的發展”,這種想法不能那么輕率地就加以駁斥,就像人們對后現代主義理論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批判那樣。事實上,是有一種現代化過程,它同時也是全球化的過程,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資本主義。在一些人看來,誰要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現代的西方社會自近代初期以來就身處現代化的漩渦之中,至今仍未結束,那他就是盲目的。但是這些人忽略了現代化的兩個方面,因為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民眾在 20世紀下半葉之前一直把現代化帶來的進步片面地看成積極的、指導性的因素,而我們從今天的辯證法角度來看,更清楚地意識到這個現代化過程所包含的兩面性。一方面,在一個日益現代化的世界里,啟蒙思想的最高目標通過多種方式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框架內得以實現,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導致了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內的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以及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與以前的工業不發達地區——目前它們的數目并不多——之間的鴻溝日益加大。我們必須意識到,不管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非西方國家,現代化和全球化都不可能是一個單調平靜的過程。在歐洲的心臟地,我們曾描述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遷都一再遇到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結構的頑強抵抗,法國大革命的崇高目標“自由民主”只能很緩慢地被逐一貫徹,其中還經歷了不少重大的倒退和挫折。繼 19世紀中、西歐地區的猶太人解放運動之后,卻出現了一種新的反猶太主義及二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在歐洲境內的經濟和政治界線被跨越之時,在世界的其他地區,如巴爾干和高加索地區、近東、阿富汗和斯里蘭卡以及非洲,血腥的種族沖突卻給人們帶來了浩劫。兩次世界大戰,納粹分子和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統治,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恰好同世人斷言的更人性化的、更理智的社會發展趨勢相違背嗎?納粹主義和蘇維埃共產主義究竟是現代化的變異形式,還是用現代權力手段形成的完全脫離現代社會發展方向的返祖現象?
可以肯定,根本沒有純粹的現代化或者全球化。尤其在過去的 30年里,歷史編纂學特別強調文化因素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事件和變遷中的影響作用。例如,自 20世紀 20年代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Lefebvre)發表早期作品以來,至 70年代,歷史編纂學偏重從經濟因素的相互影響的角度來闡釋法國大革命,而在最近30年里,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話語討論,其中的一些文化現象,如語言和象征,相對地獨立于社會和經濟結構,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同時,歷史編纂學也逐漸意識到了各個地區具有不同的特點以及這種地區特性的作用,比如,西西里島和南加利福尼亞的現代性便呈現不同的風格,甚至在這些地區內部,現代性的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顯然,這些差異在非西方世界更大,遇到的阻力也更多。在整個伊斯蘭教社會,印度,以色列以及奉行新教的北美地區,我們都無法避免原教旨主義,它極力反對現代化趨勢,或者想給這些不同的現代化變體換上另一種社會形式。
這一切對人類科學,尤其對后殖民主義或者所謂的后殖民主義時代中的歷史學意味著什么?今天,我們已不能像 40年前那樣編纂歷史。那時,一種社會學取向的歷史學取代了 19世紀出現的具有歷史主義傾向的古典歷史學。后者反映了前工業和前民主時期的政治和社會關系,把注意力聚焦在“創造歷史”——引用特萊希克 (Treitschke)的話來說——的國家和偉人身上。1945年后,歷史學轉向社會學領域,分析研究結構和過程,從而顛覆了以往側重研究人物和事件的歷史學。但是這兩種歷史學觀點具有同樣的兩條基本前提,即它們認為,歷史編纂學和真實的過去具有直接的一致性,歷史對它們而言主要集中在歐洲或歐美地區。同時,這種社會學取向的歷史學也傾向于,把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代世界的歷史同等重要——視為凱旋般的勝利,卻完全忽視了勝利背后慘痛而巨大的犧牲。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批判對這種歷史學觀念及其斷言的科學性要求已經提出質疑,指出并不存在統一的歷史,而是多樣化的歷史,每種歷史都由歷史學家的主體性及其意識形態前提來決定。另外,這種批判還強調歷史研究和歷史編纂永遠不能像一面鏡子一樣真實地映照過去,而是必須先被歷史學家建構。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在這兩點上的批判是有道理的。然而,一些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家,如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雅克·德里達 (JacquesDerrida)、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Jean-FrancoisLyotard)和讓·鮑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的極端形式有時導致了徹底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它全然否定歷史的關聯性,同時也否定歷史與虛構之間的分離。“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①參見伊格爾斯 (Georg G.Iggers),“Zur‘Linguistischen Wende’im Geschichtsdenken und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Jg.21(1995),第557-570頁。完全有理由表明語言在歷史認知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觀點的激進代表者,如漢斯·凱爾納 (Hans Kellner)①凱爾納 (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Madison,1989)。,接著又轉向了另一種立場,即根本不存在歷史現實,我們理解的現實完全是語言的產品。利奧塔 (Lyotard)和鮑德里亞 (Baudrillard)強調歷史純粹是一片混沌,任何在其中尋找意義的嘗試只會助長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些批評并非毫無根據,只是,歷史研究和歷史之間的關系遠比歷史主義取向的和社會學取向的研究所理解的那樣復雜得多,也更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兩者均以某個特定的社會制度為前提,社會學——尤其是二戰之后最初的 20年里在美國盛行的——認為西方國家戰后時期推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是規范性的標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也遵循這種基本前提,采用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進程觀點,只不過在歷史進程的開端問題上和西方理解不同。
這種歐洲中心歷史觀在當今日趨全球化的世界已不再能站得住腳了。當下思想中許多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判已尖銳地揭示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歷史學及其歷史觀存在的弱點,因為它不但把非西方世界排除在外,而且根本沒有考慮到整個人類群體和人類生活領域,比如性別問題和非社會主流群體的生活問題。被宏觀歷史學忽視的那些社會群體,其生活經驗和地方性已經受到微觀歷史學的關注。但這絕不表示,歷史研究拒絕理性的操作方法或者放棄對客觀性的追求。另外,宏觀歷史學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科學考察活動是合理的。在進行科學分析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將會是真實的發展變化過程。不言而喻,這些變化過程與我們在后殖民主義之前的時代所理解的相比,形式更具有多樣性,而且我們也認定了這個時期歷史主義以及社會學研究的主導前提。雖然在很多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身上,尤其是文學批評中,不難找到反理性主義的痕跡,但是它在歷史學家的實際研究活動中沒有被貫徹。最近 30年里,圍繞歷史開展的科學研究活動并沒有終結,反而日益增多,不斷地發展和多元化,運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比早先的歷史學和歷史意識形式更符合人類生活的多樣性。我們盡管對歷史的理解喪失了統一性,卻贏得了多樣性。
今天,啟蒙運動的帷幕還遠遠沒有落下。雖然剛才我已經尖銳地批判了霍克海默 (Horkhe imer)和阿多諾 (Adorno)對啟蒙思想的片面理解,但是我和他們一樣相信,我們需要一種批判理論,它源于科學性的理解力,對于正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社會里的現有情況不再簡單地下任何斷言,而是批判地仔細考察和研究。就像霍克海默在 30年代,即《啟蒙辯證法》出現之前就提出的那樣,這種批判性理論構建在一個“未來社會的藍圖基礎之上,(這是)一個自由人的集體,他們能夠利用現有的技術手段實現自由”②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inKritische Theorie(Frankfurt,1968),第2冊 ,第166頁 ,第191頁。,當中蘊涵著一個理性概念,其目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公平狀態”③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inKritische Theori(Frankfut,1968)第2冊 頁 。。而這正是啟蒙思想的核心內容。在當今時代,資本主義框架下飛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陷入矛盾境地,因此,把經驗分析和批判態度結合起來,對這些進程進行科學的研究,是非常緊迫和必要的措施。隨著我們意識到,人類在與全球化市場為導向的社會經濟制度相抗衡的時候,已經處于均勢,那么我們朝著人人平等的崇高目標前進的腳步就不該停止,反而應該躍升到一個更加重要的地位。
(責任編輯:蔣海升)
K091
A
1003—4145[2010]07—0017—07
2010-05-26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Georg G.Iggers),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榮譽教授。譯者詹霞,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