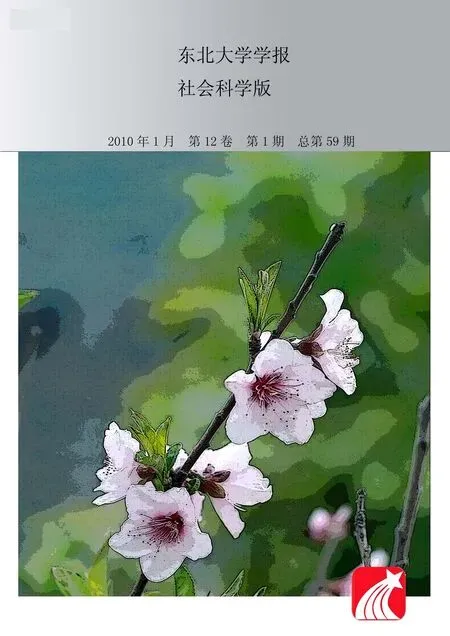改編的通俗性與文學經典的建構
原小平
(武漢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 改編與文學經典化的關系
文學名著,尤其是文學經典,一直是改編的熱點。以莎士比亞的作品為例,據統計,自電影誕生的1895年到1971年,世界上大約有450部電影根據莎士比亞的戲劇改編而成[1]1,迄今為止,這仍是一個其他作家的作品難以企及的改編數量。中國文學以四大古典名著為代表的經典之作,包括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魯迅的《阿Q正傳》、曹禺的話劇、金庸的小說等,被改編的頻率也相當高。比較而言,一般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的幾率明顯小得多。筆者曾對1935—1994年間所有中國(包括大陸和港澳臺)人拍攝的獲得過世界大獎的電影作過統計,共有282部,其中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有46部,而這46部改編之作中,有36部可以被劃為文學名著,也就是說,來源于名著的改編約占78.3%①以上四個數據,是根據張駿祥、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3—1443頁)所提供的資料,統計得出的結果。,這個比例和我們日常的經驗大體吻合:名著比一般文學作品更能吸引改編者。
改編基本上是由文字文本轉變為表演藝術,由相對高雅的文學轉變為更通俗的視覺藝術或口頭藝術,呈現出一種經由改編者到改編本接受者的階梯式接受過程。這個接受過程的特殊之處,就在于改編本的接受者,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感受原著的藝術魅力。當然,由于間接接受,原著的意蘊不可避免地有所流失和變異,這是其不足之處。不過,如果改編本很成功的話,可以有效避免原著精華過多流失。更重要的是,這種間接接受有不可替代的優勢,那就是:通過改編,可以將文學名著最大限度地普及到普通人群之中去,甚至讓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也有機會對名著有所了解----這正是文學改編得以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勞倫斯·奧立弗所言:“把莎士比亞的偉大舞臺劇本搬上銀幕是一種藝術上的妥協,但由于渴望看到這些劇本的精彩演出的人絕大多數都難償宿愿,所以還是值得這樣做的。”[1]106即使那些通俗文學作品,也需要改編才能最大限度地擴大其受眾面。金庸小說的通俗性和受歡迎程度,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中,可以說絕無僅有。據199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稱:“光是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這三大市場,歷年來金庸小說的銷售量,連同非法盜印的在內,累計已達一個億。”[2]但對于動輒數億的電視連續劇觀眾而言,金庸小說的讀者,仍是一個相對小的群體。
接受美學認為,傳播與接受是文學作品藝術生命史的一部分,沒有讀者的接受,文學作品只不過是“一個擺在那兒恒定不變的客體”,“文學作品的歷史性存在取決于讀者的理解,因此,讀者的理解是作品歷史性存在的關鍵”[3]。那么,對于經典性文學作品來講,改編這種強有力的通俗性傳播過程,會對原著產生什么影響呢?
最大的影響在原著經典性的建構方面,即對原著的經典化過程發生巨大影響。因為文學經典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擁有足夠數量的不同時空中的讀者,在于其空間上的廣泛性和時間上的持久性。文學不是科學,科學的使命指向自然界,探索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需要嚴密的邏輯推理和較強的抽象思維能力,這注定了科學永遠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精英才能理解和掌握的東西。文學的使命是表現人的內心世界,作者的創作和讀者的理解主要靠直觀把握和心靈頓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個普通人對最深刻的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內容都會有悠然神會之處。更重要的是,科學的價值在于改造自然的過程之中,而文學藝術,其價值顯然就在讀者的會心一笑和熏浸刺提之中。因此,我們固然不能說最通俗、讀者最多的文學作品就是最經典的,但真正的文學經典必然有其通俗性的一面。如果一部文學經典總是以拒絕讀者的姿態出現,那么,它的經典性就很可疑,至少其經典性還不夠純粹。宗白華曾論述:“人類第一流作家的文學或藝術,多半是所謂‘雅俗共賞’的。像荷馬、莎士比亞及歌德的文藝,拉飛爾的繪畫,莫扎特(Mozart)的音樂,李白、杜甫的詩歌,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說;不但是在文藝價值方面是屬于第一流,就在讀者及鑒賞者的數量方面也是數一數二的,為其它文藝作品所莫能及。這也就是說,它們具有相當的‘通俗性’。不過它們的通俗性并不妨礙它們本身價值的偉大和風格的高尚,境界的深邃和思想的精微。所奇特的就是它們并不拒絕通俗,它們的普遍性,人間性造成它們作為人類的‘典型的文藝’(Classical Arts)。”[4]顯然,宗白華所言的“典型的文藝”就是我們所說的經典文藝。從本質主義的觀點來說,一部作品要成為經典,它自身必然需要具有能夠成為經典的潛質,這是經典的基礎和內因。但一部潛在的經典最終成為經典,就需要傳播和一定數量讀者的認可,這是經典形成的外因。通過讀者的公認,經典最終確立,才是作品經典化過程的徹底完成。
當然,某些改編尤其是顛覆式改編,有時會消解作品的經典性,這是一種逆向的經典化過程,也被稱為去經典化過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電影《大話西游》在中國大陸放映,雖然起初一度票房收入低迷,但是不久就受到了以大陸高校學生為主體的眾多觀眾的熱烈追捧。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文化事件,它標志著60年代起源于歐美的后現代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發生了實質性影響。后現代主義鼓勵文化瀆神,以消平深度、打破中心、拒絕權威、解構經典為特色。此后,“大話”“戲說”“水煮”類作品不斷涌現,潮流所及,不僅四大古典名著遭到另類改編或改寫,而且建國后的一批以“紅色經典”為代表的當代名著,如《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沙家浜》等也遭到低俗改編。2004年4月,國家廣電總局針對“紅色經典” 低俗化改編熱,下發了《關于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狠剎亂編亂改紅色經典之風,所有“紅色經典”電視劇要報送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審查委員會終審。這說明了顛覆式改編已經動搖了某些名著或經典性作品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造成了很大不良影響,以至于國家相關部門認為只有通過行政的力量,才能遏制顛覆式改編對某些名著經典性的解構。這類改編對經典作品的沖擊,還影響到社會的知識精英階層(他們是文學作品經典化過程中的權威力量),引發了文學研究者對“經典”和“經典化”的熱烈討論。迄今為止,“經典”仍舊是文學理論界的熱點之一。2005年5月27—30日在北京召開了“文化研究語境中文學經典的建構與重構國際學術會議”。會上來自歐美亞不同學術經歷和民族背景的專家學者對“文學經典”展開了討論,著名的荷蘭學者杜衛·佛克馬的開場白是:“現在對文學經典日益增長的興趣是建立在人們對其作用和價值懷疑的基礎上的”[5]。可謂一語中的。文學研究對經典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近年流行的顛覆式改編,對文學經典的解構,已引起了知識界焦慮,這也從反面證明了名著改編對文學經典化的巨大影響。
顛覆式改編主要是一種解構力量,缺乏建設性,在名著改編中,不是主流。主流的改編追求表現原著的精神實質,追求對原著的正面普及,因此,文學改編在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建構,是一種促進的力量。一部作品經典地位的確立,需要社會中所有階層,即統治階層、知識精英階層、普通民眾階層的一致認可。其中,普通民眾的認可是經典化最根本的力量。普通民眾雖然藝術鑒賞力較弱,往往會受時尚的影響,但如果一部作品長久地被大眾所喜愛,那么,一定已經不僅僅是時尚了,它至少已具備了可成為經典的特質。民間流行的文學,往往語言不夠精粹,要進一步成為經典,還往往需要知識精英的參與、潤色,需要文化權威的承認和最終定位,所以經典化往往是普通民眾和知識精英合謀的過程。經典的通俗與高雅的特性,也由此生成。統治階層往往是從政治而非文學的角度,來評價文學作品,他們對文學經典的建構,多是基于利用和權宜之計。因此,雖然在特定的時段,政治因素會對某些文學作品經典化產生直接和巨大的影響,但長遠來看,政治對經典化的影響是微弱的、可以忽略的。建國后,魯迅、郭沫若、茅盾,曾被確立為文藝戰線上的三面旗幟,但僅幾十年時間,郭沫若許多作品的經典性,已不大被人們承認,茅盾作品的經典性也不斷引起人們質疑,即使魯迅的作品,人們對其經典意義的理解也和“十七年” 、“文革”時期大不一樣。從來沒有哪一部真正的經典是靠政治權力來確立的。有人曾認為魯迅小說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主要是由于政治的神化,然而,在魯迅早已走下神壇的今日,2003年6月由新浪網與國內17家強勢媒體共同組織的大型公眾調查----20世紀文化偶像評選活動----結果顯示:魯迅仍是最受人們推崇的作家(其次分別為金庸、錢鐘書、巴金、老舍)。這說明,魯迅作品具有真正的經典意義,它們和政治的提倡與否,關系并不大。
由于文學作品經典化主要是普通民眾和知識精英之間的互動過程,那么聯系著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的文學改編就成了經典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并由此參與了文學經典化的進程,具有重要作用。這在文學經典的生成和確立階段都有明顯體現。
二、 改編與文學經典的生成
中外許多文學經典在創作前,往往在民間有一個曾長期流傳的“本事”或曰相似的故事,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是根據意大利民間故事寫成的一部愛情悲劇,《李爾王》則取材于古代英國的歷史傳說。歌德的《浮士德》的內容,來源于德國16世紀浮士德博士的民間傳說。我國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成書之前,也都有一個在民間長期流傳演進的過程。凡能在民間長期流傳的故事,不論多么粗糙,一定具有某些超越性的意蘊和突出的原型意味,具有經典性的內核。這種內核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會不斷得到強化,并最終會為經典作品的創作鋪平道路。《水滸傳》、《三國演義》在作者署名中強調“編次”,正說明了成書前民間流傳的故事對這兩部經典的奠基之功。民間故事的流傳形式,一是口頭文學(或根據口頭文學記錄下來的一些文本,如中國宋代的話本就是當時民間藝術“說話”的底本),二是表演性的演出(如中國的戲曲)。兩者往往先后產生,相互影響,關系密切,后者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對前者的改編。王國維在論述宋元戲曲和“說話”的關系時就說:“此種說話,以敘事為主,……其發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后世戲劇之題目,多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仿為之,所以資戲劇之發達者,實不少也。”[6]顯然,被改編成表演性藝術的內容,只能是民間故事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一般來講,還應該是其中最精華的部分,這也就是說,改編本身就是一個對民間口頭文學的選擇(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生發),使其更加經典化的一個過程。這些戲曲的內容往往會被后來的經典作品所吸收,成為其核心部分。
典型的例子是元代大量的“水滸戲”和《水滸傳》創作的關系。關于宋江對抗朝廷的事跡,早在南宋已有民間流傳。宋末遺民龔圣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自序說:“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7]96這說明了南宋“水滸故事”雖內容引人注目(“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但形式還很簡陋(“街談巷語,不足采著”)。元代漢民地位低下,強烈呼喚宋江之類的英雄豪杰,以解倒懸。加上元代長期廢除科舉,大量讀書人流落下層,他們就把南宋以來的“水滸故事”大量改編為當時異樣發達的雜劇。僅元初戲曲家高文秀一人創作的水滸戲,就達8種。這些被改編成的水滸戲,至少在三個方面,為《水滸傳》的出現做了準備:第一,對南宋“水滸故事”中的英雄形象進一步強化。據《大宋宣和遺事》可知,南宋“水滸故事”主要敘述的是四件事:楊志賣刀、劫生辰綱、宋江殺惜、征方臘。其中人物主要是“盜寇強人”形象。在元代水滸戲中,梁山好漢宣稱“替天行道”,所為多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事,這就使得南宋故事中的水滸“強寇”具有了解人危難的江湖俠士身份。俠士化的草莽英雄,不但形象更為豐滿,還和流傳在中國底層的傳統墨家文化中的游俠文化對接起來了,從而具有了獨特的意義,為《水滸傳》的經典性作了進一步鋪墊。第二,語言具有了精練文雅的特色。孔子曾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通俗化并不是粗俗化,真正的通俗化也需要文從字順和適當的文采,需要民間文人的參與。由于下層文人的參與改編,元代還出現了像《梁山泊黑旋風負荊》這樣的雜劇精品。語言藝術上的提高,自然也是文學經典化的必要條件,這也增強了水滸故事的藝術魅力,擴大了它的流傳范圍。同時,這也會吸引更多更有才華的文人關注并進一步參與《水滸傳》的經典化過程。第三,元代雜劇繁盛,而當時大約平均每上演20個雜劇,其中就有一個是水滸戲[注]現存元代雜劇劇目約530多種(見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其中水滸戲約25種(見陳建平著《水滸戲與中國俠文化》,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頁)。。這一方面進一步普及了水滸故事,另一方面在改編者和民間觀眾的互動中進一步塑造了典型的水滸英雄形象。如李逵的形象,在宋代“水滸故事”中并不突出,但在元代有關李逵的水滸戲數量最多。李逵后來成為《水滸傳》中最為金圣嘆所稱道的人物形象,元代水滸戲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鄭振鐸曾分析說元代的水滸戲創作:“是跟了當時的民間嗜好而走去的。民間喜看李逵戲,作者便多寫李逵,……至于其他很可取為劇材的‘水滸故事’,他們卻不大肯過問了。”[7]103在元代水滸戲中,李逵天真快樂、疾惡如仇、勇猛魯莽,是個可愛的人物形象,并沒有后來《水滸傳》中描述的掄著兩把板斧“排頭砍去”的嗜殺傾向。武松打虎的故事在元雜劇中也都有表現,而這在作為南宋說話人底本提綱的《大宋宣和遺事》中卻沒有提到。
由南宋水滸故事改編的元雜劇,在語言、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主題等方面所具有的藝術成就,都成為了后來《水滸傳》創作的重要資源,《水滸傳》中的一些章節內容,和元代的水滸戲在情節和人物上基本雷同,就是很明顯的例證。另外,長期民間流傳,使《水滸傳》天然具有很強的通俗性,這也是那些純粹由文人創作的文學經典所難以做到的。《三國演義》、《西游記》的成書過程,和《水滸傳》類似,經典化都經歷世代累積和孕育,其間曾有大量三國戲和西游戲的改編和流傳。世代累積型的經典一旦經過文人整理加工、創作成型,憑借其長期形成的高度藝術成就和巨大社會影響力,最終被知識精英階層接受并被文化權威賦予經典地位,就是順理成章、或早或晚的事了。
三、 改編與文學經典的確立
世代累積型經典基本產生在古代社會,因為當時以小說、戲劇為代表的通俗文學不受文人重視,少有文人從事此類創作。封建社會后期,文人獨創型經典才逐漸增多,《金瓶梅》、《紅樓夢》是其中的代表。晚清以來,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逐漸占據了文學創作的中心地位,受到文人重視,越來越多的文人積極地投身其中,其后的文學經典幾乎都屬于文人獨創。文人獨創型經典,在被社會接受前,只是潛在的經典,如果沒能得到流傳,是不能視為經典的。如老舍的長篇小說《大明湖》,雖已完稿,但毀于戰火,不可復見。根據老舍對其內容的描述和由《大明湖》改寫的中篇《月牙兒》來分析,這個在《駱駝祥子》前創作的小說,很可能是堪與《駱駝祥子》相媲美的經典之作,但現在誰會說《大明湖》是現代文學的經典呢?因此,近代以來,作品完成后能否廣泛流傳,就成了其經典化過程的一個關鍵因素。文人獨創的文學經典,在現當代也有通俗和嚴肅、娛樂性和啟蒙性之分。由于近代以來中國擁有文學欣賞能力、機會和閑暇的人比例很小,所以即使現當代文學中那些最通俗的作品,從民國初年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派武俠小說、張恨水的社會言情小說,40年代趙樹理和張愛玲的小說,再到建國后的“紅色經典”、港臺金庸和瓊瑤的小說,它們以紙質文本形式流傳的范圍,主要還在知識分子或準知識分子(中學生以上)之間。由于這種流傳方式缺少民間普通民眾的互動,有時候還受到政治因素的巨大干擾,由此形成的所謂現當代文學經典,實際上經典化往往并不充分(缺少民間的認同),導致它們的經典性常常相當曖昧,往往游移不定。有些作品曾在某些階段被奉為經典(如“紅色經典”、“樣板戲”),現在看來是名不副實的。也有些作品,曾長期受到批判和冷落(如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的小說,穆旦的詩歌),現在看來它們又極具經典意義。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影響,另一方面也在于這些作品從來也沒有能夠真正普及到民間,民間的失語使得現當代文學經典的地位相當脆弱,很容易成為政治的玩偶。真正根植于民間的經典(像《水滸傳》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但在當時顯然仍被視為經典之作),是任何外在力量都難以動搖的。現當代文學名著中有些作品,因為特殊機緣而被改編為話劇和電影,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準的《李雙雙小傳》,曾被改編為電影《小二黑結婚》和《李雙雙》,在普通民眾中產生過很大影響----這當然也證明了原著具有相當的經典性,因此它們的經典地位就相對牢固些。尤其是《李雙雙小傳》,它在內容和藝術上的不足很明顯,但所有的當代文學史都無法將它繞過,甚至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還對它和電影《李雙雙》進行了專節的對比分析。顯然,電影《李雙雙》對小說原著的經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使得原著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藝術和內容上都對原著有所升華(人們公認電影《李雙雙》比原著藝術成就為高)。
影視改編對金庸小說經典地位的確立,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是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1962年前,金庸盡管已創作出《書劍恩仇錄》(1955)、《碧血劍》(1956)、《射雕英雄傳》(1957)、《神雕俠侶》(1959)、《雪山飛狐》(1959)、《飛狐外傳》(1960)、《倚天屠龍記》(1961)、《鴛鴦刀》(1961)、《白馬嘯西風》(1961),并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還遠達不到洛陽紙貴的地步。紙質文本對金庸小說傳播的速度,是相對緩慢的。60年代前期,是電影改編金庸小說的第一個高峰期[注]參見林保淳《解構金庸》,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頁。1958年到1994年間,根據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共49部,其間有三個改編高峰。一是1960—1965年間,二是1977—1984年間,三是1990—1994年間,三個時期根據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數量分別為15部、15部、14部,共計44部。,其后,金庸小說在香港的流行面才迅速擴大,金庸當時“大量的小說讀者是由電影觀眾轉變而成的”[8]。金庸小說在大陸的接受史,情形也類似。1985年金庸小說在大陸流行,受電視劇《射雕英雄傳》的熱播影響明顯。有研究者對此考察后曾說:“不能忽視的是金庸電視劇《射雕英雄傳》的熱播,也反過來促進了金庸小說的銷量,幾乎達到一紙風行的地步。”[9]
正是金庸小說的大面積流行,才使得一些大陸的文學研究者,逐漸開始深入思考“五四”以來一直受到新文學批評和排斥的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意義。錢理群曾表示:“說起我對金庸的‘閱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說是學生影響的結果。那時我正在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確實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于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說:‘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說完全了解了現代文學。’他并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別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淀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說看,而且一致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的多。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確實大吃了一驚……。”[10]相似的意思嚴家炎、陳平原都表達過。嚴家炎在其專著《金庸小說論稿》開頭,先列舉了金庸小說作為“一種奇異的閱讀現象”的四個特點:“持續時間長”、“覆蓋地域廣”、“讀者文化跨度很大”、“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這實際上也是說明了他的研究源于金庸小說的流行。此后,大陸文學研究者對金庸小說研究不斷深入,其經典性逐漸被知識精英階層所認識和接受,金庸小說才在90年代被確立為文學經典。
嚴肅的啟蒙性新文學經典,改編數量也相當可觀。據統計,到2007年為止,魯迅小說的戲劇、影視、連環畫改編本至少有38種之多[注]根據葛濤的《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中所列的改編情況統計。;巴金的小說《家》改編至少有33次[注]根據李存光的《〈家〉〈春〉〈秋〉版本圖錄·研究索引》(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中所列改編情況統計。。還有論者稱:“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中,老舍是迄今為止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最多,而且質量最高的一位。”并稱之為“老舍現象”[11]。這個論斷不一定精確,但老舍的作品被大量改編則是事實。沈從文的作品,一方面解放后長期在大陸被禁,另一方面由于故事性不強,被改編的條件比較欠缺,即使如此,小說《邊城》仍有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出現的兩個改編電影。從改編的頻繁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出某一部作品受到的推崇程度----那些經典性最強的作品才容易受到不同階層、不同時代的文人重視,從而獲得較大數量的改編。從魯迅、巴金、老舍、茅盾、沈從文等人作品的被改編數量來看,不僅他們的總體改編數量突出(當然由于各自作品風格的差異,他們作品的改編數量也并不平衡),更重要的是,他們各自最經典的作品無一例外地都比他們的其他作品改編頻率要高的多。如魯迅小說中改編數量最多的是《阿Q正傳》,至今各類改編約有20種,而《祝福》雖說在魯迅小說中改編數量處于第二位,卻只有約8種改編本。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家》的改編本約有33種,數量最多,而《春》和《秋》的改編數量在巴金的所有小說中,雖僅次于《家》,卻各自只有6種改編本。此類現象,也可以在老舍、茅盾、沈從文的小說改編中得到印證。一部作品的每一次改編,都是改編者對它的一次肯定,它連續地在不同時代獲得改編,就是不斷得到不同時代的知識階層的肯定。這不斷被肯定的過程,就是作品不斷被經典化的過程----改編由此促進了新文學作品的經典化。
四、 結 語
當然,應該看到改編只是經典普及和名著經典化的一種手段,我們不能將其夸大和絕對化。對于不同題材的經典,改編參與名著經典化過程的程度并不相同,如影視改編對敘事性的小說和戲劇更方便些,改編散文和詩歌就困難些。因此,改編對散文和詩歌的傳播和經典化作用,顯然并不明顯。盡管如此,由于真正的文學經典,民間性是其應有之義,而改編作為通俗性傳播方式、一個普及經典的方便橋梁,就和文學經典及其經典化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種種關系。因此,改編無疑是文學作品經典化中一個永遠難以繞開的話題。
參考文獻:
[1]羅吉·曼威爾. 莎士比亞與電影[M]. 史正,譯.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1984.
[2]張琦. 金庸在西方[N]. 文藝報, 1997-01-28(3).
[3]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287.
[4]宗白華. 常人欣賞文藝的形式[M]∥藝境.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175.
[5]杜衛·佛克馬. 所有的經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M]∥童慶炳,陶東風. 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和重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17.
[6]王國維. 宋元戲曲史[M]. 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6:40.
[7]鄭振鐸. 水滸傳的演化[M]∥鄭振鐸文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
[8]宋偉杰. 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沖動[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9:40.
[9]李云. 邁向“經典”的途徑----“金庸小說熱”在大陸:1976—1999[J]. 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21(3):1-8.
[10]嚴家炎. 金庸小說論稿[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1-2.
[11]高思新,朱杰. 傳媒時代的經典----老舍作品的影視劇改編[J]. 理論月刊, 2005(10):14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