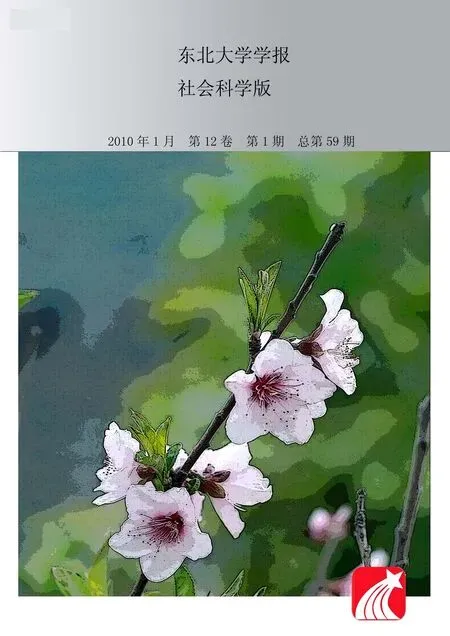科學認識的模式
----以微血管減壓術的發展為例
張今杰,徐志欣
(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湘潭 411105)
科學認識是人類面對復雜而神秘的自然界時所采取的一種理性行為,也是人類對自然界進行認知的成果。“人類在創造自身生存條件的活動中,為了能夠反作用于自然界,包括人類自身,首先必須發現自然的奧秘,認識自然的規律性,并因此獲得自由。一切科學認識和科學發現都是復雜的人類活動。”[1]97人類在長期的科學認識活動中,總結出了一些普遍而有效的規律或者模式。現代西方的科學哲學中不少流派的代表人物都競相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理論來證明這一點。如托馬斯·庫恩的“范式論”、卡爾·波普爾的“否證論”、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他們的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科學認識進步的規律或模式。醫學的發展和進步同樣遵循一定的模式。本文試圖以醫學中微血管減壓術的產生、發展和成熟并最終成為治療竇性心動過緩的一種新術式作為實例,說明科學認識發展的模式。
一、 微血管減壓術的臨床實踐
微血管減壓術是現代臨床醫學中的一種常用的術式。“微血管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簡稱MVD) 是指應用顯微外科操作技術,將走行于三叉神經、面神經等顱神經根部并對神經進出腦干區造成病理性壓迫的血管推移墊開,以解除血管對神經的壓迫,治愈相應臨床癥狀的一種術式。”[2]人們早在上世紀40年代在尸體解剖時就發現,在三叉神經痛(trigeminal neuragia,簡稱TN)和面肌痙攣的患者中的顱內小腦延髓池里存在動脈血管對顱神經的接觸或壓迫,這種壓迫的出現幾率較高。美國的Gardner在1962年首先報道用微血管減壓治療面肌痙攣。當時的微血管減壓的治療效果還不是十分確切,1966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的Jannetta教授將顯微外科技術成功用于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HFS)的手術治療,并將這一手術命名為微血管減壓術。Jannetta手術效果比Gardner明顯提高,Jannetta也提出微血管減壓術的原理。他認為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的病因學是三叉神經(第五顱神經)和面神經(第七顱神經)的出根區/入根區(root exit/entry zone)存在橋小腦角的動脈血管壓迫,導致三叉神經和面神經受到刺激引起的臨床癥狀。他認為將壓迫血管推開減壓后,受累的神經去掉壓迫,神經功能恢復正常后臨床癥狀將自動消失。手術治療原理采用“插入法”,解除血管對神經的壓迫,其關鍵步驟是判明責任血管后,將血管充分游離之后再將其推移離開面神經,將適當大小的Teflon棉放置在責任血管和腦干之間。Jannetta的微血管減壓術的原理由于其治療效果的相對確切(創傷小、治愈率高、手術并發癥發生率低,特別是其完全保留血管、神經功能的特性),逐漸被世界各地神經外科醫師所接受。另外,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及磁共振血管斷層造影(MRTA)除提供清晰的神經血管圖像外,還可以分辨責任血管的形態來源走行及與神經壓迫的關系。因此,“隨著手術經驗的積累和神經影像學的發展及鎖孔技術的應用,MVD技術已經是治療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的首推治療方法”[3]。
美國的Steven教授等人對美國1996—2000年全國性的住院患者采用追蹤隨訪性研究,結果顯示,“采用MVD治療三叉神經痛患者1326例,面肌痙攣237例,舌咽神經痛27例,總死亡率只有0.3%,有神經方面并發癥1.7%,術后腦脊液(CSF)漏0.4%,0.7%的患者需呼吸機,3.4%的TN患者同時接受了三叉神經感覺根切斷術”[4]。這些研究數據顯示對于藥物及其他方法難以控制的TN患者實行MVD治療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方法。國內左煥琮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用微血管減壓術治療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由于中國的此類病人數量巨大,我國的微血管減壓術已經十分成熟,治療效果也十分滿意。
二、微血管減壓術的發展所遵循的科學認識模式
從微血管減壓術的提出、完善到正式成為一種新的術式的過程來看,微血管減壓術作為人類對自身這樣一個認知客體所進行的認識的取得遵循了一定的模式,總起來說,它經歷了幾個前后關聯的發展階段。
1. 醫學實踐中遭遇難題
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是臨床上十分常見的疾病,50~60歲的中老年人發病率最高。三叉神經痛是一種在面部三叉神經分布區內反復發作的陣發性劇烈神經痛,被人稱為“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經痛是神經外科常見病之一,也是國際公認的疑難雜癥之一。由于其發病機理長期未能明確,藥物治療時一般是服用鎮痛劑,只能暫緩疼痛,且有副作用。而手術治療則大多對神經有一定的破壞,會引發其他方面的疾病,而且容易復發。
面肌痙攣即面部一側抽搐(個別人出現雙側痙攣),精神越緊張、激動痙攣越嚴重,直至發展為口眼歪斜。面肌痙攣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原發型面肌痙攣,一種是面癱后遺癥產生的面肌痙攣。兩種類型可以從癥狀表現上區分出來。原發型的面肌痙攣,在靜止狀態下也可發生,痙攣數分鐘后緩解,不受控制;面癱后遺癥產生的面肌痙攣,只在做眨眼、抬眉等動作時產生。我國民間治療面肌痙攣的方法繁多,面肌痙攣治療時間都較長,如貼膏藥治療、服中藥治療、針灸等常規治療,但大多傳統口服藥物只是單純地通經活絡,祛風化淤,只會見效,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這些常規治療方法在緩慢治療的同時,也給病人帶來了許多不便。病人往往得長期生活于痛苦之中。
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成為了困擾人類多年的難治之癥,不過,隨著微血管減壓術的出現,這個難題就有了解決之道。
2. 臨床醫學的實驗嘗試
臨床醫學歷史悠久,“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創立醫學形成學派,堅持把疾病看做是一種要服從自然法則過程,強調用細致的觀察來研究疾病,因而對許多疾病進行了描述,并提出了適當的治療方法,是現代臨床醫學的開端”[5]。人們認為,我們今天也只有從臨床現象的觀察到病理規律的把握,再從病理規律的掌握到新術式的采用,以及這些過程的循環往復中,才能不斷地推進醫學的發展和完善。
早在上世紀的上半葉,就有多種開顱手術應用于三叉神經痛的治療,包括三叉神經節減壓術,圓孔、卵圓孔減壓術,三叉神經感覺根切斷術,硬腦膜減壓術,三叉神經根減壓術等。根據1934年美國的Dandy的報道:“經枕下開顱手術治療三叉神經痛215例,在三叉神經出根區(root exit zone,簡稱REZ)意外發現了神經根被動脈瓣壓迫66例(30.7%),靜脈壓在神經根30例(14%),提出了微血管壓迫(MVC)這一概念,并且將其推廣到面肌痙攣的發病原因中,進而提出,MVC是顱神經疾病一個不可忽視的致病因素。”[6]1959年美國的Gardner對18例TN患者采用枕下開顱小腦橋角探查術,發現有6例血管壓迫神經根,將壓迫神經根的血管剝離開減壓后,疼痛消失而治愈,并提出了“短路”(short circuit)學說。Gardner指出:“使用脫脂海綿解除這些血管壓迫獲得良好的臨床療效 。”[7]正是這些醫學研究人員通過不斷的臨床醫學的實驗嘗試,才有了微血管減壓術的漸趨完善,這個實驗嘗試過程也并不是獨立進行的,而是始終與科學認識的其他過程相伴而行的。
3. 科學假說的提出
人類往往在經過一系列的實驗嘗試過程之后,會對所研究的問題提出一些嘗試性的假說。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定義,科學假說是指根據已有和新的科學事實對所研究的問題作出的一種猜測性陳述。它是將認識從已知推向未知,進而變未知為已知的必不可少的思維方法,是科學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一對科學假說的規定中,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科學假說具有猜測、假設的性質,還不屬于被實踐所驗證了的科學事實;二是科學假說又不同于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而是以已知的科學知識和新的科學事實為基礎,是在這些基礎上提煉出的科學問題,并在多種科學知識基礎上運用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類比和想象等方法,形成解答問題的基本觀點。波普的證偽原則告訴人們,“一切科學理論都只是猜測和假說,它們不會被最終證實,但卻會隨時被證偽,證偽的過程使用試錯法的程序:假說—事例—(更完善的)假說”[8]。因此可以說假說是通向理論的必要環節,科學假說是科學理論的可能方案。科學假說帶有或然性,微血管減壓術治療三叉神經痛和面肌痙攣的原理最初僅僅是一種假說。
在對微血管減壓術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對面肌痙攣的患者進行微血管減壓治療的時候,在國際上首先觀察到一種臨床現象:面肌痙攣的患者中有一部分合并有竇性心動過緩(竇性心率慢于每分鐘60次),而且在大多數這些患者的微血管減壓術中可以見到與面肌痙攣同側的迷走神經或者延髓腹外側也存在顱內動脈血管的壓迫。術中對個別患者同時進行了迷走神經或延髓腹外側的減壓,術后觀察到患者的心率明顯增加。研究人員選擇了部分合并有竇性心動過緩的面肌痙攣患者,對這些壓迫血管同時進行減壓,觀察這些患者的術后心率變化。結果發現這些竇性心動過緩的患者的面肌痙攣癥狀多數發生于右側臉部,術后近期(約一周)和術后遠期(1年)的心率無統計學差異;術前的心率和術后近期及遠期的心率比較均有顯著的統計學差異。研究人員于是提出假說:面肌痙攣合并竇性心動過緩的原因是顱內動脈血管對迷走神經顱內段或者延髓腹外側的壓迫導致延髓內的疑核或迷走神經背核,迷走神經顱內段受到刺激,迷走神經的興奮性增高。支配心臟的心迷走神經具有負性的變時變傳導作用,因此引起心率變慢。竇房結主要受右心迷走神經的支配,因此具有明顯的右側優勢。這只是研究人員對這種現象提出的假說,并沒有得到證實。
4. 實踐的檢驗
把假說運用于實踐,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事實和這個假說相符合,并且沒有任何已知事實和它矛盾,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假說接受為理論,它具有相對的真理性。所以,我們必須把假說放到實踐中去接受大量實踐事實的考驗,或者用科學實驗去證明(證實)或反駁(證偽)它。在假說與實驗之間的關系問題上,20世紀初不少科學家已經注意到:不停地提供材料的實驗和不停地進行解釋的假說之間不斷的斗爭,推動著科學認識不斷前進。“在這一對立中,一方面,假說的提出和驗證要有實驗根據;另一方面,實驗的設計和進行實驗的解釋又必須依賴于假說。”[1]101
無論在驗證假說還是導致新理論的情況中,科學實驗毫無例外都是科學認識的源泉和檢驗真理的標準。有一類實驗不是對某些客體或自然現象本身進行實驗觀察,而是先設計與該客體或自然現象相似的模型,用它們模擬原型,如用動物去模擬人,通過對模型的實驗來間接研究原型的性質和特點。如動物實驗就是醫學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指在醫學研究中給予動物某種實驗處理后觀察動物反應及其規律性變化,并將結果推論到人的過程。它在人類的疾病調查和防治研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模型實驗大大擴展了人們進行經驗研究的可能性,它是一種間接的經驗。為了進一步得到更多的證據來證實前面提出的假說,研究人員也進行了動物實驗。開顱對貓的迷走神經或延髓腹外側進行一定程度的壓迫,實驗動物分左右側和對照組,結果發現壓迫右側延髓腹外側后心率有明顯的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效果在一定時間內得到保持。實驗結果支持研究人員提出的假說。
任何假說都應具備解釋功能和預見功能。根據上述假說,神經受到動脈血管的壓迫會導致功能的異常。但為什么這種情況只在三叉神經和面神經發生,而沒有在其他部位出現呢?許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有人認為,如果其他部位的血管壓迫神經,而血管和神經的情況也大體相同的話,也應該會引起相應的臨床癥狀。于是人們繼續進行檢驗,后來發現對第9顱神經微血管減壓后有治療舌咽神經痛的效果,并且已經逐步應用于臨床。但是在對其他部分的血管和神經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表明,上述假說并不成立,這是什么原因呢?進一步的研究結果能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血管對神經的壓迫主要發生在橋小腦角,因為在顱內甚至全身只有這個部位有潛在的腔隙,并且血管神經十分豐富,大部分的顱神經都在此經過。椎基底動脈的主干和分支也走行在這個區域,而且血管的走行變異較大。因此這里血管對神經的壓迫相對來說是常見的。近年來人們又發現偏頭痛的病因可能也與血管壓迫有關系。對引起偏頭痛的主要神經(眶上神經、耳顳神經和枕大神經)的減壓在部分偏頭痛患者中取得了成功。對于全身其他部位血管壓迫臨近神經的情況則大不一樣。在四肢和體腔,由于動脈血管和神經一般都是走行比較規律,變異不大,周圍多是軟組織,缺乏束縛,故很少引起對神經的壓迫癥狀。而顱腔容量較小,被顱骨固定,潛在腔隙小,其中走行的神經血管比較豐富,走行變異較大,此部位的顱神經出顱部位神經裸露,行程較遠,位置相對固定,容易形成血管對神經的壓迫。
回過頭來再分析顱神經的解剖特點,就能發現這種壓迫現象其實應該是一種必然要存在的現象。顱神經一共有12對:視神經、嗅神經、動眼神經、滑車神經、三叉神經、外展神經、面神經、聽神經和前庭神經、舌咽神經、迷走神經、副神經、舌下神經。前面我們已經對迷走神經有所分析,就不再贅述,這里再分析一下其他11對顱神經:視神經和嗅神經本身位于前顱窩底,沒有伴行的較大的動脈血管,動眼神經、滑車神經、外展神經細長柔軟,動脈血管難以對之形成張力性壓迫,因此臨床目前沒有發現動脈對這些神經的壓迫癥狀。三叉神經和面神經相對短粗,行程固定,因此容易被變異的動脈血管壓迫出現臨床癥狀。舌咽神經行程也相對固定,長度中等,舌咽神經應該也可以出現動脈血管的壓迫癥狀,舌咽神經已經在臨床被證實有壓迫癥狀,并且微血管減壓有一定的治療效果。副神經的部分神經根行程較短,此部分神經根可能出現壓迫癥狀,在痙攣性斜頸的患者術中切斷部分副神經根可能就是這個原因。舌下神經行程相對較長,難以出現壓迫癥狀。迷走神經的顱內行程不長,直徑中等,動脈血管能否造成壓迫迷走神經的癥狀呢?按照前面的一般推理,應該是可以出現的。
5. 術式的推廣應用
我們認識自然界的奧妙,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人類不斷探索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為了將認識到的真理用于指導實踐。任何科學認識,都來源于實踐,并最終回到實踐。對此,列寧曾作出深刻的概括:“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途徑”[9]。也就是說,認識的目的是為了實踐,“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0]。那么,科學家們所提出的這種在微血管減壓術應用中通過了實踐檢驗的假說真的能指導我們的實踐嗎?
研究人員結合此假說的原理和竇性心動過緩病癥的特點,認為這種術式完全可以用于治療竇性心動過緩。在臨床上,盡管大多數竇性心動過緩(如心率不低于每分鐘50次),沒有癥狀,并不需要治療,只有少數有心輸出量不足的患者才需要植入起搏器治療,但專家們認為,許多沒有面肌痙攣的單純竇性心動過緩的患者也可能是由于顱內動脈血管壓迫引起的,如果他們出現心輸出量不足的情況,如果能夠通過減壓增加心率,增加心輸出量,就有可能避免心臟起搏器的植入。因此,人們相信對迷走神經或者延髓腹外側的微血管減壓將來可能成為一種治療有癥狀的竇性心動過緩的手段,成為一種應用性很強的新術式。
現代醫療器械的進步為這種新術式的應用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許多新的技術已應用于MVD。其中有關神經內鏡的報道較多,神經內鏡可用于橋小腦角的探查,也可輔助顯微鏡用于MVD。因顯微鏡有所謂的“死角”,內鏡可作為輔助手段,用以顯示腦池,尋找變異的血管,顯示壓迫神經的血管。減壓結束后,內鏡可用來確立手術的完整性。在一些病例中內鏡可用以輔助電切和電凝靜脈,對血管神經的高倍數放大在探查橋小腦角時尤顯重要。雖然神經內鏡也存在一些問題,有關內鏡的圖像融合技術、握持裝置、防霧裝置、沖洗裝置也有待進一步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手術的成功率,但是,“隨著這些問題的克服及顯微鏡與內鏡融合技術的不斷發展,神經內鏡的使用會越來越廣泛”[11]。相關醫療器械的進步為這種新術式的推廣應用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由此可見,微血管減壓術治療竇性心動過緩是大有可為的。
三、 科學認識發展的一般模式
人類對自然界及自我的認識是全方位的,微血管減壓術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的方面。從微血管減壓術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科學認識的發展不是隨機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這些模式在實踐中被科學家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著。
那么科學認識發展的源頭是什么呢?早期的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始于觀察所得的經驗材料,科學認識最后又必須回到經驗中進行檢驗。波普爾則強調“觀察滲透著理論”。他說:“我們的日常語言是充滿著理論的,觀察總是借助于理論的觀察。”[12]在他看來,客觀的、無先入之見的觀察以及觀察陳述是不存在的,一切科學觀察都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是滲透著理論的觀察,因此觀察并不是科學的真正起點。科學開始于問題,始于科學研究和生活中所遇到的難題。“應當把科學設想為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13]科學理論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猜想,而觀察乃是對這種猜想的檢驗和反駁。在這里,波普爾把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倒轉了過來,成為邏輯實證主義過渡到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關鍵人物。波普爾的觀點雖有偏頗之處,但總體上來說有一定的合理性。
面對難題,科學家共同體會提出一系列相互競爭的科學假說,任何科學認識最先都僅是一種假說,而假說則是一組模型化的解釋命題。科學家們借助于這種模型化的解釋命題,把他們對于對象的認知模擬出來。這種模型所描述的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整體性的相似關系。正因為有這種相似關系,這種理論模型才可能在科學實踐中成功地解釋和預言科學現象。理論模型是科學家們建構出來的,但這種建構并非純粹是理性的,而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
科學家們建構出來的假說無疑帶有一定的虛構性,但是這種虛構性將會在與公認的實驗事實的比較中不斷地得到矯正,并且不斷地向著與真實世界的一致性逼近。在科學認識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并存著相互競爭的假說系統,分別描繪出相互競爭的幾個不同的可能世界,這些可能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相似性程度決定了人們對這些假說的取舍態度。人們一般都會選取相似性程度較高的假說,并對其進行經驗和實驗的檢驗,不斷進行修補和完善,一步步增加其真理性的程度。也就是說,這種相似性不是兩個系統之間的固定不變的關系,而是會隨著我們對世界的深入理解和認知而不斷增強。當假說系統在解釋和預測科學事實的實踐中不斷經受住考驗時,人們就會承認和接受它為一種正確的理論,同時將其應用于科學研究和生產、生活的實踐中。
微血管減壓術的產生、成熟和發展及推廣為我們呈現了科學認識發展的一個典型范例。在臨床醫學中,醫學研究人員通過微血管減壓術的實踐中所偶然發現的迷走神經被壓迫的癥狀,提出了迷走神經被壓迫的假說,并通過相關患者的手術和動物實驗初步檢驗了這種假說,然后將此假說作進一步的推廣應用,試圖將微血管減壓術作為治療竇性心動過緩的一種新術式。
四、 結 語
科學認識不是理論系統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絕對的一致性的表征,而僅是理論模型與實在世界之間一定程度上的相似關系。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對自然界認識的不斷深入,這種相似關系最終將逐漸地趨向模型與世界之間的一致性關系。也就是說,科學真理將是關于世界的理論模型與實在世界之間的相似關系的一種極限,這是科學認識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微血管減壓術這樣一個臨床醫學技術發展的案例本身給我們展現了科學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科學的發展需要經過實驗嘗試、提出假說、實踐檢驗和推廣應用等環節。這個科學認識發展的程序,既不是純量變的“積累式”,也不是純質變的“革命式”,而是把量變和質變統一起來的科學認識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劉大椿. 科學技術哲學導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2]Jannetta P J. Microsurgical Manage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Arch Neuro, 1985,42:800.
[3]Hainess S J, Jannetta P J, Zorub D S. Microvascular Relation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An Anatomical Study with Clinical Correlation[J]. Neurosurgery, 1980,52:381-386.
[4]Kalka anis, Steven N. M D, Eskandar, et al.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in the Unites States, 1996 to 2000: Mortality Rates, Morbidity Rates, and the Effects of Hospital and Surgeon Volumes[J]. Neuro-surgery, 2003,52:1251-1262.
[5]黎松強,張學先. 解“李約瑟難題”看現代科學[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63.
[6]Dandy W E. Concerning the Cau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Am J Surg, 1934,22:447-455.
[7]Gardner W J, Miklos M V. Respon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to “Decompression” of Sensory Root: Discussion of Cau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JAMA, 1959,170:1773-1776.
[8]趙敦華. 現代西方哲學新編[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227.
[9]列寧. 哲學筆記[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81.
[10]余源培,吳曉明. 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文本導讀:上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42.
[11]王召平,種衍軍,朱廣廷,等. 三叉神經痛微血管減壓術的現狀與進展[J]. 中華現代外科學雜志, 2005(5):438-439.
[12]波普爾. 科學發現的邏輯[M].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6:31.
[13]波普爾. 猜想與反駁[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