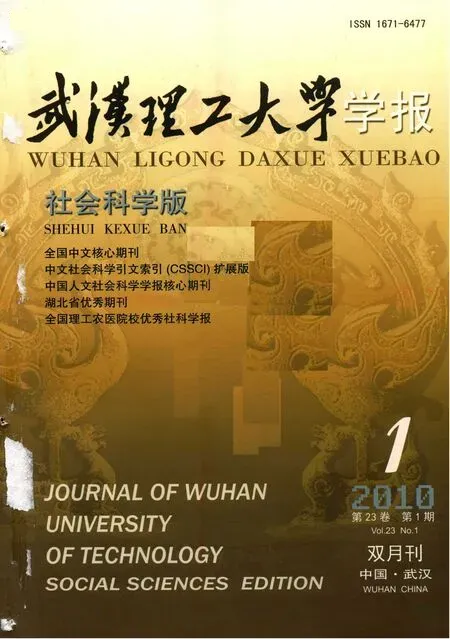論當前死緩適用的問題與對策*
李 萍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875)
論當前死緩適用的問題與對策*
李 萍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875)
死緩的確立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司法適用中也凸顯出適用標準不一致,適用范圍不當擴張等問題,甚至成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和維護審判效果的手段。應當結合司法實踐,對死緩適用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從立法上進一步規范死刑適用條件,正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確實抵制外界不當干擾。
死緩;適用標準;刑事司法理念;寬嚴相濟
死緩制度是我國獨創的一種死刑執行制度,它既具有死刑特有的威懾力,又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刑罰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對貫徹執行“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縮小死刑立即執行的范圍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不可否認,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過程中,死緩的適用①還存在著司法適用標準不一,隨意性大,不當擴張等問題。筆者作為一名與死刑案件零距離接觸的刑事法官,得以直觀地研究死緩的適用,在此試就死緩適用存在的問題與對策進行探討。
一、死緩適用中存在問題和缺陷
近年來,隨著司法實踐中對死刑適用的嚴格控制,死緩適用的范圍逐步擴大,死緩的適用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死緩刑的適用標準不盡一致
死緩刑的適用標準不統一,是司法實踐中反映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隨著寬嚴相濟和“少殺慎殺”刑事政策的貫徹實施,法官在死刑裁量時會更加慎重,但哪些情況下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死刑”,各級法院,各地法院,各個法官,甚至同一法官不同時期的觀點都不一致。三級法院所掌握的死緩刑標準有一定差異,其中,高級法院與最高法院掌握的標準較一致,而與中級法院分歧較大。由于死緩適用條件的不明確性,在實際執行中也容易異化為司法人員操弄的司法工具,為司法腐敗創造可乘之機。
(二)死緩適用的范圍不當擴張
隨著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死刑控制力度加大,死緩的適用范圍也不斷擴大。2007年全國判處死緩的人數,多年來第一次超過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1]。這不僅是我國慎用死刑的體現,也說明死刑復核權上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審判實踐中,也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是把死刑數量的跌漲作為是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少殺慎殺”的硬指標,為追求死刑數量的減少而對一些罪大惡極,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告人判處死緩;二是把死緩作為介于死刑和無期徒刑之間的刑種,為了嚴懲犯罪分子,或為了迫使其在二審中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損失,對具有法定從寬事由且阻卻死刑適用的被告人判處死緩刑。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在實踐中尤其是死刑適用日趨嚴格、慎重的背景下,死緩的具體適用卻偏離了最初的設置目的,被當作僅次于死刑的最嚴厲的刑罰而得到了廣泛的適用,并使得刑罰裁量的不平衡更為突出。”[2]
(三)死緩成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
司法實踐中有一些證據存在瑕疵的疑罪案件,由于法院退查權廢除,公安、檢察機關迫于外界的壓力,最終把這類案件都移送到法院解決。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往往會陷于兩難境地:如果宣告無罪,就會招致社會各界的質疑,也可能會引發被害方的私力復仇、纏訴上訪等社會矛盾;如果草率判處死刑,法院、法官就會獨自承受錯案追究甚至被刑事追究的壓力。法院既沒有信心判處死刑,也沒有勇氣作出無罪判決,只好將案件降格處理,判處死緩刑。“在這種態度指導下,某些死緩判決已經脫離了刑法規定的原意而變成一種含混不清的折衷式判決”[3]。事實證明,這種折衷式判決往往會造成冤錯案件,如近年來發生的李化偉冤錯案,一審法院在審理時就發現該案有十大疑點,二審法院也認為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但還是“勉強”判處了李化偉死緩刑,直到警方在偵破另一起案件時抓獲真兇,李化偉才從屈蹲了14年的大獄中被釋放[4]。
(四)死緩淪為維護社會效果的工具
司法實踐中有這樣一類案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本應當在無期徒刑以下量刑,但由于受到來自地方黨委和政府、社會輿論和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壓力,法院往往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之間難以取舍:對被告人判處死刑或者死緩,毫無疑問可以撫慰民情公憤,消解被害人的冤恨,但卻有違法律規定及刑事政策;如果依法在無期徒刑以下量刑,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心里落差將會很大,由此可能導致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無奈之下,一審法院往往對被告人判處死刑或死緩,將“皮球”踢給上級法院解決。筆者就親歷了這樣一個案件:被告人明某系在校大學生,因戀愛糾紛,在被害人激怒之下實施了殺人行為,隨后投案自首。經法醫鑒定,明某在作案時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對于這樣一個具有多個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案件,由于地方黨委的干涉和被害人親屬的不斷施壓,一審法院判處明某死刑,二審法院在重重壓力下改判明某死緩。判決宣告后,被害人親屬仍不罷休,四處上訪,并不斷糾纏承辦法官。可見,在現有的司法環境下,死緩有時并非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則裁判的結果,而是成為了息訴的手段,維護司法的社會效果的工具。
出于種種原因,“在實踐運作當中,死緩制度的原初面目日漸模糊,宛如普洛透斯的臉,時而表現對被告人的生命及人權的尊重,時而又成了彰顯嚴厲打擊犯罪的利器,時而是阻卻或削減死刑適用的有效工具,時而又成為安撫被害方的便利手段”[5]。
二、導致死緩適用問題的原因分析
導致死緩適用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的缺陷,司法人員主觀上的因素,也有不可避免的客觀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死緩適用條件不甚明確
我國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首先,“罪行極其嚴重”這一死緩適用的前提條件,其本身表述比較抽象,并且相當程度上具有重行為人的客觀危害,輕行為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裁判導向,對死刑的限制適用難以發揮強有力的引導作用[6]。其次,“不是必須立即執行”這一適用死緩的實質條件,采用否定式、不周延的立法技術加以規定,不僅抽象、模糊,而且實際操作性不強,賦予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各地司法機關在適用時各行其是,甚至導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審理出現截然不同的判決。再次,對犯罪情節的把握實踐中存在困惑。諸如應當如何認識和把握婚姻家庭糾紛的存在范圍和表現形式;被告人有自首情節的,在哪些情況下可以判處死緩,哪些情況下不能從輕,都是實踐中有待明確的問題。此外,我國《刑法》對一些影響量刑尤其是影響判處死刑的重要情節沒有法定化,如嚴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的過錯、毒品犯罪和其他有組織犯罪中的“犯罪引誘”等,由于缺乏剛性的規定,司法人員對死刑和死緩的界限難以分清。
(1)調節閥分為手動調節閥和電動調節閥兩種。電動調節閥一般是由電氣儀表專業根據設計參數進行選型。冷、熱源系統中安裝手動調節閥的位置一般在:①分水器的各個分支管上,對各支路流量進行調節;②換熱器一次水的回水管上,調節換熱器的供熱量。手動調節閥要選擇閥門開度和流量基本為等百分比型的,要根據管道的最大流量值確定調節閥的口徑,一般情況下閥的口徑要小于所安裝管道的管徑。
(二)刑事司法理念陳舊落后
“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現代司法理念雖然在我國相關法律中得到確立,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重刑主義、“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等傳統習慣思維方式和落后的司法觀念仍嚴重地影響司法人員的辦案。這在死緩的適用上表現為兩個方面。
1.重刑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在對中級法院死刑案件審理情況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對于只要有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院一般都考慮判處死刑,強調打擊犯罪的一面,而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情節則較少考慮,一般未予從輕處罰。特別是在一些有重大影響的命案中,因關注于嚴懲罪犯而忽視了對自首、正當防衛等情節的認定。可見在部分司法人員中已形成了重刑主義的思維定式和辦案模式,他們推崇刑罰的威懾功能,寄予了刑罰尤其是重刑預防犯罪過高的期望值。“在重刑主義者看來,犯罪增加的原因,要么是刑罰還不夠嚴厲,要么是殺的還不夠多。因此,在犯罪控制實踐中十分重視重刑和死刑的運用,希望能收到‘以殺止殺’的效果”[7]。司法者自身的重刑思想與社會中的死刑報應情感一結合,因顧及“民憤”和外在形勢需要,對于應當在無期徒刑以下量刑的非死刑案件“該寬不寬”,結果不當擴張了死緩的適用。
2.“有罪推定”觀念尚未根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但為何少數法院在審理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疑案時,明明知道證據不足或者疑竇重重,仍然會“留有余地”地對被告人判處死緩呢?除了制度的弊端和外界的壓力等客觀因素影響外,司法人員“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是主觀因素。正是由于少數司法人員內心確信被告人有罪,擔心“疑罪從無”會放縱犯罪,還會遭到有關部門的責難,對本應宣告無罪的案件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緩判決,從而釀成錯案。
(三)對刑事政策的錯誤解讀
近年來,死緩適用的不當擴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少數司法人員對刑事政策的誤讀。他們簡單地認為寬嚴相濟是對“嚴打”的否定,是刑罰輕緩化的代名詞;而把“少殺、慎殺”政策理解為必然導致死刑人數削減,一些司法機關甚至把死刑數量的跌漲作為是否貫徹“少殺、慎殺”的硬指標,這些片面的觀念和做法,直接導致了死緩的過度適用,放縱了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
(四)外界不當的壓力和影響
我國目前法制還不夠完備,公民法治素養普遍不高,殺人償命等復仇、報應思想還十分強烈。“‘復仇’在中國傳統法律中,已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關乎社會人倫道德與法律內在精神和外在標榜一系列糾纏不清的社會問題”[8]。加上主張少殺慎殺的人還僅限于法學界和部分司法人員,多數百姓和地方官員還是主張重刑,藉此來保一方平安,導致大量本應在無期徒刑以下量刑的案件被適用死緩。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可以判處死刑,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的案件,由于被害方的態度而影響死刑裁判的案件,并不是個別現象”[9]。
在辦理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倍受關注的命案時,司法機關往往會受到各界的巨大壓力。這些壓力或來自于被害人親屬、單位,或來自于媒體輿論,或來自于地方領導。在“從速、從重法辦兇手”的社會呼聲下,在“民憤極大”的影響下,在有關部門或地方領導的高度關注下,審判機關對于一些存疑案件和有影響的案件往往不能、不敢、不愿做出無罪判決,往往矛盾上交,依賴地方黨委協調。即使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不敢宣告無罪,而是降格判處死緩,以免承擔打擊不力的責難。
三、解決死緩適用問題的路徑探析
要解決死緩適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不僅要從立法入手,明確死緩的適用條件;也要從司法者入手,不斷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司法能力。
(一)立法規范死緩適用條件
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不少學者建議將“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具體化,以便于實踐統一適用,防止各地執法不一[10]。全國人大常委會部分委員提出“必須立即執行”的標準不明確,對在什么情況下適用死刑必須立即執行應當作具體規定,以減少執法的隨意性,但是,立法機關基于“注意保持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指導思想最后還是原封不動地未作細化修改[11]。由于當前司法實踐中死緩適用定位不準、隨意性大、不均衡、不統一的現象較為突出,有學者提出應對我國死緩制度進行變革,通過明示的列舉式因而是限定式規定死刑“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盡可能使死刑的執行成為例外,而使死緩成為通例[12]。有的學者提出應當重新構建死緩制度,將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范圍在立法上加以限制,僅僅局限于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暴力犯罪、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和嚴重侵害人身的暴力犯罪[13]。此外,還有較多的學者主張,刑法應明確規定將死緩作為所有判處死刑案件的必經程序[14]。這些見解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啟動法律修改程序并非易事,何況啟動法律修改程序后能否對死緩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也不容樂觀。
筆者認為,現階段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規范死緩的適用條件。
2.明確規定對經濟犯罪一般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對經濟犯罪應當明確以適用死緩為通例,適用死刑為特例。因為經濟犯罪屬非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不僅在犯罪基本構成特征中不包含暴力因素,而且不以他人人身為犯罪對象,其社會危害性顯然有別于故意殺人罪等暴力犯罪,尚不能被認為罪行極其嚴重”[15]。如果對非暴力犯罪判處死刑,就會有違刑法公平正義的立場,從而破壞各死刑罪名之間在把握“罪行極其嚴重”上的橫向平衡。
除了制定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還可以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召開會議統一司法政策,編發典型案例等方式,規范和統一死緩的適用。
(二)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司法理念直接影響著對具體案件的處理。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就會頑固地控制人們的頭腦,支配人們觀察事物的視角、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16].
1.強化和諧司法理念。強化以人權保障和司法公正為核心內容的和諧司法理念,走出重刑主義誤區,是正確適用死緩的認識基礎。要理性地認識死刑的威懾功能,切實增強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自覺性。“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17],這是貝卡里亞在200多年前就給人們提出的問題,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在貝卡里亞看來,“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列寧也認為:“懲罰的警戒作用決不是懲罰的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重要的不是嚴懲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18]這說明,刑罰的及時性、確定性比刑罰的嚴酷性更加重要。而司法實踐和現代犯罪學研究結論也已經充分證明,增加死刑的適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惡性犯罪案件的上升。解決犯罪問題的關鍵在于消除和抑制產生犯罪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刑等刑罰方法。因此,注重打擊犯罪和人權保障之間的動態平衡,最大限度地追求刑罰適用的公正性,才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價值所在。
2.牢固樹立“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是法律的理性選擇,也是司法昌明的必然要求。由于案件的復雜性,偵查手段的有限性,被害人或證人指認錯誤等情況都有可能使無辜的公民陷入刑事訴訟中。因此,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宣判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如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應推定其無罪。司法人員不能將眼前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視為罪犯;也不能圍繞其有罪而展開偵查和審判。對那些有一定社會影響,外界壓力大,干擾多的案件尤其應當如此。司法實踐中常常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當證據證明到相當的程度,會出現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沒有作案、大于無罪的情況,這就要求法官仔細甄別,只有在證據達到確實、充分,且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的情況下才能下判;否則,必須本著“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現代司法理念,勇敢地作出公正的法律判斷,而不能“留有余地”地作出死緩判決,把責任和代價轉嫁到被告人身上。這種做法從個案上講,有可能放縱了罪犯,但從整體司法環境看,則體現了法治對人權的高度尊重。
(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對刑事立法及具體司法實踐提供宏觀的、指導性的方針、原則和導向。“刑法之制定與運用,罪刑之確定與執行,都應由刑事政策的觀點出發,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為指向,不合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是不良的立法,離開刑事政策的判決與執行,也必定是不良的判決與執行”[19].死緩是刑罰適用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一項刑罰執行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要正確適用死緩,必須將其放眼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少殺慎殺”死刑政策的視野之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刑罰兩極化的發展傾向:即“寬松的刑事政策”和“嚴厲的刑事政策”兩個不同方向、并行不悖地發展,又叫做“輕輕重重”的兩極化刑事政策[20].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對罪行極其嚴重,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刑事犯罪分子,應當依法適用死刑,不能為了削減死刑數量而“當嚴不嚴”,判處死緩,從而放縱罪犯;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國嚴格控制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執行的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比較認同的報應與功利相統一的刑罰目的,對行為的客觀危害相對較輕,或者行為的客觀危害很重,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的情形,均宜判處死刑緩期執行[21]。正如馬克昌先生所說:“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罪當判處死刑但具有從寬情節的,依法不適用死刑是對該政策的貫徹落實,依法適用死刑亦同理。”[22]
此外,要注意劃清“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和“不得適用死刑”的界限。凡是犯罪分子具有“不得適用死刑”的情形,不屬“罪行極其嚴重的”,就不能適用死刑(包括死緩),而不能僅僅把這一情形作為適用死緩的量刑因素來考慮,否則就是曲解了立法原意。
(四)正確抵制外界不當干擾
盡管在現實條件下,司法者在死刑控制方面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仍然較大,但忠誠于法律和事實,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對犯罪人的權利予以應有的關注和保障,是司法者不能也不應該推卸的天職。司法機關要自覺服從黨委的領導,接受輿論監督,高度重視社情民意,維護好社會和諧穩定,但更要認識并承擔起法律賦予的職責,敢于和善于堅持依法獨立辦案。不要輕易對案件中的事實、證據認定問題以及實體適用法律問題采取不負責任的態度,為了嚴懲犯罪分子、安撫被害人、或者促使被告人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損失等原因,對本不符合“罪行極其嚴重”這一死緩適用前提條件的被告人判處死緩,將矛盾“踢”給上級法院。
司法者應理性對待民意,不應一味地去迎合、滿足民眾出自本能、情緒性的報應要求而增加死緩的適用,而應通過理性和文明的執法活動正確地引導涉案群眾。同時,司法者在嚴格執法的前提下,也應充分認識到犯罪給被害人一方所造成的巨大身心傷害和物質利益的損失,并在現行法律、政策和相關制度容許的范圍內,積極地予以安撫和補償,化解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的敵意,使其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社會的寬容。
注釋:
① 在刑事法一體化的視野中,死緩的適用不僅包括刑事實體適用,而且包括刑事程序適用。限于篇幅,本文僅對刑事實體適用進行研究。
[1] 楊維漢,陳 菲.慎殺少殺,死緩首超死刑立即執行[N].新華每日電訊,2008-3-11(6).
[2] 林 維.論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制度的異化[J].河北法學,2005(7):63-66.
[3] 陳杰人.死緩非為折衷而設[J].法律與生活,2004(8):24.
[4] 時代商報.妻子遇害丈夫被疑為兇手含冤入獄14年[EB/OL].(2005-04-16)[2009-10-30].http:∥new s.sina.com.cn/s/2005-04κ16/04505663768s.shtm l.
[5] 金 福.如何應對死緩的擴張適用——兼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正確理解[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65-67.
[6] 李 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死刑司法控制的困惑與對策[J].法學論壇,2008(4):115-121.
[7] 龍 洋.關于我國死刑政策與死刑限制的反思與重構[J].民主與法制,2005(11):83-85.
[8] 馬作武.中國古代法律文化[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87.
[9] 胡云騰.關于死刑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的裁量[M]∥中英量刑問題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28-129.
[10] 張正新.中國死緩制度的理論與實踐[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143.
[11] 高憬宏,劉樹德.死緩適用條件設置的四維思考[J].當代法學,2005(5):91-98.
[12] 盧建平.死緩制度的刑事政策意義及其擴張[J].法學家,2004(5):137-141.
[13] 劉 霜.我國死緩制度的發展及其完善[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76-78.
[14] 張 文,黃偉明.死緩應當作為死刑執行的必經程序[J].現代法學,2004(4):75-79.
[15] 趙秉志.論中國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廢止[J].政法論壇,2005(1):92-99.
[16] 李希慧,王宏偉.論死刑的司法控制——以死刑觀念為視角[M]∥和諧社會的刑法現實問題——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2007年度),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763.
[17] 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 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47.
[18] 陳興良.刑法的啟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7.
[19] 林紀東.刑事政策學[M].臺灣:臺北中正書局,1963:8-9.
[20] 儲槐植.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69.
[21] 劉志偉.通過死緩減少死刑立即執行的路徑探究——基于刑法解釋論的考量[J].政治與法律,2008(11):9-12.
[22] 馬克昌.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國法學,2007(4):117-122.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rrent Reprieve
LI 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Reprieve is China’s original system of a death penalty.This system not only has the deterrence of death penalty,and is practical to narrow the scope of immediate execu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which gives full p lay to the penalty function and transforming functions of education.But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the reprieve has some problem s,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applicable standards are still inconsistent,inappropriate expansions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so on.Combining the judicial practice,the author takes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reprieve application,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s well.
reprieve;applicable standards;criminal justice ideology;appropriate degrees of strictness
DF613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18
2009-11-21
李 萍(1972-),女,四川省內江市人,法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博士后,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兼審判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刑法學和犯罪學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重點調研課題“關于刑事審判工作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調研”;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8年重點調研課題“死刑適用標準研究”
(責任編輯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