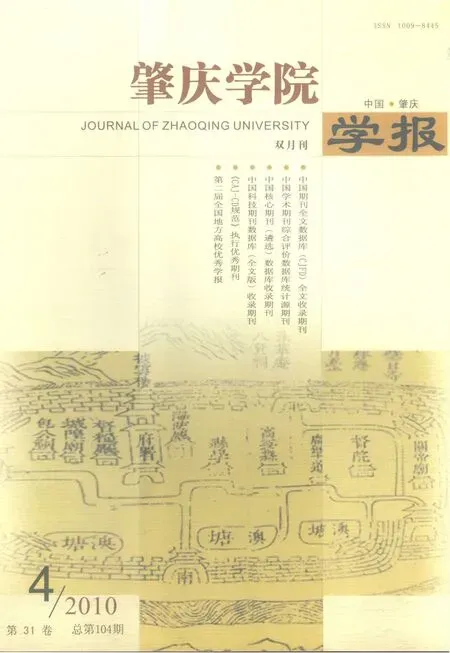《朗讀者》:鑿向多元敘述的利斧
——小說敘事藝術探微
仲米磊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廣東廣州510665)
《朗讀者》:鑿向多元敘述的利斧
——小說敘事藝術探微
仲米磊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廣東廣州510665)
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以精致、獨到的小說藝術贏得一致好評。其在文本敘事方面的主要特征是:鑲嵌并置的多重故事敘事,時間顛倒的時序倒置,隱喻與深層結構下的宗教話語言說;這些策略的運用,將小說的敘述藝術以多元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故事并置;時序倒錯;宗教氛圍
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1],作為有史以來第一部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德語書,以莊重的懺悔意識、嚴肅的人性思考,對愛與性、背叛和死亡,做了一個全新的注解;同時,以普通小人物的轉變為焦點,采用多元的文本敘述意識來結構小說,將這個飽含著愛與罪惡、秘密與救贖的故事予以全新的演繹:“人并不因為曾做了罪惡的事而完全是一個魔鬼,或被貶為魔鬼;因為愛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愛之人的罪惡中去,并將由此陷入理解和譴責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惡還將置下一代于這罪惡的陰影之中。”這一具有普遍性的主題,在作家精致的文本敘述策略和結構藝術中予以盡情地展現,讓人感受到了敘述藝術的精妙和新奇。本文擬從敘事學的角度,對“鑿破我們心中冰封海洋”(卡夫卡語)的懺悔之作以欣賞和解讀。
一、“中國套盒”:多重故事的鑲嵌并置
敘事學,已不僅僅局限于敘“故事”,更在于注重“敘”的技巧和方式,已上升為一種“修辭”的藝術。在詹姆斯.費倫看來,敘事作為修辭的藝術,“這個說法不僅僅意味著敘事使用修辭,或具有一個修辭維度。相反,它意味著敘事不僅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動。某人在某個場合出于某種目的對某人講一個故事。”而且,“由講述者、故事、情節、讀者、目的組成的這樣一個基本結構在大多數敘事中至少是雙重的:首先是敘述者向他的讀者講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讀者講述的敘述者的講述。”[2]由此,形成了由多種聲音建構和傳達,多重故事彼此鑲嵌、并置的“中國套盒”式修辭藝術。所謂“中國套盒”式,既是技巧,更是敘事手段:通過變化敘述者(即時間、空間和現實層面的變換),在故事里面插入故事,在插入的故事中講述另外相關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在各自的分敘事中,圍繞“盒心”——講述事件的中心或主旨,在看似分散和凌亂中形成整體性的統一。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短暫的生命》、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等都對這一“套盒”式敘事技巧青睞。
在《朗讀者》的文本敘述中,至少有以下3個相關層面的敘事。這3個相關層面是:
(1)內部層面,是由漢娜敘述的:關于自己在二戰集中營看守所的所作所為,即她自己的故事。
(2)中間層面,是由米夏敘述的:他與漢娜的邂逅、交往及揭示她因文盲,為保守這一秘密而做出的種種選擇,并最終走上自殺道路的經過,即米夏的故事。
(3)外部層面,是由作家作為隱含的作者所建構和構想的層面:施林克作為敘事者講述的米夏所講的關于漢娜的故事的故事,即真實作家施林克的故事。
在以上3個敘事層面的故事中,層面(1),漢娜的敘述較多地被置于文本建構的背景位置,空白和縫隙也留有較大的空間,因此,只是作為層面(2)的參照和補充來體現,是“不可靠故事”,在故事講述中所體現的思想規范與隱含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差異。“如果一個同故事敘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關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敘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講述就會偏離隱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講述。”[3]漢娜始終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并不具有什么道義上的罪惡,只是沒有得到別人的理解:“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沒人曉得我本是什么人,干過些什么事。你明白嗎,如果沒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沒人能要求你講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在此,漢娜完全符合美國作家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對“不可靠人物敘述”的定義,使文本所具有的闡釋空間變得更加的廣闊。層面(2)的故事構成了文本的絕大部分,作為與隱含作者有相似觀點的米夏——敘述本人,也具有雙重的敘述角色:既是所經歷過事件的“親歷者”,又是對“親歷者”事件進行講述的講述者;是講述的主體,又是被講述的客體。由此,對同一事件,當以迥異的視角審視時,便形成了不同的關照方式:15歲的童年視角——茫然、懷戀:對女性身體的渴望和共處時的歡愉,“我在記憶里呼喚著那次靈肉際會”“朗讀,淋浴,做愛,并排小睡,成了我們幽會的常規節目”;敘事者的成人視角——自責、反思:“我曾經確信,是我的背叛和不忠攆走了她,而事實上,她不過是為了避免在電車部門出丑。”“我曾經是旁觀者,卻突然變成了參與者和共同裁決者。這個新角色不是我尋找和選擇的,可我卻擁有了它,無論我是否愿意,無論我是有所行動還是消極等待。”
兩種視角交替敘事,過去與現在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敘事聲音的“復合”與“疊加”,“敘事者”置身在兩種不同場域中,由此形成的話語姿態也形式各異:米夏童年腦海中的記憶,畢竟是他個人經歷,與漢娜從偶然的相識,再到身體的接觸,直至突然消失,一切都注定了他們兩代人之間代際身份的鴻溝是無法彌合的;他們都沒有錯,一個單身女人,一個懵懂少年,就這樣偶然地結合在一起。這些故事敘事,是以敘事者的童年追憶視角來顯現的;當過渡到成人話語時,又暗含著難以言傳的復雜情結:既有對已逝“美好時光”的欣賞和眷戀,但更多是深思其中在當下看來似乎不可能的荒唐,報之以否定和自責。不同基調之間,由此產生了濃厚了藝術張力,類似這樣看似矛盾的敘事呈現和不同話語之間的過渡轉化,“從敘事技巧的角度看,正是由于敘述者的這種雙重作用,才使得敘事不是單純的事件陳述,而是充滿了批判精神的自我回顧和自我剖析。”[4]達到了強烈的反思過去,對上一代人的罪惡進行悔過和審視的目的,兩種話語將反思的深度推向了更深一層,引人深思。
“套盒”式敘事策略不僅是整部小說的整體模式,更是每一個分故事中的子一級敘事框架,在每一級中,各種故事混雜在一起,但統一于一個核心,在層層解析中撩開故事的真實面目,讓人在敘事的迷宮中走向清晰,對漢娜的過去、講述者米夏的過去及隱含作者的意圖策略進行了解構,顯示了敘事手段的新穎和別致。
二、“時間倒錯”:雙重時序的倒置
多重故事的互相纏繞,體現在文本結構上,突出特點便是錯置的時間安排。《朗讀者》文本最明顯的特征是較多地采用了第一人稱“我”的倒敘策略,用追憶的方式講述了15年前的一段故事,是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即熱奈特所言的“例敘”[5]17。在追述性的故事講述中,必然會使敘事時序(文本順序)與故事時序發生一定程度上的錯位,形成“時間倒錯”的藝術格局。兩種故事的講述都發生在一定時間幅度范圍內,因此,一定程度上,時序的安排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故事講述的方式,對時序的研究,可以透入故事的內核,探究隱含作者的深層敘事目的和動機。此外,“研究敘事的時間順序,就是對照事件或時間段在敘述話語中的排列順序和這些事件或時間段在故事中的接續順序。”[5]54下面我們就在此基礎上,考察這部小說中的時間性因素在講述故事時的可能性作用。
在這部小說中,至少存在以下兩種不同的時間序列:文本故事中的人物“故事”序列和作為言說主體的“文本”顯示出來的序列。
漢娜的時間序列(人物“故事”時序):
(1)二戰時,漢娜曾經殺害300名猶太人→(2) 15歲那年,我邂逅了漢娜,與其相戀,但她卻突然消失→(3)大學時,我旁聽了對漢娜的審判→(4)離婚后,回到故鄉,開始給漢娜寄錄音磁帶→(5)漢娜死去→(6)我寫出我和漢娜的故事。
“文本”呈現的敘述時序:
A.我離婚,并與別的女人同居,但沒有結婚→B.15歲那年,我邂逅了漢娜,與其相戀,但她卻突然消失→C.大學時,我旁聽了對漢娜的審判→D.二戰時,漢娜曾經殺害300名猶太人→E.離婚后,回到故鄉,開始給漢娜寄錄音磁帶→F.漢娜死去→G.我寫出我和漢娜的故事。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出以下對應方式:
A(6)、B(2)、C(3)、D(1)、E(4)、F(5)、G(6)
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形成如此時間錯置格局,主要是由文本在總體上的倒敘方式所致。我們發現,全書共3個部分,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即以第一部分漢娜的突然離去和在審判席的出現為界限。而且,這兩個層面的敘事總是以一種互相交融的形式顯現:在敘事過去的事件時,總是預敘了現在,用的是“講述”;在述說現在的情形時,又不自由地追溯過去的點滴以及支離破碎的回憶。這種碎片狀的故事推進方式,顛覆了傳統文本的統一性,使得文本具有了強烈的召喚性,讓讀者充滿了了解故事來龍去脈的渴望。時間安排上的倒錯交疊,有限的時間展示了無限的空間。表面上,時間倒錯阻礙了讀者進行順利閱讀的可能。實際上,這種超越時空的敘事方式無限地擴大了心理時間的表現力,敘事的技巧,在這里也具有了現代性敘事的詩質,在錯置的時空格局中,不僅講述了故事本身,更突出了隱含在故事背后的深層隱喻意義,其中,最明顯的特征便是作為能指功能而存在的大量的宗教意象。
三、“宗教式莊重”:隱喻與深層結構
在G.庫爾茨看來,隱喻具有“文本結構作用”,它“顯示未來意義的可能性,連接環境與性格、空間和故事,構建支配性結構。”[6]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敘事的功能,在敘事文本中,與深層結構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是解讀深層結構的途徑和鑰匙。《朗讀者》作為一個“決非易消化食品”(福爾克爾·哈格語),它的那份在曹文軒看來所具有的“宗教式莊重”,在很大程度上與文本中一系列具有隱喻性質的宗教意象符號相關。
“朗讀”: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認同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只有通過有效的對話、交流才能達到相互理解,最終共享知識,彼此信任,主客體之間才能有平等對話的可能和基礎。在《朗讀者》這個關于救贖與被救贖、啟蒙與被啟蒙的故事里,以“朗讀者”身份出現的米夏,在文本中較多的扮演了啟蒙者和教導者的角色,這是關系到生與死的舉動,罪惡感將兩者結合在了一起。誠如作家所言,“通過漢娜和米夏,我想表現的是,第三帝國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參與了建設和維護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給世界和戰后一代留下印記,它又造成了什么樣的罪責感。”
從米夏一方來看,他主動的行為,最終在法庭得知漢娜的真實身份時,他選擇了沉默:沒有道出她文盲的真相及其與自己的關系,而且,他也始終處于迷茫和不知所措之中,“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于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么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余地了。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這是一種無奈的被動;從漢娜一方言,她熱衷于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強烈,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惡和恐懼也就越深層,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面。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追求尊嚴的道路,為此不惜撒謊,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漢娜最終自殺,也說明了被救贖的不可能實現。漢娜與米夏的關系既可隱喻為納粹罪行與無辜一代的代際關系,又可隱喻宗教意義上的上帝與凡人之間的關系,米夏無法救贖漢娜,漢娜也無法拯救集中營的犯人,他們如同萬能的上帝一樣,無力洗刷凡人的罪惡,都是一種失敗性的努力。從這個層面來理解,“朗讀”所涉及的愛、救贖、罪惡,與小說所要表達的反思罪過主題,深層次上具有了內在的相通性。
“水與教堂”:在小說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分,“水”的這一象征性意象場面多次出現,不僅成了他們做愛前必不可少的程序和儀式,更隱喻了漢娜企圖清除自身罪行的愿望:“我要洗澡,我想休息。”對米夏而言,沐浴已經是他的“成年儀式”,以至于洗澡已經成了他們幽會、在一起必不可少的節目,更是他作為第二代人必須承擔的責任。在小說的第三部分,當米夏與良久不見的漢娜相遇時,首先聞到的也是那種難以入鼻的汗臭體味,“水”在這里已經失去了滌去罪惡的功能,“水,是清洗,基督教里的洗禮象征人的罪可以‘洗’掉……文本此處的深層意義在于,情欲在人性的反復洗滌之后,可以上升為純潔的‘愛’,這是帶給人生命陽光的‘大愛’。”[7]既然罪惡無法擦拭,那么,漢娜悲劇性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必然性。
“教堂”,雖然在小說中出現的次數不是很多,但由于其與宗教在本質上的內在聯系,使它也同樣具有了象征和隱喻的含義。首次出現“教堂”這一場景,是米夏與漢娜在旅行途中,當漢娜隨著唱詩班的歌聲走進去靜靜地聆聽時,熱淚盈眶,是感動更是一種精神意義上的洗禮,盡管是不完全的。當我們在以后的情節中看到,教堂隨著熊熊烈火一起燃燒掉時,更感覺到了一種拯救的無望。
此外,“火”、“法庭”以及漢娜最終選擇的自殺,這些意象和舉動也都不同程度上地染上了宗教上含義,在此,不再一一贅述。因此,正是這些與深層結構有著關聯的意象和舉動,使得文本的宗教氣氛變得更加濃厚,染上了一份揮之不去的“莊重”。
四、結語
《朗讀者》以文學上的精打細磨,同時,引人入勝的形式表述了對德國歷史的發問,具有高度的精神上的獨立性以及穿透人性的理解力,融匯表現在富有張力敘述藝術之中。正是這一講述故事的“形式”和“強大的敘述力量”,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多重故事的鑲嵌并置,使得故事在不同敘述者的聲音中呈現出多樣的風貌;同時,追述策略的運用,讓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之間錯置,形成小說敘事的巨大張力。此外,文本中富有隱喻和象征功能的眾多意象和情節,在一定程度上又神話了小說懺悔主題,宗教性的莊重意味在講述中得以盡情地流露和顯現。正是這些結構小說的敘事策略和方式,使小說的敘事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猶如一把鑿向敘事藝術的利斧,給人帶來美的享受。
[1]本哈德.施林克.朗讀者[M].錢定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18.
[2]詹姆斯.費倫.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M].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4.
[3]戴衛.赫爾曼.新敘事學[M].馬海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40-41.
[4]馮亞琳.《生死朗讀》的敘事策略探析[J].外國文學評論:2002(1):110.
[5]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6]GerhardKurz:Metapher,Allegorie,Symbol,Ga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97,S.81f.
[7]廖峻瀾.愛與罪的自救——論《朗讀者》的隱喻結構[J].安徽文學:2008(2):38-39.
The Reader,an Ax Chisels to the Narrative from Multiple Sides——a study on novel narratives
ZHONG Milei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65,China)
The Reader,a work of the German writer Bernhard Schlink,has won unanimous praise with his elaborate and unique art of novel writing.Th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narration are parallel and multiple story narration,inverted time sequence,and metaphor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s under deep structure.With these strategies,he presented the art of narratives from multiple sides.
parallel stories;inverted time sequence;religious atmosphere
I106.4
A
1009-8445(2010)04-0025-04
(責任編輯:禤展圖)
2010-05-16
仲米磊(1982-),男,安徽蚌埠人,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2008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