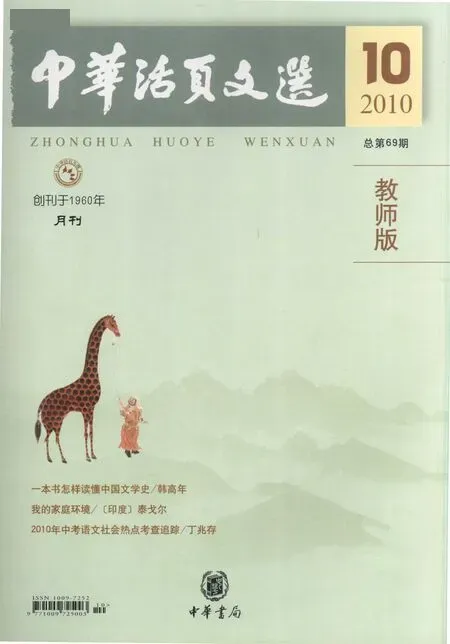我的家庭環(huán)境
〔印度〕泰戈爾
我年輕時代所享有的一個很大的便宜,就是彌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藝氣氛。我記得在我小時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見那座有客廳房子的獨立的建筑的涼臺欄桿上。每天晚上這幾間客廳的屋子都是燈火輝煌。華麗的馬車一直拉進門廊底下,賓客來往不絕。我說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樣的集會,我只從黑暗中凝望著一排排亮著的窗戶。隔斷的空間雖然不大,而在我的兒童世界和這些亮光之間的空隙,卻是很廣闊的。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剛拿到塔卡拉特那(孟加拉著名劇作家)先生寫的一個劇本,要在我們家里演出。他對于文學和美術(shù)的熱情是無限量的。他是那一個團體的中心人物。他們永遠有意識地努力從各方面引進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文藝復興。服裝上、文學上、音樂上、美術(shù)上、戲劇上突出的民族主義,在他心中和周圍覺醒了。他在各國歷史上,是個精研的學者,他已經(jīng)開始用孟加拉文寫了些歷史研究,但是沒有完成。他翻譯并且發(fā)表了梵文戲劇《優(yōu)哩婆濕》,還有許多有名頌歌都是他的手筆。在創(chuàng)作愛國詩歌上,他可以說是給我們做了領(lǐng)路人。這是在當“印度教徒協(xié)會”(印度的一個愛國組織)還是個年會組織的時候,在會里總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榮我感到羞愧》。
我還很小的時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見過他一次的人,也絕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莊嚴的相貌。他有一種不可抵抗的社會影響。他能夠把人們吸引到他的周圍而且永遠和他連結(jié)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強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絕不會有分裂的問題。他是我們國家特別類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個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們的家庭和村莊里出名。在任何一個有大的政治、社會或商業(yè)團體的國家里,這種人會自然地成為民族領(lǐng)袖。把許多人組織到一個團結(jié)的團體的力量,是依靠一種特殊的天才的。這種天才在我們國家里都白廢了,白廢而又可惜,我認為,就像是從天上摘下星星來當火柴用一樣。
我記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名畫家加甘南達拉和阿巴寧達拉的父親)。他也總使這家庭里充滿了他的人格。他的寬大仁慈的心,把親戚、朋友、客人和家屬都一視同仁地擁抱了起來。不論是在他寬闊的南邊涼臺上,泉邊的草地上,或是池邊的釣臺上,他總在主持著一個不招自來的集會,像一個“殷勤”的化身。他對于藝術(shù)和才智的廣泛的欣賞,使他永遠發(fā)出熱情的光輝。任何關(guān)于節(jié)慶、游戲、戲劇或是其他娛樂中的新穎想法,他總是一個踴躍爽快的贊助者,在他的幫助下,就會開花結(jié)果。
那時候我們年紀太小,不能參加那些活動,但是他們推動的熱鬧與活力的波浪,奔涌而來敲打著我們好奇的心門。我記得有一次我大哥寫的一出諷刺劇在堂兄的客廳里排演。從我們這邊,倚在涼臺的欄桿上,我們能聽到對面洞開的窗戶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聲雜在一起,我們有時也能看到阿克謝?瑪正達的絕妙的滑稽戲。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總在希望有一天能夠知道。
我記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贏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對我的特別好感。我除了得過一次品行優(yōu)良的獎賞以外,從來也沒得過獎。我們?nèi)齻€人中間,我侄子薩提亞是功課最好的一個。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獎金。我們到家的時候,我從馬車里跳出來把這重要消息告訴了正在園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著說:“薩提亞得獎了。”他微笑著把我拉到他膝前去。問:“你得了獎沒有?”我說:“沒有。不是我,是薩提亞得獎了。”我對薩提亞的優(yōu)良成績的由衷喜悅,似乎特別地感動了我的堂兄。他轉(zhuǎn)向他的朋友說著這件事,認為是很好的特色。我記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為我沒有從這一點上來體會我的感情。因為沒有得獎而得到了這個獎賞對我并沒有好處。給孩子禮物是無害的,但是他們不應(yīng)當?shù)玫綀蟪辍J购⒆雍π呤遣唤】档摹?/p>
午飯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們這邊房子里來處理房產(chǎn)事務(wù)。我們長輩的辦公室是一種俱樂部。在那里面談笑和處理事務(wù)自由地雜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長椅上靠著,我總找個機會挨到他面前去。
他常給我講印度歷史上的故事。我還記得當我聽克里夫(征服印度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建立了英國統(tǒng)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殺而死的時候,我是如何地驚訝。一方面,寫下了新的歷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卻隱藏著悲劇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樣的成功之內(nèi),怎會包含有那痛苦的失敗呢?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有時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著什么東西。在輕微的鼓勵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來了。我不必說明我的堂兄不是一個嚴厲的批評家;事實上,他所表示的意見,倒可以作為極好的宣傳。但是當我詩中的稚氣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時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親》的詩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韻,那個字是“車子”的意思,我必須把這車子拉進來,雖然連一條可讓車子通過的道路的影子都沒有——押韻的堅決要求,不肯聽受純理性的任何推托。古南德拉堂兄迎接這車子時狂笑的大風,把這輛車子吹回到那條不可能有車子走來的道路上,從此就沒有消息了。
我大哥那時已忙著寫他的杰作《夢游記》。他的坐墊放在南邊涼臺上,前面擺一張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來坐一會兒。他對于欣賞的廣大的能力,春風般地催助詩歌的萌芽。大哥寫了一會兒就把他寫的朗誦出來,他對于自己創(chuàng)造的幻象的洪亮笑聲,使涼臺都震動了起來。
大哥寫出來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詩的靈感是那樣地豐富,像過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蔭下鋪下了一層毯子,《夢游記》的撕棄的稿紙,也散擲得滿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這些稿紙都保留起來的話,今天真可以當做一籃花朵,來裝飾我們的孟加拉文學。
在門邊偷聽,在屋角偷看,我們曾充分地分享了這個詩筵,它是那樣豐盛,那樣富余。那時大哥正在才華英發(fā)的高峰;從他筆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詩的想象、韻律和詞句的洪流,以喜悅橫溢的勝利的歡歌,來充滿泛濫它的兩岸。我們能夠充分了解《夢游記》嗎?但我們在那時候是否必須完全了解才能欣賞它呢?我們也許得不到海洋深處的珍寶——即使我們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們在海岸邊狂歡戲水,在它們的沖擊之下,我們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歡樂地涌過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這一時期,就越體會到我們再也沒有了所謂的穆杰利斯(孟加拉語,意為不請自來的非正式集會)的東西了。在我們童年的時候,看到了這一個作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臨終光輝。那時候鄉(xiāng)鄰的感情是那樣地強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個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場合有所貢獻的人,就受過巨大的歡迎。現(xiàn)在人們只為著事務(wù)而互相訪問,或把它當做社會義務(wù),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來集會的。他們沒有時間,他們中間也沒有同樣的親密關(guān)系!我們從前看到的是什么樣的交往,紛紜的談話和斷續(xù)的笑聲,使得屋里和涼臺上顯得多么歡暢啊!我們祖先能成為團體和集會的中心,能創(chuàng)始和保持活潑有趣的閑談,這種才能現(xiàn)在都消失了。人們還是來來往往,但這些同一的房子和涼臺卻顯得空虛而荒涼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從器具到宴會,都是為多數(shù)人的享用而設(shè)計的。因此無論這些東西是多么豪華精致,也沒有一點傲慢的意味。這些附屬品,從那時以后在數(shù)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們已變得無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貴賤一致地感到賓至如歸的藝術(shù)。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襤褸的人,不能只憑著笑臉的魅力,而必須得到許可,才有使用或占據(jù)它們的權(quán)利。我們今天在蓋房子或設(shè)計家具時候,所想要親近的人們,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社會和它的寬泛的款待。我們的毛病是,我們拋棄了我們原有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在歐洲標準上面重建新東西的辦法,結(jié)果我們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歡了。我們?nèi)詾槭聞?wù)和政治的目的而聚會,但從不純?yōu)楸舜艘娒娑蹠恕N覀儾辉傧氤鰴C會,只為著熱愛我們的同胞,而把人們聚集起來。我想象不出還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惡的東西了,當我回憶到這些人從心底發(fā)出的朗朗笑聲,使我們減輕了俗務(wù)的負擔,他們仿佛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客人了。
(選自《圖本泰戈爾回憶錄》,冰心譯,湖南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