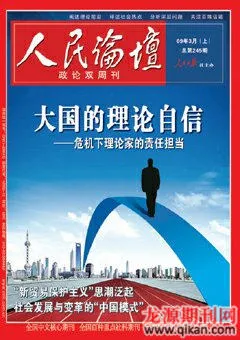農村基層治理再次走到變革關口

村民自治不應被斥為“民主的怪胎”
從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國農村的實施已有20多年。20多年來,有的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興高采烈,他們在此看到了中國民主的希望;有的則嗤之以鼻,認為此舉無足輕重,甚至斥之為一種“民主的怪胎”;還有的人則對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
的確,村民自治及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遠不是完美的,與法律的要求和人們的期望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各地村民自治的發展不平衡,實踐成效迥異;真正嚴格依法實行民主直選、全面落實村務公開以及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監督的村數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選舉流于形式,壓制、阻撓村民自由民主選舉的事件屢屢發生,各種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員會組織本身也名存實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對村民自治的實踐及前景表現出深深的懷疑、憂慮、悲觀甚至否定。
從實踐來看,經過20多年的實踐,我國農村普遍完成了從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轉換。作為農民群眾的自治組織,也是農村基層基本的組織與管理制度,村民委員會已經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起來。尤其值得關注和肯定的是,村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規范,村級民主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及基層政權組織的民主日益顯現出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實踐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紀末我國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體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制度特點:
其一是“城鄉分離”。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延續了這一體制。
其二是“村社一體”。從實踐來看,大多數村根據中央的規定,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實行“兩塊牌子,一班人馬,交叉任職”。
其三是“組織封閉”。基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及承包關系,農民歸屬于一定的“集體”,享有相應的權利。村委會組織及黨支部組織也是在這種集體范圍內組建起來的。
構建城鄉一體的社區制度,將是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變革
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經面臨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條件,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面臨新的變革。
首先,國家城鄉發展戰略從城鄉分離向城鄉一體轉變,要求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改革以來的村民自治的實施并沒有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組織與管理體制,事實上延續了這一體制。不過,改革以后,黨和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廢除了城鄉二元的糧食供應制度,改革戶籍管理方式,鼓勵農民進城及勞動力自由流動,推進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漸打破了長期城鄉隔絕的局面,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特別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的同時,強調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其實質就在于黨和國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構建城鄉一體的社區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
其次,不斷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農村服務從農民自我服務為主向社會公共服務為主轉變。隨著我國農村政策從“資源索取”到“反哺農村”的戰略轉變,傳統村民自治所承擔的公共服務及公益事業將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中央和地方也將更多地承擔村民自治的財政及運行成本,鄉村組織的工作內容和重點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的功能和作用也將進行重新定位。
第三,農村社會從靜止、封閉向開放和流動轉變,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轉變。過去,村民自治僅僅是擁有村集體產權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逐步放開了市場,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及鄉村內部的流動日益加快。農地流轉的不斷增多,不少人務工經商或移民城鎮放棄土地經營,也有不少人遠赴他鄉承包經營,而一個村莊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傳統封閉的村落和集體組織日趨瓦解。隨著農村社區體制的建設,我國的村民自治也將向居民自治轉變。
最后,農村社區與經濟組織逐漸分離,農村社區從生產和行政共同體向社會生活共同體轉變。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樣化,打破了傳統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或者說人們不再從屬于單一的集體經濟組織,社區也將不再是一種集體經濟組織或生產共同體,而是從事多種經營、多種職業的人們的生活聚居地或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經過了從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制”到村民自治時期的“村組制”兩次重大變革。如果說社隊制是適應計劃經濟體制及城鄉分離的需要而建立的話,村民自治及村組制就是在改革和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及打破城鄉分割的過程中建立的。隨著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及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的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再次走到歷史性變革的重要關口: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及城鄉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城鄉一體的社區制度,將是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重大變革。(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