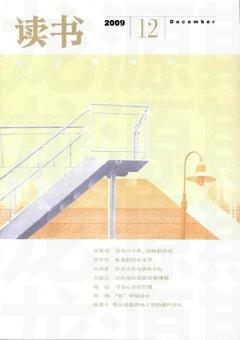憲政的超驗之維
韋 森
宗教信仰與人類社會種種制度的生成與變遷的關系,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還是個有待進一步開發的研究領域。因為,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在古代、近現代乃至當代的許多國家和社會中,宗教信仰以及與之相連的一些文化信念在種種政治、法律、經濟等社會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中均起著一些深層次的作用和影響。就此而論,若忽視人類社會制度形成與變遷中的宗教信仰與文化信念維度,就很難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和制度變遷過程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和較為確當的理解。
近代以來,在西歐和北美諸國漸次出現了一種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秩序,伴隨著這一社會體制的生成,十八世紀之后在西歐和北美相繼發生了工業革命和快速的經濟增長。近代以來在西歐和北美社會中由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所推動的近現代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又常常被人們簡稱為“西方世界的興起”。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一直是個經久不衰且到目前仍難說已有確切答案的重大問題。正是因為這一點,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乃至政治學家和科學史家等都曾付出過巨大的努力,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解釋與學說。近些年來,又有一些學者深入探討基督教信仰、宗教活動以及教會制度在歐洲中世紀乃至歐美近現代社會中對政治、法律、經濟乃至科技制度的形成與歷史變遷過程的作用與影響,產生了一些令人振奮且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從思想史上來看,從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文化原因,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在西方社會中一直并不缺乏。一些人類思想史上的大師級學者——如維爾納·桑巴特和馬克斯·韋伯——都曾做過這方面的努力。但是,就筆者管窺所及,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中所真正缺乏的,是對宗教(基督教信仰、活動和教會制度)在近現代歐洲和北美社會制度生成與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影響的較為深入的理論探討和史實的考察。對于桑巴特尤其是韋伯的觀點,國內學界多年來已經比較熟悉了。筆者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幾經研讀韋伯和桑巴特的觀點,并一度深受他們的影響。然而,筆者一直覺得,韋伯和桑巴特二人對宗教與歐美資本主義興起之間關系的論斷,雖各有其理,卻只是各講出了極其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的某一方面。
為什么這樣說?首先,從歷史上看,天主教尤其是基督新教信仰在歐洲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各國以及北美社會的制度形成與變遷中,以及表現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法治化的現代市場經濟秩序中均起到至深至遠的作用和影響,這一點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但問題是,這種作用和影響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斷言的那樣,現代資本主義是從清教徒的建立在他們的天職(the calling)信念基礎上的禁欲主義中衍生出來的,從桑巴特的《現代資本主義》中,我們會注意到,韋伯的這種對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關系的解說,早就為桑巴特本人所摒棄和拒斥過。桑巴特曾認為,清教教義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證”道:“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們完全反對所有發財致富的行為”;“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制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見桑巴特的《資本主義范型》一書第十九章,倫敦T. F. Unwin 一九三○年英文版)。如果我們相信桑巴特這些斷言是真的,即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并不如韋伯所斷言的那樣有某種直接的關聯——或者某種“選擇性的親和”(selective affinity),那么,難道桑巴特的近代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與猶太教教義以及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有關的斷言就能說明整個西歐和北美近代市場經濟興起的文化原因?顯然也不能,或至多也只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解釋。因為,無論在西歐中世紀和近代歷史上,還是在北美社會中,猶太人和猶太教只是各社會的一個極小組成部分。因而,如果把猶太教的理性主義、條文主義以及猶太人的經商精神視為整個西方世界近現代市場經濟興起的根本文化原因,顯然也有失偏頗。另外,在對資本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的認識和解說上,在韋伯與桑巴特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眾所周知,盡管桑巴特和韋伯均重視企業家精神在西歐和北美近代市場經濟興起中的重要作用,但韋伯認為,清教徒的節儉、禁欲主義以及作為上帝的管家而積累財富的天職觀念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文化原因,而桑巴特則反過來卻認為,是奢侈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到底孰是孰非?
現在看來,無論韋伯所言的是清教徒的節儉和禁欲主義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還是桑巴特所認為的奢侈是資本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甚至懷特海(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所提出的近代科學革命之所以在歐美社會中發生的文化原因在于基督教信仰的斷言,都是這些思想大家們根據自己當時所處環境和自己的觀察和體悟所做的一些具有個性化的理論推斷,從世界近現代歷史來看,是在有著基督新教信仰背景的西歐和北美社會中漸次產生了法治化的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同時發生了由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快速經濟起飛和長期的社會發展,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在有著天主教信仰傳統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們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中,卻在西歐和北美經濟起飛的同時而相對落后了,因而在人類近現代歷史上就出現了加州學派的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所言的“大分流”現象。這一世界歷史事實無疑向世人昭示著這樣一種研究線索:在基督新教信仰與近現代法治化的市場經濟興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些內在聯系,且這種內在聯系可能不盡是某種“選擇性的親和”那樣的簡單關系,而似乎有著內在的、復雜的和深層次的根本性關聯。這種關聯到底是什么?讀過伯爾曼(Harold J. Berman)的《法律與革命》第一卷,我們已知道,在十一世紀末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對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所發動的授權之爭(Investiture Contest)以及由此在歐洲中世紀歷史上所引發的全面政教沖突,曾引發了歐洲中世紀各種法律體系(諸如教會法、城市法、王室法、商事法、封建法和莊園法)的蓬勃發展,從而為西歐的近現代社會中確保市場交易中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的產生拉開了序幕。最近通過讀一些早期蘇格蘭基督教憲政主義的歷史文獻,我們又發現,正是由于加爾文、蘇格蘭偉大的清教徒宗教改革家和思想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約1505—1572)和薩繆爾·拉瑟福德(Samuel Rutherford,1600?—1661)等其他清教徒思想家以及英國國教(安立甘宗)的最重要思想家和創始人之一的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3—1600)等的憲政民主和法律思想的影響,君主永遠在上帝的律法和人民的契約雙重約束之下,以及政府權力有限這些近現代憲政民主政治的理念才在法國、荷蘭、蘇格蘭、英格蘭等西歐諸國廣泛傳播并深入人心,繼而才在近代西歐各國和北美社會的憲政民主政制的基本框架下生成并演變出了確保近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近現代法律制度。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今天方能理解西方法治化市場經濟生成和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文化原因。現在看來,新教改革中萌生的基督教憲政思想,是西歐和北美近現代法律制度生成和現代市場經濟興起的最根本的“文化基因”,而這一最根本的文化基因,卻是韋伯、桑巴特乃至懷特海這些人類思想史上的巨擘先前所沒有注意到的。
為什么說加爾文主義的宗教信仰對歐洲和北美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憲政民主政制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研究十六到十八世紀歐洲政制史的一位當代學者凱利(Douglas F. Kelly)在其《自由的崛起》一書中曾給出了很清晰到位的歷史解釋。據凱利研究,在影響法國、荷蘭、蘇格蘭乃至英國的新教改革運動的加爾文派的教義中,一個重要的理念是,“政府必須受憲法約束,以顯示它服從于上帝的道和初代教會的信仰”(加爾文一五四一年九月十六日致Farel的信中的話)。在這一加爾文主義宗教理念的影響下,十六世紀后半期,基督教的胡格諾派(Hugunots)曾在法國有過較大范圍的發展和思想傳播。在胡格諾派的思想家中,弗朗索瓦·霍特曼(Francois Hotman)曾于一五七三年發表了題為《論法蘭西憲政》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霍特曼重申了法蘭西古老憲政傳統的一個重要原則:“國王終其一生只是一名政府官員,如果他不能盡守職責,他就什么也不是,而人民有權廢黜他。”盡管胡格諾派在十六世紀法國的宗教戰爭中失敗了,但是其宗教信仰與政治主張中的憲政思想,卻影響了后來的法國乃至荷蘭、蘇格蘭、英格蘭以及北美殖民地的憲政主義思潮。在十六世紀的蘇格蘭,與加爾文主義的“上帝是所有權力存在的合法性源頭”的理念在精神上相一致,偉大的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約1505—1572)基于上帝圣約的觀念,更明確提出了上帝同人民的圣約直接賦予了人民反抗一切世俗非正義暴政權力的偉大思想。這一思想曾極大地影響了后來在十七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發生的英國清教徒革命,乃至對后來英國的“光榮革命”和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也發生了至深至遠的影響。對此,凱利明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光榮革命也就是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革命的最后完成,是圣約運動(國民誓約派)所持的那些信念最終贏得了勝利。”凱利還認為,在北美殖民地的加爾文主義的清教教會“在圣約觀念下的憲政經驗,對于北美的社會共同體、殖民政府乃至以后的聯邦政府的憲章性盟約(這里作者是指一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教徒在一艘船上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引者注)的發展都有著直接的影響。長老會的治理模式則以它自己的方式對美國的政體形成有其獨特的貢獻,如代議制、聯邦制、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同時對法官的違憲審查制度也有著深刻的影響”。除諾克斯外,在十七世紀,蘇格蘭另一位神學家、思想和政治家薩繆爾·拉瑟福德的基督教憲政思想,也對英國光榮革命前整個蘇格蘭和英格蘭社會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譬如,在一六四四年,作為威斯敏斯特會議的蘇格蘭委員,拉瑟福德出版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法律為王》(Lex, Rex)(這部著作將由山東大學謝文郁教授翻譯為中文,并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人類歷史上這部極其重要的憲政民主政治理論的經典文獻中,拉瑟福德曾明確提出,英國國王也要服從上帝的律法,并對人民這一權力的源頭負責:“人民賦予國王的權力是有限的,而人民保留的權力則是無限的,并以此約束和限制著國王的權力。因此,與人民的權力相比,國王的權力更小。”正是有了加爾文、諾克斯、拉瑟福德以及胡克等這些基督新教思想家的影響,“主權在民”、政府的“有限權力”、“法律為王”以及君主永遠在上帝的律法和人民的契約雙重約束之下的思想才在法國、荷蘭、蘇格蘭、英格蘭等西歐諸國得以廣泛傳播和深入人心。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今天才能全面理解英國光榮革命發生及其勝利的思想根源。正如凱利所言,英國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的“勝利顯然應該歸功于蘇格蘭的諾克斯、梅爾維爾(Andrew Melville)和拉瑟福德的思想,甚至也應該歸功于國民誓約派(Convenanters)的成員們。因為這些人宣稱國王與人民一樣,也在上帝的圣約之下,他也必須受到上帝在圣約中的律法(包括其祝福與詛咒)的約束。如果國王濫用權力,也應該被廢”。
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說憲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在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憲政民主政制為近現代市場經濟的良序運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而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聯邦國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和美國——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正是在憲政民主政制的基礎性框架上“生長”起來或言是“相伴生成”的(因為,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實際上——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抽象規則”約束住了統治者和政府對民眾財物和財富的任意“攫掠之手”),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憲政民主政制與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憲政民主政制的基本構成和核心理念是“稅權法定”)。對此,諾思(Douglass C. North)在他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九九○)以及在他與瓦利斯(John J. Wallis)和溫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的二○○九年的新書《暴力與社會秩序》(中譯本將由格致出版社出版)中都有很多精彩的論述。實際上,哈耶克在他的《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以及后來的《致命的自負》中也都有不少論述,只不過是在哈耶克的話語中,西方世界興起的真正原因在于在英美憲政民主政制下的自由(liberty)確立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普通法“內在規則”的形成。現在看來,無論是哈耶克,還是諾思,他們的共同問題是均沒有進一步深入探討英美以及荷蘭、法國和德國的現代憲政民主政制的歷史起源,結果導致哈耶克只是把西方世界近代的制度變遷過程(請注意哈耶克非常不愿意使用“institution”這個詞,而寧肯使用“social order”概念)歸結為自發社會秩序的生成和演進,而諾思等人則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程式而更為簡單地把這一過程臆斷為統治者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計算的理性設計與建構。對于西方憲政民主政制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在歐洲近代社會中漸進形成的三大歷史淵源(包括早期猶太教—基督教信仰,日耳曼人的立約精神和早期日耳曼公社中的初民民主政治實踐,以及古希臘城邦的貴族民主政治和羅馬法的傳統遺產),哈耶克和諾思等經濟學思想大師均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現在看來,無論是哈耶克,還是諾思,無論是桑巴特,還是韋伯,他們幾乎都忽視了基督教憲政主義的理念在英美乃至歐洲其他國家中至深至遠的影響;甚至像英國政治思想史的大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在其《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這樣的巨著中,以及像弗里德里希(Karl J. Friedrich)這樣的西方當代重量級的政治學說史家在其《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這樣的專門著作中似乎也沒有給予完全充分的強調和更深入的史料發掘。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法律與革命》第二卷中,像伯爾曼這樣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法制史學家竟然也幾乎完全忽略了英美憲政民主政制和法律制度的清教徒思想的歷史淵源這一最重要的超驗維度。
最后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相信從對基督教憲政主義思想源流溯源和理論梳理的視角探尋基督教信仰在西歐和北美社會近現代憲政民主政制生成中的作用,將會展示出與桑巴特、韋伯乃至哈耶克和諾思的理論視界均有所不同的一幅新的“歷史圖景”,且我們相信這幅“歷史圖景”可能會比這些先前學者的理論描述和解釋更接近歷史演變的真相,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伯爾曼、凱利等有著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思想史學者的工作,并非拒斥或言完全否定桑巴特、韋伯乃至哈耶克和諾思的先前理論解說。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興起是個極其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在其中,桑巴特所說的“企業家精神”——或照韋伯的說法“資本主義精神”——無疑曾起過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沒有桑巴特的那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征服與營利”的企業家精神,沒有韋伯的“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沒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業家永無止境的“創新精神”,就不可能有近現代西方世界的興起,甚至不可能有在近現代憲政民主政治下人們追求自由的訴求和建構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的內在沖動。從一方面來看,近現代憲政民主政制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為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揮和張揚提供了一種外在的制度保障和社會條件;而近現代憲政民主政制以及在此基礎上架構生長出來的保護交易中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又可以是人們追求自由、幸福以及個人利益和財富——尤其是“企業家”和“創業者”發展事業的沖動——的一種社會演進后果。顯然,這里最終繞不開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精神”或言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源自何處這一老問題:是源自韋伯的清教徒禁欲主義的節儉精神和為上帝看管和積累財富的天職觀念,還是來自桑巴特的貴族的“奢侈”以及猶太教的經濟理性主義觀念、條文主義與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抑或來自馬克思的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狂熱地追求價值增殖”的無限沖動?抑或如凱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的企業家的某種不斷擴張自己企業的“動物精神”?還是最后回到亞當·斯密那里,認為這種近現代企業家精神是由人所秉有自利追求與人有喜好交易的天性所轉化生成的?那么,人的這些天生秉性與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根據上述的理論梳理,這里所能得出的一些初步結論只能是:宗教信仰——具體來說基督教信仰——確實在西歐和北美近代早期的制度生成與社會變遷中以及在近現代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的興起中起到一些深層次的且根本性的作用,但這些作用也許并不如韋伯所斷言的那樣是來自清教徒的節儉、禁欲和天職觀念,也不是像桑巴特所斷言的那樣是貴族的奢侈和猶太教教義及猶太人的商業精神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現在看來,至多我們只能說韋伯、桑巴特以及懷特海只是看到了西方世界興起這一復雜世界歷史現象的文化原因的某一個面相,而且他們所看到的可能還不是一些基本的或言根本性的面相。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Influence of Calvin on Five Governments from the 16 th through 18 th Centries, By Douglas F. Kelly. 《自由的崛起:十六——十八世紀,加爾文主義和五個政府的形成》,[美]道格拉斯·F.凱利著,王怡、李玉臻譯,江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七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