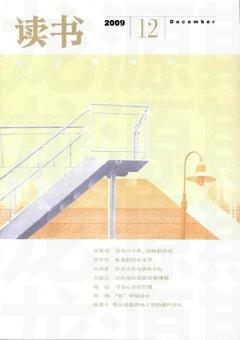說引喻失義
王道還
《讀書》二○○八年十一期145頁,王敦從嚴復《天演論》上卷《導言十六·進微》截了一段,做起文章來,犯了論文之大忌。
案,那段文字出自赫胥黎原著導言第十三節(XIII)。赫胥黎討論的是,人世的歷史變化并不等同于生物的自然變化,與人工培育生物的過程也不同。赫胥黎以英國從伊麗莎白女王(一五五八年登基)到維多利亞女王(一八三七年登基)這近三百年歷史為例,指出英國的政教、軍事、工業各方面都有長足進步,并不是英國國民的遺傳組成發生了變化的結果。社會中有些人作奸犯科,不全是因為他們的遺傳素質太差。而且英國并沒有采取嚴格的優生措施,使作奸犯科的人都無法生育。
赫胥黎認為,同樣的“德行”,即使是來自遺傳秉賦,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會成就不同的“聲名”。赫胥黎說:“精力與勇氣,讓軍人崛起、升官;冷靜與膽識,讓金融家賺大錢。要是他們處于不利的情境中,也許會因而走上絞架,或者陷身囹圄,也未可知。”
這就是嚴復那句所謂“英諺”的原意:糞在田則為肥,在衣則為不潔。然則不潔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
案,這句英諺,赫胥黎的原文非常簡潔:
dirt is riches in the wrong place;
直譯是“財富失所則成糞土”。赫胥黎本人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一本書里,描述過“溪流中的泥巴,其實只是從屋頂與街道鋪石上沖洗下的污泥”。赫胥黎這篇文章發表之后一年,一八九五年夏,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葛瑞(John C. Gray, 1839—1915)在一本書的序言中引用了同樣的諺語,不過他是這么說的:Dirt is only matter out of place; and what is a blot on the escutcheon of the Common Law may be a jewel in the crown of the Social Republic.這句話更符合嚴復的“譯文”。特別是out of place剛好對應于“失其所”,以及“在衣則為不潔”。
理解了赫胥黎使用這一英諺的目的之后,嚴復將這一節命名為“進微”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他告訴讀者,這一段的主旨是:指出英國人在最近三百年并未“進化”。嚴復本節最后以“嗚呼,可謂奇觀也已”做結,是在強調“歐美”近幾百年“所日進者,乃在政教學術工商兵戰之間”,而不是國民體、智、德的先天秉賦“進化”了。
嚴復唯恐讀者對這一點難以把握,立即以案語強調此意,認為中國應立即努力變法圖強:不可謂古之變率極漸,后之變率歲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歐洲政教學術農工商戰數者而論,合前數千年之變,殆不如晚近之數百年,至最后數十年,其變彌厲。
案,從這一則案語,可見嚴復的生物演化論造詣實在有限。赫胥黎在原文中一再強調生物演化與人文發展是不同的過程,人文進程不受達爾文的天擇原理支配。理由很簡單:人文進程不會影響人的遺傳組成。這就是德國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動物學講座教授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 的“生殖質”(the germ-plasma)理論,對當時仍十分流行的“后天形質(性狀)遺傳說”(即“拉馬克機制”)是個致命打擊。
話說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赫胥黎在牛津大學講演《演化與倫理》,講詞事前已印行發售,嚴復據之譯成《天演論》下卷。當時魏斯曼的理論已譯成英文,在英國引起了激烈辯論,與達爾文齊名的演化學者華萊士(贊成)與斯賓塞(反對)都卷入了。赫胥黎并沒有參戰,但是他在講詞中以“注一”表明了立場。嚴復以“案語”將那個注譯了出來(《天演論下卷·論一·能實》后之《復案》),然而不但他本人不解其中竅要,學界至今莫名其妙,可說是另一個引喻失義的例子(詳見《新史學》第三期,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