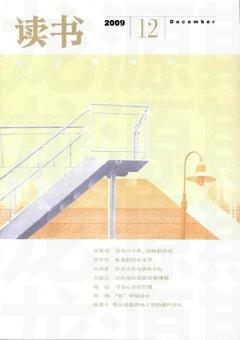西北邊疆輿地之學(xué)的現(xiàn)代巡禮
陳亞平
晚清重臣左宗棠面對同光之際的西北動(dòng)亂局勢曾經(jīng)說過:“中國盛世,無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而國勢盛衰不僅影響了中央政權(quán)對西北的政治控制,也決定著西北史地學(xué)的發(fā)展興替。歷數(shù)漢唐以來的西北史地學(xué)成就,那些影響重大的西北學(xué)術(shù)成果多是在國勢強(qiáng)盛的基礎(chǔ)上取得的。郭麗萍的專著《絕域與絕學(xué)——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xué)研究》從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著手,探討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xué)興盛與康乾盛世國家對西北控制的聯(lián)系,對乾嘉以降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和考據(jù)學(xué)傳統(tǒng)對西北史地學(xué)的影響條分縷析,認(rèn)為“清代中葉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關(guān)于經(jīng)世之思考與成熟考據(jù)學(xué)雙重作用的產(chǎn)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應(yīng)包括兩個(gè)方面:經(jīng)世致用的貫徹、考據(jù)學(xué)的發(fā)揚(yáng)”。她把歷代學(xué)人的家世、仕學(xué)經(jīng)歷、朋僚交游、學(xué)術(shù)傳承等,放到具體的時(shí)代背景下細(xì)致描述,揭發(fā)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線索,向我們展示了清代西北史地學(xué)豐厚飽滿的學(xué)術(shù)內(nèi)涵。本書以乾嘉以降的清代西北史地學(xué)為中心展開,但行文不拘泥于斷代時(shí)限,上溯自清代康熙、雍正西北用兵時(shí)期的征人行紀(jì),下探到晚清伊犁交涉遇到的歷史地理學(xué)和地圖學(xué)問題,使這部著作成為對清代西北史地學(xué)成就的總攬性作品。
閱讀這部書,可以看到清代西北史地學(xué)學(xué)科形成發(fā)展以至沉寂的曲折理路,在歷史比較中發(fā)現(xiàn)清人對以往相關(guān)學(xué)問的大幅度超越,窺見這一學(xué)術(shù)舊邦深藏的珍寶重器,還可以在清代學(xué)人“烹羊炊餅”、“劇談西北”的流風(fēng)遺韻中領(lǐng)略當(dāng)年的“絕學(xué)”風(fēng)采。
傳統(tǒng)的西北史地學(xué)研究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方向是在清代才正式形成的,歷經(jīng)幾代學(xué)人的努力,最終形成了在資料收集、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獨(dú)具特色的學(xué)術(shù)成就,使清代的西域?qū)W成就達(dá)到了中國傳統(tǒng)西北史地研究的高峰。客觀地說,清代學(xué)人所達(dá)到的高度,我們至今也還難以企及。
朝廷的開疆治理與文化宣示
清代西北學(xué)研究的最初印象是由康熙時(shí)期那些跟隨征戰(zhàn)大軍走出邊塞、走進(jìn)大漠的文人學(xué)士們留下的征人行紀(jì)、日記、雜記描繪出來的。
在康熙、乾隆兩朝征戰(zhàn)西北的同時(shí),清代開始了對西北大規(guī)模的輿地勘測和輿圖繪制工作。“通過測量獲取各地的經(jīng)度、緯度、時(shí)刻、日景等數(shù)據(jù)”,欽天監(jiān)官員“掌握了西域九十多個(gè)測量點(diǎn)的北極高度、東西偏度、冬至夏至的晝夜長短及節(jié)氣早晚等數(shù)據(jù)”。確定了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西域的區(qū)域范圍及其在王朝版圖中的位置,“新疆的輪廓較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了”(24頁)。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這批資料轉(zhuǎn)給了方略館,經(jīng)過軍機(jī)大臣傅恒等人再次編輯,形成《西域圖志》的雛形。
《西域圖志》于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修訂完成,該書確定了西域的疆域四至和鄰接部族,以圖文相間的形式記載了西域的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四大區(qū)域,說明各城鎮(zhèn)的地理、民風(fēng)與歷史沿革,用地圖表明各地之間的相對空間位置,以實(shí)測數(shù)據(jù)為各個(gè)地點(diǎn)做了準(zhǔn)確的地理定位。清廷將實(shí)測的西北各地節(jié)氣數(shù)據(jù)編入《時(shí)憲書》,“體現(xiàn)著朝廷對社會生活秩序的劃一管理”。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完成的新本《大清一統(tǒng)志》以“西域新疆統(tǒng)部”為篇名,增加了舊本《一統(tǒng)志》闕如的西域部分。這一時(shí)期官修的關(guān)于西域地區(qū)的大型圖書還有《平定準(zhǔn)格爾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西域同文志》等。
《西域圖志》和《西域同文志》成為當(dāng)時(shí)官方認(rèn)定的兩部規(guī)范化的大型西域工具書。《西域同文志》是一部關(guān)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區(qū)的地名、山名、水名與人名的辭典,書中除有各詞條的解釋之外,還有滿、漢、蒙古、西番、托忒、回等各種文字的譯音對音。該書編成以后,“西北官書編纂一般是地理位置以《欽定西域圖志》為準(zhǔn),所用地名一體遵照《欽定西域同文志》”(34頁)。“在封建大一統(tǒng)的時(shí)代,入時(shí)憲、頒正朔意味著時(shí)間秩序的劃一;入輿圖、宣一統(tǒng)昭示著空間秩序的統(tǒng)一;方志史料匯入《一統(tǒng)志》反映著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對于西北的自然地理認(rèn)識由此落實(shí)到政治地域的認(rèn)同。”(27頁)上述官書的編纂是清王朝鞏固帝國政府在西域統(tǒng)治的龐大的政治參考書,也是乾隆皇帝昭顯“中外一統(tǒng)之盛”的標(biāo)志性工程,當(dāng)然也是清朝西域?qū)W研究得以發(fā)展擴(kuò)張的基礎(chǔ)性工程,是道光以后的西域?qū)W發(fā)展成為“顯學(xué)”的必不可少的一類史料。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康乾以來的盛世局面,如果沒有康乾時(shí)代對西域的開拓進(jìn)取,人們就很難走出邊關(guān)、走進(jìn)大漠,親身觀察西域的遼闊自然,切實(shí)感受西域的豐厚文化,對西域的認(rèn)識就絕沒有超越往時(shí)的基本條件。清代西域?qū)W的輝煌既建立在國家對西域的政治控制和社會管理的基礎(chǔ)上,也建立在清朝官方編輯和私人撰述的大量西域圖志史料基礎(chǔ)上。
西域地方志的編纂
盛世修史,明時(shí)修志。西域重新納入中央帝國版圖控制之后,編撰西域地區(qū)的地方志以為地方官員治理參考的工作跟著提上了議事日程。成書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的《新疆回部志》是現(xiàn)存最早的記載新疆地方情形的書籍。乾隆后期輾轉(zhuǎn)新疆任職的官員永保是清代最早熱衷于修志的新疆地方官員。在他歷任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等地的時(shí)候,每到一地,他都致力于修志活動(dòng)。先后創(chuàng)修了《塔爾巴哈臺事宜》、《喀什葛爾事宜》、《烏魯木齊事宜》、《總統(tǒng)伊犁事宜》等地方志著作。這類“事宜”著作,重視官署衙門的檔案文書和撰寫者耳聞目見的現(xiàn)實(shí)材料,兼及地理形勢、生產(chǎn)情況,偏重行政管理和政事沿革,重點(diǎn)在于“服務(wù)于地方治理”,“反映著地方官理政的實(shí)際需求”(54頁)。嘉慶七年(一八○二)和瑛編撰的《回疆通志》在不同版本中亦被稱為《回疆事宜》,比較全面地展現(xiàn)了南疆維吾爾聚居十城之地的風(fēng)貌,細(xì)致入微地記述了維吾爾族的宗教信仰與習(xí)俗服飾(56頁)。這些書籍在資治參政的同時(shí)也在積累著“絕域孤學(xué)”的知識基礎(chǔ)。
嘉慶七年松筠赴任伊犁將軍,為新疆地區(qū)的最高軍政長官。四年后他正式上奏提出修纂《伊犁總志》的構(gòu)想。后在謫發(fā)新疆的舉人汪廷楷和進(jìn)士出身的祁韻士大力參與,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完成了《西陲總統(tǒng)事略》的編撰。事略包括以伊犁為中心的疆域山川、風(fēng)俗物產(chǎn)、城池衙署、壇廟祠宇、屯田水利、錢稅牧養(yǎng)、職官題名,甚至滿營孀婦等內(nèi)容(62頁)。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松筠再任新疆后,延攬徐松入幕,在《西陲總統(tǒng)事略》基礎(chǔ)上補(bǔ)充編撰完成了《伊犁總統(tǒng)事略》。
嘉慶道光年間的張格爾叛亂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了八年時(shí)間,這場“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帑銀千萬余兩”的戰(zhàn)爭迫使道光皇帝為首的清廷急欲了解西北情形,祁韻士的著作《西陲要略》與《西域水道記》成為他入值南書房的兒子祁藻的重要參考書。徐松主持編撰的《伊犁總統(tǒng)事略》更加受到皇帝的嘉許和贊賞,道光帝御賜書名《新疆識略》,并且親撰序文,下旨交武英殿刊印。道光帝對徐松大加褒寵,召見“奏對西陲情形”,“賞內(nèi)閣中書”。徐松聲譽(yù)日高的同時(shí),西北史地學(xué)研究也進(jìn)入了高潮,成為一時(shí)顯學(xué)。
空前的西域?qū)W盛況
以新疆為中心的西北地區(qū)是漢唐故土,也是中國傳統(tǒng)史地學(xué)早就關(guān)注的地區(qū)。從研究西域的學(xué)者們列出的參考書目上我們不難見到《山海經(jīng)》、《史記》、前后《漢書》、《水經(jīng)注》、《大唐西域記》等歷史久遠(yuǎn)的古典名著。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gè)時(shí)代像嘉道時(shí)期那樣,有那么多頂尖的學(xué)者都將他們的目光投注到這片新疆故土,也沒有哪個(gè)時(shí)期的西域研究能夠像嘉道時(shí)期的西域?qū)W那樣成批地創(chuàng)作出足以超越前人啟發(fā)來者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
祁韻士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中進(jìn)士,他的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被梁啟超視為“中國學(xué)者對于蒙古事情為系統(tǒng)的研究”的開端(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他在西戍新疆的歲月里完成了《西陲總統(tǒng)事略》、《西域釋地》、《西陲要略》等著作,使他“成為內(nèi)地西北著作與新疆地方史志的溝通者,成為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推進(jìn)者”(75頁)。徐松是嘉慶十年(一八○五)進(jìn)士,七年后被遣新疆,“成為迄今所知對于新疆地區(qū)進(jìn)行全面考察的第一人”(86頁)。除了上述《新疆識略》之外,徐松在謫居新疆期間還初步形成了《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bǔ)注》、《西域水道記》三部專論新疆的著作。他們是乾嘉學(xué)者中少有的經(jīng)過身履目驗(yàn)西域情勢的西域?qū)W專家。
道光初年的張格爾事件不僅促使清人為戰(zhàn)爭需要而了解西域,也為戰(zhàn)后制定治理策略的需要而研究西域提供了契機(jī)。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魏源撰寫了他的第一篇西北專論《答人問西北邊域書》,批駁“捐西守東”說。龔自珍在熟悉西域史地的學(xué)者程同文影響下早就開始關(guān)注皇朝輿地和“四裔之學(xué)”,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就定稿了《西域置行省議》,他還循《西域圖志》的思路構(gòu)思撰寫《蒙古圖志》,意在了解清代邊疆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shí),并試圖以自己的研究解釋和影響帝國的邊疆政策。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在殿試《對策》中表達(dá)了對西北邊防的認(rèn)識,并在朝考中撰寫了著名的《御試安邊綏遠(yuǎn)疏》,集中表達(dá)了他對治理西北邊疆的見解,提出移民實(shí)邊,“以邊安邊”、“足兵足食”、“常則不仰餉于內(nèi)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的主張(127—129頁)。
沈是在一批江南考據(jù)和輿地學(xué)者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西域?qū)W研究者。他以《新疆私議》一舉成名而進(jìn)入北京的西域?qū)W學(xué)人圈,先后為姚元之校《國史地理志》與《道光九域志》,與徐松研究《長春真人西游記》并撰寫《西游記金山以東釋》,使新疆金山以東的山川地理“遐荒萬里”猶如目驗(yàn);沈還參與校補(bǔ)徐松的《西域水道記》,并留下大量與徐松相關(guān)聯(lián)的輿地和西域?qū)W著述。另一學(xué)者張穆在與京城師友交游中逐漸走進(jìn)了西北史地研究,得到俞正燮、徐松等前輩學(xué)者的指點(diǎn),受到祁藻、程恩澤等人的提攜,成為校勘祁韻士西北史地著作的重要學(xué)者,他還校訂了《藩部要略》和多部友朋著作,逐漸積累資料,最終完成的《蒙古游牧記》是“對清代蒙古地理研究的一次總結(jié)”,“標(biāo)志著當(dāng)時(shí)運(yùn)用中文資料研究中國北部邊疆地理所能達(dá)到的高度”(248—251頁)。
張穆的《蒙古游牧記》和魏源的《元史新編》、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是嘉道時(shí)期西域?qū)W研究留下的三部代表作。《蒙古游牧記》撰寫于清代西域?qū)W研究的最興盛時(shí)期,不僅遼、金、元諸史以及歷代輿地學(xué)著作是其基本史料,清代前期問世的西北著述和私家行紀(jì)、考據(jù)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等等,張穆都能“信手拈來”,因此,“《蒙古游牧記》也是對清代西北文獻(xiàn)的一次大檢閱”(241頁)。
魏源撰寫《元史新編》直接淵源于《海國圖志》的資料收集(251頁)。《元史新編》是一部“基本由舊式史料支撐下的元史著作,作者拿元朝比較處于盛世尾聲的清王朝,通過纂修元史,于褒貶得失之間發(fā)揮其史鑒功能。他的《擬進(jìn)呈元史新編序》結(jié)尾說,“前事者,后事之師。元起于塞外有中原,遠(yuǎn)非遼金之比,其始終得失,固有百代之殷鑒也哉”。鮮明地表達(dá)了他的寫作意圖。《元史新編》“也是對清中葉西北史地研究的一次總結(jié)”(260頁)。
何秋濤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成進(jìn)士,在和徐松、張穆、何紹基等人的交游中相互觀摩,成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殿軍。何秋濤從校訂《元圣武親征錄》積累了大量西北文獻(xiàn)、熟悉考訂方法,在文獻(xiàn)校訂中形成了對中國北部邊疆及其以外地區(qū)的認(rèn)識。他還特別注重積累吸收域外史料,不僅林則徐、魏源、徐繼、姚瑩等人收集整理的世界地理文獻(xiàn)被他統(tǒng)統(tǒng)收集,一些當(dāng)時(shí)新刊的外國史地著作也成為他關(guān)注的新材料。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他的八十卷《北徼匯編》全書定稿。該書描繪了一條由庫頁島向西、轉(zhuǎn)西北、達(dá)伊犁連綿不斷、拱繞內(nèi)地的邊徼地帶,他的關(guān)注點(diǎn)不僅僅在中原與邊疆的關(guān)系,還有邊疆之外的俄羅斯,“關(guān)注的是清朝與俄羅斯的關(guān)系,是俄國的外向擴(kuò)張力”。他“完整記述了東海諸部、索倫諸部、喀爾喀、準(zhǔn)噶爾、蒙古、烏梁海三部到哈薩克各部歸附清廷的過程”——這也是清朝北部疆域的形成史;他在明確的邊境線概念下,敘述中俄分界諸山、俄羅斯境內(nèi)諸山,附綴中國境內(nèi)作為俄國眾山之祖的阿爾泰山;他以三種類別描繪了中國境內(nèi)諸水、由中國流入俄羅斯境再入北海二河、源委均在俄境內(nèi)諸水;他還介紹了俄羅斯的疆域、城垣、教門、方物等。該書對俄羅斯的記載,全面、完整、豐富都超越過了前人,“是嘉道以來人們認(rèn)識研究俄羅斯的結(jié)果”。《北徼匯編》八十卷本問世之時(shí),正是俄國在東北占土掠地愈演愈烈之時(shí),因此,咸豐十年(一八六○),何秋濤的這部著作被咸豐皇帝御賜書名《朔方備乘》,何秋濤本人也以“通達(dá)時(shí)務(wù)、曉暢戎機(jī)”,由主事擢升為員外郎(265—274頁)。
嘉道時(shí)期的西域?qū)W研究實(shí)乃康乾盛世疆土開發(fā)與統(tǒng)治鞏固的厚賜,也是乾嘉學(xué)風(fēng)與中國傳統(tǒng)輿地研究相結(jié)合產(chǎn)生的碩果。
只今絕學(xué)真成絕?
歷數(shù)清代西域?qū)W研究的成就,人們不能不思考一個(gè)問題:清代西域?qū)W是不是真的成了一門后無來者的“絕學(xué)”呢?
嘉道西域?qū)W研究具有濃厚的乾嘉色彩:“是前人關(guān)于經(jīng)世之思考與成熟考據(jù)學(xué)雙重作用的產(chǎn)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應(yīng)包括兩個(gè)方面:經(jīng)世致用的貫徹、考據(jù)學(xué)的發(fā)揚(yáng)。”(302頁)這個(gè)概括暴露出嘉道時(shí)期的西域?qū)W的致命缺陷:即主要以考據(jù)學(xué)的方法去貫徹經(jīng)世致用的理想。這之間必然產(chǎn)生隔閡與困惑,沈、魏源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這樣的困惑。沈在“技”與“學(xué)”的背離和割裂中“藉考證以自給”,無奈地耗費(fèi)著人生,“所從事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沈距離用世之學(xué)卻越來越遠(yuǎn)”,最后郁郁而終。“一種學(xué)問,尚不能救己,更難以救世。剛過不惑之年的沈帶著滿腹的遺憾與悲哀離開人世時(shí),中英沖突的序幕剛剛拉開。”(194—208頁)
這樣,把一個(gè)人的命運(yùn)放到大的時(shí)代的運(yùn)勢中加以觀照,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個(gè)人的命運(yùn)不僅與一種學(xué)問的命運(yùn)興衰相照映,而且還與更加宏闊的文化的命運(yùn)、民族的命運(yùn)相印證。在這種映照中呈現(xiàn)出來的感傷和惋惜即使作者沒有說出來,我們也能夠從本書的字里行間讀出來。“清代嘉、道、咸時(shí)期是一個(gè)轉(zhuǎn)折期,清王朝由興盛走向衰落,中國社會開始了由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zhuǎn)變。轉(zhuǎn)變時(shí)期需要應(yīng)合時(shí)代的學(xué)術(shù),但學(xué)術(shù)往往深深根植于傳統(tǒng),其轉(zhuǎn)變往往遲滯緩慢。”嘉慶年間,頌揚(yáng)大一統(tǒng)盛況是那時(shí)學(xué)術(shù)的常見主題。道光朝邊疆危機(jī)已現(xiàn),西北研究倒出現(xiàn)了由今向古的興趣轉(zhuǎn)移。“直到咸豐朝,俄國人已經(jīng)在東北割占土地了,何秋濤還不得不周旋于浩渺的文獻(xiàn)記載。這些史實(shí)中,可見這一學(xué)問與時(shí)代的不合拍之處,可見那群人追趕時(shí)代步伐的力不從心。”(304頁)近代西方地理學(xué)是一種以近代物理學(xué)、近代數(shù)學(xué)等學(xué)科為基礎(chǔ),是一個(gè)重實(shí)測、求精確的科學(xué)體系。源于西方的近代地理學(xué)和地圖學(xué)的引進(jìn),無異于宣布了“傳統(tǒng)學(xué)以致用的命題已經(jīng)終結(jié)”(305頁)。
用近代地理學(xué)標(biāo)準(zhǔn)衡量,十九世紀(jì)祁韻士、徐松對西域的實(shí)地考察,只是一個(gè)記錄耳聞目睹的過程,根本無法與西方地理學(xué)創(chuàng)始人那種“名副其實(shí)的科學(xué)考察”相提并論。中國學(xué)者著作中標(biāo)榜的對西域熟悉如“掌上螺紋”的知識沒有能夠給同光時(shí)期的外交談判提供有益的幫助;中國傳統(tǒng)輿地研究所呈現(xiàn)的那種描繪大略、長于直觀而失之精確的地圖繪制,僅僅能夠給人一種大概的方位示意。光緒六年(一八八○)中俄伊犁交涉和后來的帕米爾爭端,曾紀(jì)澤、許景澄沒有合適可用的中國地圖支持自己的主張,無疑會給原本困難重重的外交談判增添更多的障礙與風(fēng)險(xiǎn)。談判中“中方的主要依據(jù)是西方的地圖,中方交涉者缺少來自本國地圖的必要支持”。嘉道西域?qū)W奉為圭臬的經(jīng)世致用原則,貫于考古而疏于知今的治學(xué)路數(shù),經(jīng)史之學(xué)講求治法和提倡人心風(fēng)俗的學(xué)術(shù)理路,最終導(dǎo)致了“以道咸之學(xué),致同光之用”時(shí)的捉襟見肘。這些基于具體事例的評價(jià)都是在拿西方近代地理學(xué)、地圖學(xué)為參照,對照出來的中國西域?qū)W的不足。這不能不讓人對清代學(xué)人的努力感到惋惜。
這種對照評價(jià)能夠給清代西域?qū)W一個(gè)合理的定位嗎?
一百多年來,西方在各個(gè)方面展現(xiàn)給中國人的優(yōu)勢面相,很容易讓中國學(xué)人回顧歷史的時(shí)候產(chǎn)生自慚形穢的感覺。人們常常拿西方的長處比照出自己的短處,在輿地學(xué)方面我們往往拿西方更加專業(yè)化的地理學(xué)、地圖學(xué)特別是自然地理方面的精準(zhǔn)比較出中國輿地學(xué)的含混籠統(tǒng),卻不太在意中國傳統(tǒng)輿地學(xué)最具優(yōu)長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綜合性和人文性。只要我們承認(rèn)清代西域?qū)W是一個(gè)包容了歷史、地理、經(jīng)濟(jì)、民俗、宗教、民族乃至語言學(xué)等許多內(nèi)容的綜合的整體,而且這個(gè)整體從來沒有一個(gè)時(shí)代能夠像清代那樣完整地展現(xiàn)過,也從來沒有一個(gè)學(xué)派或者一種科學(xué)能夠像清代學(xué)人那樣留下如此豐厚的學(xué)術(shù)積累,那么,任何以西域?yàn)檠芯繉ο蟮默F(xiàn)代學(xué)科都不能不以清代西域?qū)W作為它未來成長的根基。清代的西域研究是綜合的研究,它表現(xiàn)在康熙以來那些西出陽關(guān),走過大漠的征人旅客的行紀(jì)、雜記和筆記中,也表現(xiàn)在乾嘉以來的學(xué)者們孜孜以求的研究方法上,還表現(xiàn)在嘉道以來整體亮相的學(xué)者們留下的無量著作里。只是時(shí)勢因緣的轉(zhuǎn)移導(dǎo)致的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遮蔽了它本來具有的光芒,這在價(jià)值和影響上并不能遮蓋它綻放出來的斑斕色彩。
如果西域?qū)W能夠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xué)問發(fā)展的話,他不會僅僅是一門區(qū)域史地學(xué),而應(yīng)該是一種融會自然、歷史與人文等多個(gè)方面的綜合性學(xué)科,奠定這一學(xué)問基礎(chǔ)的無疑應(yīng)該是清代的西域研究者。
遭遇時(shí)運(yùn)轉(zhuǎn)移,清代西域?qū)W至今還是一個(gè)未被人充分認(rèn)識的領(lǐng)域。即使在中國讀書人心目中,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西域著作也遠(yuǎn)遠(yuǎn)比清代的西域研究更具吸引力。如果認(rèn)真閱讀斯坦因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西域研究是那樣毫無保留地展示他對中國文獻(xiàn)的依賴。自《史記》和兩《漢書》以來一切有關(guān)西域的記載、魏晉以來西行進(jìn)香僧人的游記,唐宋時(shí)代關(guān)于西域的一切著作,都是他最為關(guān)心、屢屢羅列的資料,他使用較多的最近資料是元代馬可·波羅的行紀(jì),至于清人的學(xué)術(shù)成果則很少涉及。斯坦因以盜寶為中心的考古行紀(jì)也是一個(gè)綜合性極強(qiáng)的學(xué)術(shù)匯集,其中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地理學(xué)、人類學(xué)、文化學(xué)、宗教學(xué)、語言學(xué)、藝術(shù)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內(nèi)容,為了特定的考古目的,他沒有用單獨(dú)某一門西方近代科學(xué)作為方法準(zhǔn)則指導(dǎo)他的西域研究。斯坦因的著作“代表了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以前在這一領(lǐng)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孟凡人,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漢譯本前言)。就是這樣的著作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有可能,斯坦因每到一處都要拿漢文文獻(xiàn)記載來印證他的實(shí)地觀察,像祁韻士、徐松他們身履目驗(yàn),以今證古的做法一樣,他無數(shù)次地驚嘆漢文歷史文獻(xiàn)留下的準(zhǔn)確記載。他求助于漢文文獻(xiàn)的時(shí)間要遠(yuǎn)遠(yuǎn)多于求助于平板儀的時(shí)間。漢文文獻(xiàn)指引著他的西域行程,引導(dǎo)他到達(dá)輝煌的頂點(diǎn)。
斯坦因未能認(rèn)識到清代學(xué)人的西域?qū)W貢獻(xiàn)。以西方近代學(xué)術(shù)為標(biāo)準(zhǔn)的研究理路又遮蔽了今人對清代西域?qū)W的深入了解,學(xué)術(shù)上的今古中西隔閡沒有為清代西域?qū)W的現(xiàn)代發(fā)展提供機(jī)會,這些都制約了現(xiàn)代西域?qū)W的發(fā)展。我想,西域研究如果不愿意成為一門“絕學(xué)”的話,當(dāng)時(shí)刻記取王國維那段“正告天下”的聲明:“學(xué)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xué)之徒,即學(xué)焉,而未嘗知學(xué)者也。”(引王國維《國學(xué)叢刊序》,305頁)如能真正破除此類隔閡,以前人豐厚的學(xué)術(shù)積累為基礎(chǔ),加上現(xiàn)代科學(xué)理念和研究范式的推進(jìn),推陳出新,則中國西域?qū)W的舊邦新造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九年八月四日
(《絕域與絕學(xué)——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xué)研究》,郭麗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七年十二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