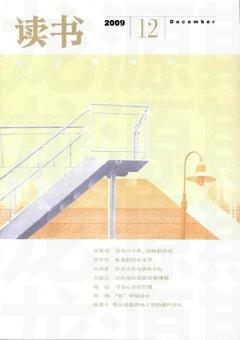反思六十年,迎接新挑戰
吳敬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已經六十年了。在紀念國慶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不妨套用列寧的話說,“慶祝偉大革命的紀念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在過去六十年中,現代中國的建設走過一條迂回曲折的道路,經歷過無數艱辛、動蕩、搖擺與反復,既有山重水復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轉機。這是一段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能為我們指明解決任務的方向。
回想六十年前,天安門的禮炮聲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曾經災禍縱橫的中國醫治好戰爭的創傷,國民經濟面貌為之一新。這使億萬民眾從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國》的歌聲:“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然而,勝利的同時,也存在問題。恢復國民經濟的偉大勝利,使人們滋長了虛夸冒進和高估自己的能力的思想。在匆忙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蘇聯式的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進一步激發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形成了毛澤東所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個多世紀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先后采取了不同的辦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區分,可以將中國半個多世紀改革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改革的重點,是中央政府向下屬各級政府放權讓利。
一九五七年,中國從一九五八年初開始了被定義為“體制下放”的“體制改革”。改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計劃管理權的下放;(二)企業管轄權的下放;(三)物資分配權的下放;(四)財政權和稅收權的下放;(五)勞動管理權的下放。
在保持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的總框架不變的條件下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所形成的分權型命令經濟體制和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社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構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的制度基礎。在這種體制支持下,“三年超英、十年超美”,各級政府充分運用自己支配資源的權力,無償調撥農民的財產勞力資源,大上基本建設項目,來完成“鋼鐵生產一年翻一番”之類異想天開的高指標。結果很快爆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由于經濟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只是一大堆為了邀功請賞而制造的虛夸數字。后來的事實證明,當時號稱已經完成的鋼鐵、糧食等生產指標,完全是虛假的。
一九五八年末,這種完全脫離實際、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極后果終于顯現,生產下降,大批工商企業出現虧損,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經濟陷入嚴重困難。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導致的第二次“共產風”,使經濟和社會狀況進一步惡化。一九五九年全國共生產糧食一千七百億公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實際產量兩千億公斤減少了三百億公斤;一九六○年糧食產量降到一千四百三十五億公斤,比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七億公斤還低,全國普遍發生饑荒。由于封鎖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鎮地區廣泛出現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病,農村地區則造成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
一九六○年秋季,中共中央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恢復了由陳云任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采取堅決措施來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
經過幾個月的調整,經濟逐漸穩定下來,并在一九六四年大體上得到恢復。
不過,在人們慶幸經濟秩序恢復的同時,卻發現集中計劃經濟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來。于是又醞釀再次進行改革。
但是,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由于存在社會主義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這樣的意識形態障礙,市場取向的改革很難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政府向地方下放計劃權力,幾乎成了唯一可能的改革選擇。因此,此后仍然多次進行過類似于一九五八年的行政性分權改革,例如,一九七○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為口號的大規模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就是一九五八年“體制下放”的重演。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的多次“體制下放”,無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亂和以隨后重新集中而告終。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下,形成了“放—亂—收—死”的怪圈。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轉機。由于把整個社會禁錮和使上億人遭到迫害,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全面專政”制度徹底絕望,全國上下一致認為舊路線和舊體制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須通過改革開放變革救亡圖存的共識。中國改革也進入它的第二個階段。
啟動改革的第一項行動,是解除思想禁錮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以此為開端,全國掀起了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啟蒙運動。“思想解放”意味著原來認為天經地義的“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之類的理論是可以懷疑的,原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命令經濟和“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包括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制度是可以改變的。這次運動打破了數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縛,激發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開動腦筋去尋找挽救危亡、求得發展的出路。他們認真總結自己的教訓,學習他國的經驗,提出了各種各樣變革的設想。
至于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的想法:
第一種是以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在“撥亂反正”中,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黨政領導人認同孫冶方的經濟思想,認為應當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提高企業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另一種意見的思考范圍更加寬廣,認為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一種完全不同于蘇聯模式的新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例如,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宿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長期擔任中央政府經濟領導工作的薛暮橋,在一九八○年初夏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受第一種思想的影響,四川省率先開始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接著把這一改革推廣到全國主要的國有企業。在開始的幾個月內,“擴權”顯著提高了試點企業職工增產增收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做法的消極方面也很快就表現出來。加之當時對發展工業要求過高過急,增加投資的壓力很大,造成了總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經濟秩序陷于混亂,使國企改革不得不停下來,整個國民經濟也進入新一輪調整。
當國有企業的擴大自主權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經掌握實際領導權力的鄧小平改變了改革的重點,從城市的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轉變,是對農村包產到戶由禁止到允許的轉變。以家庭承包制度為基礎的農村改革,迅速推動了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當這種“存量不動、增量改革”的戰略在農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國黨政領導將這種經驗推廣到其他部門,逐步放開對私人創業活動的限制。加上在這之前已經開始的對外資開放國內市場,也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使非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得以自下而上地發展起來。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的十二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
實行增量改革戰略,在大體維持國有經濟現有體制的條件下,容許私有經濟發展和引入部分市場機制,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命令經濟與市場經濟、“調撥價格”與市場價格雙軌并存的狀態。
“雙軌制”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正像一些學者所說,它給民間創業活動一定的空間,使各種類型的民營企業得以成長;另一方面,如果這種被定義為“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續下去甚至得到加強,就會造成廣泛的尋租環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而如果不能及時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鏟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助長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后果。
這樣,“雙軌體制”就把兩條可能的進一步發展道路擺在中國的面前:一條是堅持改革,建設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強化尋租基礎,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由于存在這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這些年來就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規范的市場經濟逐步建立促成了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雖然出現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為,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勢。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權貴既得利益的阻礙,或者遭到了他們的扭曲,官員的權力擴張和干預加強,就會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造成腐敗活動加劇,貧富差別進一步擴大,大眾不滿的情緒滋生的態勢。
為了克服雙重體制膠著對峙造成的種種弊端,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制定了價、稅、財、金、貿五個方面配套改革方案,并準備從一九八七年初開始實施。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為進行“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出臺了一系列措施。
可惜這兩項改革都沒有能夠進行下去。接著發生的一九八八年的經濟風波和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使改革受到挫折。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后掀起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新高潮,使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整體推進的新階段。
首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商品市場的價格全面放開,市場活躍,“官倒”商品尋租的空間大幅度地被壓縮,腐敗被抑制。大眾對改革的推進十分滿意。
從一九九四年初開始,根據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財稅、銀行、外匯管理等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重要進展。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新的決定,也為國有企業改革確定了正確的方向。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在產權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十五大”明確宣布,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代表大會要求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調整和完善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調整包括三項主要內容:(一)縮小國有經濟的范圍,國有資本要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二)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多種公有制實現形式,發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三)明確宣布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在往后幾年中,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一些重大的進展。
第一,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已從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變為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業為主。絕大多數國有二級企業已經改組為國家相對或絕對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類企業中,二十一世紀初實現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海外整體上市,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微觀基礎。這些公司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框架。
第二,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明顯優化,從國有經濟一家獨大的結構轉變為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除少數壟斷行業外,民營經濟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業方面,民營企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體。首先在沿海地區,然后在許多其他省份,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
由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形成和市場化改革的進展,中國經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迅速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已經被世界公認為保持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國雖然在二十世紀末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場經濟的若干重要架構,例如規范的金融市場,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治體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說,距離原來確定的經濟改革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有鑒于此,二○○三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
不過,這一決定的執行不是沒有阻力和障礙的。
首先,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一些行業的行政壟斷還有所強化。在某些國企改革中,還出現了改革遭到扭曲,“掌勺者私占大鍋飯”的權貴私有化的現象。所有這些,都使民怨沸騰。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有些論者提出,在這些行業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不但不應當降低,還應當提高。二○○四年以后,社會上開始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開倒車現象。
第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從二○○三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的現象。在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判斷時,主流意見卻把問題的性質確定為“局部過熱”,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聯合發文,采用審批等行政手段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的投資、生產活動進行控制。從那時起,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
第三,政治改革滯后。鄧小平在一九八○年發動全國農村承包制改革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著名的“八一八”講話,啟動了政治改革。一九八六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于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過,這兩次改革都沒有能夠進行下去。鄧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領導人在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展十分緩慢。例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十三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體系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還有的人利用這種情勢,主動地運用不受約束的權力發財致富。于是,就出現了尋租、造租的“新動力”。
尋租活動基礎的擴大使腐敗活動日益猖獗,“傍大款”和“傍大官”的“官商勾結”,“買官賣官”等丑惡現象也隨之蔓延開來。根據一九八八年以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額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四萬億至五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中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對這種情勢的原因,社會上存在不同的判斷,也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另一部分人把腐敗蔓延、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他們認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話語,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帶來貧富兩極分化和勞動者生活水平下降。主流媒體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原因和應對措施的闡述加強了這種思想傾向。于是,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恢復國有企業的統治地位以及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狀況。
在這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的情況下,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大眾對于丑惡現象的正當不滿,玩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口號迷惑大眾,把反對和打擊的目標從運用公共權力牟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團轉移到在市場化改革中成長起來的一般“富人”,包括同樣身受貴族壓榨的中產階級身上。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等都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動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公有財產被私有化了的財產,全盤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在政治上,則要重舉“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行幾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狀所做的這些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
如果說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所做的“診斷”屬于“誤診”,他們開出的“處方”,即回到“全面專政”時代,就更是南轅北轍了。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適得其反,更加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嗎?
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的歲月中續寫輝煌,將取決于我們能否根據過去六十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正確應對新一輪的挑戰。
最近,青年記者馬國川采訪了十位出生在建國前后、有深厚學術修養的經濟學家,結集為《共和國一代訪談錄》一書出版。訪談圍繞著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成長展開,從一代人成長的軌跡中,不但可以看到六十年間國家走過的艱難歷程,可以看到三十年間改革走過的不平凡道路,而且可以為今后的改革尋找到仍然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共和國一代訪談錄》,馬國川著,華夏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