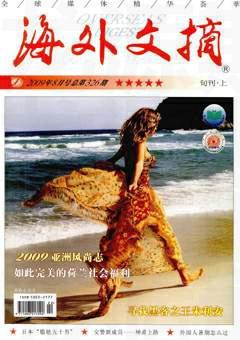加拿大博彩業進退維谷
杰伊·特伊爾特
兩個相對的示例
2007年春季的一個星期五下午,61歲患有帕金森癥的工程師約瑟夫·特賴耶斯撐著他的助行器進入多倫多市西北郊伍德賓賽馬場的門廳,在賭場的老虎機中輸掉了1000多加元。到那天為止,這個老賭徒在過去10年中,總共在賭博中輸掉了30萬加元,其中包括他與妻子離婚時賣掉一套房子中分得的20萬加元,以及他想方設法借到的3萬加元。此外,他還將應該支付護理院房租的殘障費支票也輸給了賭場,結果被院方趕了出來。
當約瑟夫·特賴耶斯一拐一瘸地從賭場走出來時,在這座城市的另一處,24歲的查克·特伊特爾突然因右腿麻木摔倒。他被緊急送入多倫多市圣邁克爾醫院,在那里做了MRI(磁共振成像)檢查。MRI機在他的脊椎處發現一個腫瘤。兩個星期后,通過外科手術,這腫瘤被切除了,查克·特伊特爾恢復了健康。
意想不到吧?政府掌控的賭場使約瑟夫·特賴耶斯破了產;但同時政府又用賭場的收益辦了醫院,買了機器,為查克·特伊特爾開了刀,使他過上了健康的生活。一個人的災難卻成了另一個人的救星。
賭場收益的去向與來源
自從政府主管發行的彩票于1969年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后,政府掌管的賭場也于上世紀80年代在加拿大問世。賭博對社會顯而易見的毒害和它帶來的經濟收益產生了一個道德上的進退維谷。加拿大政府創辦合法賭博場所的理由是:無論我們將賭博合法化或禁止,人們都會參與賭博,因此不如讓我們好好掌控它;賭博業以前是一項未利用的籌資渠道,它獲得的收益可直接用于有益的事業。據說,從收支比例分析,加拿大人花在賭博上的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所以,將賭博業合法化是否值得?從實踐或道德上來分析,查克·特伊特爾和約瑟夫·特賴耶斯,孰輕孰重?
無可否認,政府掌控的賭博業的確財源滾滾。1982年,阿拉伯塔省的賭博業總收益是0.44億加元。2008年,該省的彩票基金上交給省政府的款項為15億加元,其中2.605億用于保健、4.754億用于文化和社區建設、1.291億用于教育。2008年,安大略省彩票和賭博業公司總收益為62億加元,其中19億上交給了政府(其余的作為彩票獎金、運作開支和其他費用)。而在政府收取的19億加元中,15億用于公立醫院經營,包括MRI機的運營成本——每臺機器一年都得花費數十萬加元。
這些數字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們并不是這一問題的全部。
羅伯特·威廉姆斯是賴斯伯利基大學健康科學教授和阿爾伯塔賭博業研究所的負責人。在過去5年中,他一直在進行賭博業對社會影響的研究,他對于那些聲稱賭博合法化所獲得的經濟利益高于社會成本的說法產生了疑問。
“在美國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以及摩納哥、澳門這類地方,這種說法可能站得住腳”,威廉姆斯說,“賭博業在那些地方能產生真實的財富效應,因為那些錢不是來自當地,而是來自旅游者。這些地方幾乎不承擔社會成本。旅游者將所有的錢交給了賭場,然后帶著各種懊悔和沮喪返回故鄉。”可是在加拿大,他指出,除了在安大略省與美國交界的那些賭場以及一些土著人辦的賭場,賭場的收益主要來自當地人的腰包,沒有新財富創造出來。收益只不過是一種再分配而已。
“一些省份從賭博業的收益中積累了大量資金”,威廉姆斯說,“但證據顯示,這些收益的大部分間接來自加拿大的其他地區。在那些地區,人們把原本用于娛樂的錢,如打保齡球、上酒吧等等,都輸在了賭場,使該地區喪失了不少商業收益,甚至工作崗位。這種錢的轉移并非有益于社會,緊隨其后的是后患無窮的社會問題。”
賭博的危害性
那么,這些危害是什么呢?威廉姆斯認為,它們的形式多種多樣:金融問題和破產,精神健康問題和自殺,法律問題以及婚姻問題。據這位教授估計,約80萬加拿大人(占總人口3.2%)有賭博嗜好,至少有10%的加拿大人會受到賭博業負面效應的影響。
當然,有關政府部門也試圖幫助那些賭博成癮的人,即所謂的問題賭博者。阿爾伯塔省設立了“阿爾伯塔賭博研究所”,以研究賭博衍生出的各種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安大略省政府從賭場和賽馬場安放的老虎機收入總額中每年拿出2%(約3500萬加元),用于“賭博業問題策略”項目的研究。
賭博的危害是會傳導的。問題賭博者的子女也很有可能染上賭癮。雖然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在某些城市,已發生過一些子女偷父母的錢去老虎機上賭博的事情。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合法的賭博業還導致了犯罪率的增加,如挪用公款和詐騙。問題賭博者為了還賭債,在有機可乘時就有可能以此類方法鋌而走險,拿了錢再去賭,試圖贏回失去的錢。“擺在面前的局勢是”,威廉姆斯指出,“政府從犯罪的后果中受益 —— 一名賭徒從公司或某個機構搞到錢,將它在政府擁有的賭場中輸掉。”
綜上所述,許多對于賭博業持負面看法的加拿大公眾認為:作為具有公共機構特征的政府部門,不應該誘導市民進入賭場這個拿金錢博弈的世界。購買或運作MRI機的資金來源應該通過別的渠道想辦法。某些人的好運不能以另一些人的不幸作為交換。
[編譯自加拿大《讀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