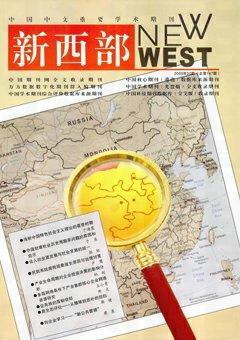卡夫卡小說《變形記》的反諷結構
【摘 要】 反諷產生于認同感的缺失和對自我意識的審視,是無限絕對的否定。卡夫卡在小說《變形記》中通過主人公格里高爾變為大甲蟲之后產生的認同感危機,建構了多層次的反諷,探究了現代人的意識和認同危機,對社會體系提出了質疑,同時徹底地否定了他所身處的社會價值體系。
【關鍵詞】 卡夫卡;反諷;認同;現代意識;否定
一、反諷結構
反諷產生于認同感發生危機。隨著對人的意識、人的主體性的更多關注,以認同感缺位為基礎的反諷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現代作品中,成為西方現代作品的一種最常見的創作手法和精神態度。反諷在卡夫卡小說中,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或者藝術手法,同時也是卡夫卡在謀篇布局時的基本思路,它構筑了卡夫卡許多小說的基本框架和結構。以小說《變形記》為例,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在作品中的遭遇悲慘而荒謬,而在全家人不乏善意的幫助下,他的處境卻每況愈下,最終死去。而他的死訊竟然成為家里人的福音。主人公和家人都被莫名的力量所牽引,一切良好的初衷最終都走向其反面。這正是因為卡夫卡在小說《變形記》中刻意構造了一個多層的反諷結構來探究現代人的意識和身份認同感,并通過這些反諷結構,質疑了現存的社會機制,徹底地否定了現實世界的各種關系。
薩姆沙在一個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大甲蟲,他的房間沒有發生變化,他周圍的人也沒有發生變化。他的人的意識與他的甲殼蟲的軀殼頃刻之間產生了認同危機,他的人類的意識拒絕認同他的蟲子身軀,這一認同危機貫穿全文。人的意識和蟲的身軀之間,也就是靈與肉之間的沖突對立就此展開,小說的反諷結構就建筑在全篇的這一基本對立之上。卡夫卡在行文中一方面細致入微地再現了格里高爾的意識活動:他的工作焦慮、對家人的依戀、不安、恐懼等等,他的思維完全是在一個人的正常健康的大腦中展開的;另一方面卡夫卡又不吝筆墨詳盡地描寫了大甲蟲的生活起居的種種細節;格里高爾如何克服種種困難,起床開門;如何適應蟲子的新身軀、飲食習性、爬行習慣等等。卡夫卡極力渲染人的意識與蟲的軀體這兩個極端,這在讀者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而這巨大的反差以及靈與肉的不一致正是反諷的基礎。
二、認同感的危機
卡夫卡在敘述中采用的是人物視角,也就是內視角,即卡夫卡以主人公格里高爾的視角來講述這個變形的故事。卡夫卡在小說開端用冷靜的語調來敘述一個巨大的不幸和災難的發生,冷靜的語調和若無其事的口吻正好符合格里高爾想將大事化了的鴕鳥心態:把眼睛閉上,不去想它,不去看它,變成蟲子巨大的災難仿佛就不存在了。格里高爾的意識中并沒有出現他的軀體變為甲蟲這一事實,如果格里高爾的軀體和意識趨于一致,成為一只沒有任何意識活動的大甲蟲,那么意識與軀體之間的張力將消失,反諷將不復存在。正因為他的人類的意識完全拒絕承認他的軀體變為甲蟲這一事實,因為他想一如既往,什么事也沒發生一般地照常去工作,他的動物軀體和人的靈魂之間的反差才顯得那樣刺眼。從他的心理活動讀者可以探究他變成大甲蟲的原因,在工作中他已經越來越遠離自我,他的異化早就開始了。當他讓自己的意識隨意流淌時,他想逃避工作,但這種逃避發生在他的潛意識中。而在他的意識層面,他還是個任勞任怨盡職盡責的職員,還想著趕下一班火車去上班。由此可見,卡夫卡在格里高爾的意識與軀體、意識和潛意識之間建構了反諷。
在開門之前,他已經做好了兩種準備:“如果他們嚇一跳,那么格里高爾可沒有什么責任;如果他們平靜地完全接受這一切,那他也沒有什么理由去激動,他如果抓緊些還可以在八點鐘趕到火車站。”[1](P64)也就是說,在開門之前,格里高爾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對他的新形象視若無睹,他還可以同往常一樣若無其事地去工作。門打開后,大家確信無疑見到了一只大甲蟲,而不是公司雇員、家里的兒子和兄長。在格里高爾是否是人這一點上,社會環境給予了負面的回答。這無疑使他在異化的路上更進了一步。格里高爾的自我認識和他的社會環境對他的認識截然相反,也同樣構成一個客觀反諷。周圍的人確信,他是動物,大家都對這只大甲蟲心懷恐懼。家人越是關心他,卻越是與他的意愿相反,越將他推入蟲類;而格里高爾不放過任何一個表明自己是人的機會,但他每次為此進行的抗爭都愈加被周圍的環境誤解,他越是想成為人,也越是反而更加速地跌入蟲類。這兩種對立的反諷構成了一個悲哀而毫無出路的怪圈,故事的發展不斷地以自身來否定自身,這是一個典型的反諷境地。“如果格里高爾再回到我們中間”[1](P76)雖然表達了家人的愿望,但也正是家人的作用使他無法也不可能再變回人類,而他無法變成人,他就將永遠不再有用,這意味著他將成為全家人的累贅。
三、反諷的否定性
格里高爾蛻變為甲蟲的過程昭顯著起決定作用的社會體系的強大作用,它能夠使人變為蟲。握在父親手里的那些秘而不宣的錢表明,迫使格里高爾去不停工作的并不是這個家庭經濟狀況的真正窘迫,而是格里高爾所屬的小市民階層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的戰戰兢兢的恐懼心理和悲觀心態。這種心態迫使社會成員被卷入那個社會體制中去,盡力地去符合社會體系的道德標準,以成為它的合格成員。這正是使格里高爾無可挽回地走上異化道路的原因。
格里高爾的父親經營破產,他把父親的債務完全背在自己的肩上,在變為大甲蟲后,他聽到家人為家庭前景擔憂。他羞愧得面紅耳赤[3](P76)。奧地利研究卡夫卡的專家索克爾認為:“債就是格里高爾本人。家庭的債體現在他那嚇人的形象上,從家庭轉到了他身上。而他的變形使家庭從債中解放出來。直至他的消失,債才完全還清。”[2](P110—111)格里高爾由于在工作中耗盡了身心之力,變成了一只大甲蟲。這不是他的自愿選擇的結果,而是工作和生存壓力使然。格里高爾的意識是社會體系培養出來的一個合格成員的意識,而這個體系卻將它的合格成員異化成大甲蟲,也就是說,對那個社會體系的積極認同者卻最終因為他的認同被那個社會的道德體系所拋棄、所否定,這是否定的過程,也正是反諷的過程。正是通過格里高爾的變形過程,卡夫卡展現了這個社會倫理和道德標準的殘酷性。而正是在這種道德的要求下,人出現了異化,而異化的人馬上被這個社會所拋棄。這是卡夫卡的反諷,這樣的反諷深刻地質疑了社會體系。
四、結束語
克爾凱郭爾從反諷主體與現實關系的角度分析反諷者的特殊位置,將反諷定義為“無限絕對的否定性”[3](P218)。小說《變形記》正是克爾凱郭爾反諷定義的最佳詮釋,卡夫卡從一個奇異的角度描述了這個失去了有效性的社會歷史現實以及敏感的現代人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的分裂的自我和認同危機。格里高爾正因為愛他的家人,玩命工作,克勤克儉地養活他們,卻因此越來越遠離自我,最后異化成了大甲蟲,喪失了人的身份,喪失了工作能力,無法繼續養家。正是他的愛使他最終被家人拋棄,在他活著不再對家人有任何用處時,他通過生命的終結來最后一次對他的家庭有用,這也是反諷的極致。
【參考文獻】
[1] Franz Kafka.Verwandlung[A].n:Sfimtliche Erzfihlungen[M].Frankfurt am Main.1970.
[2] Walter H.Soke1.Franz Kafka.Tragik und Ironie[M].Frankfurt,1976.
[3] S.Kierkegaard.fiber den Begrif der lronie.Mit stfindiger Rflcksicht auf Sokrates[M].MOnchen und Berlin,1929.
【作者簡介】
劉秀玲,西安文理學院外語系,職稱: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