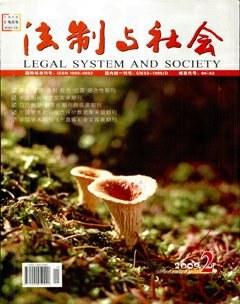論WTO爭端解決中的“司法積極主義”
吳 峰
摘要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是世界貿易法律體制中的偉大創新,為維護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促進全球貿易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爭端解決機構在爭端解決中所呈現出的“司法積極主義”傾向,在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和促進世界貿易發展的同時,嚴重背離了WTO的“政治契約”的本質,也違背了民主立法原則。“司法積極主義”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的出現,使得WTO的決策權開始從政治部門向司法部門轉移,并有可能使WTO陷入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關鍵詞世界貿易組織 爭端解決機構 司法積極主義 合法性危機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2-031-02
“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它指的是“一種司法哲學,促使法官為推動進步的社會政策而偏離嚴格的遵循先例原則”。WTO爭端解決中的“司法積極主義”受到了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一方面,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簡稱“DSB”)通過“司法積極主義”對WTO的實體及程序規則作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一定程度上為維護世界貿易體制的穩定和促進世界貿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DSB“司法積極主義”的實踐也可能會將WTO推入“合法性”危機的泥沼。
一、 “司法積極主義”在WTO爭端解決中的具體表現
(一)將WTO之外的一般或特殊國際法規則納入WTO
如在1998年“美國海蝦——海龜”案中,上訴機構援用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來解釋GATT第20條g款,以說明海龜屬于“可用竭的自然資源”。在涉及環境措施的爭端中援引爭端當事方共同參加的多邊環境條約作為解釋WTO規則的淵源,已經在實踐中為DSB所逐步接受。DSB在對待“非WTO規則”問題上的“司法積極主義”傾向由此可見一斑。
(二)通過發展性解釋對WTO規則作出與時俱進的發展
例如關于GATT94第20條(g)款“可用竭的自然資源”是指采取保護措施的國家管轄范圍之內的自然資源,還是也包括其管轄范圍之外的自然資源這一問題,DSB在歷史上曾做出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在美墨“金槍魚——海豚案”中,專家組認為該款僅適用于保護“采取保護措施的國家管轄范圍之內的自然資源”。然而在兩年后的美歐“金槍魚案”中,該案的專家組卻認為“自然資源”可以是位于采取保護措施的國家管轄范圍之內的,也包括該國管轄范圍之外的,還可以是不屬于任何國家管轄領域的自然資源。在1997年“海蝦—海龜案”中,上訴機構進一步提出“自然資源”的含義并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應當是“發展的”(evolutionary)。“可用竭的自然資源”不僅包括礦產資源,而且還包括有生命的自然資源。
(三)超越《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以下簡稱“DSU”)的授權創設規則
這一點我們可從DSB對待“法庭之友”的態度上得到確證。早先在“美國汽油標準案”和“歐共體牛肉荷爾蒙案”中,專家組都拒絕考慮接受法庭之友陳述。而在2000年的“英國鋼鐵公司補貼案”中,上訴機構明確賦予自己接受“法庭之友”報告的權利,并認為自己有權以不與DSU相沖突的方式決定DSU中未曾涉及的程序問題。在2001年3月的“歐盟石棉及石棉制品案”中,上訴機構就走得更遠了。不但主動向利害關系方聽取意見,而且還起草了一套書面規則,明確規定了向上訴機構提交“法庭之友”陳述的程序。
(四)超越成員方間(尤其是爭端當事方間)的共識進行司法
例如在“澳大利亞汽車皮革案”中,專家組認為,即使“任何一方都沒有在我們面前提出自己對該條含義的特殊解釋,而且事實上,雙方都認為我們不應涉及他們并沒有提出的解釋問題。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發現對面前爭端的解決存有必要的話,并不能排除我們考慮這一問題。專家組對協定的解釋不能受當事方論點的限制。”因此,該案的專家組明顯背離了先前專家組所一貫堅持的“不告不理”原則。
二、“司法積極主義”在WTO爭端解決中面臨的困境
(一)與WTO的性質不符
“世界貿易體制之所以能夠建立和運行,條約是法律上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作為一個“成員主導型”國際組織,WTO的成立基礎是《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條約”。這種“政治性”契約屬性就意味著在WTO中,任何規則若未經成員方達成一致,不應成為WTO規則并予以適用的。同時根據DSU的規定,DSB在爭端解決中的法律解釋“不能增加或減少適用協定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這也充分表明,現有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仍然是一個契約性的法律適用機制。因此,DSB的任務就是維持爭端方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而不是根據他們的判斷來發展WTO規則。而DSB在“積極主義”的司法模式之下,通過自己能動的司法解釋將WTO之外的規則納入其中,構成了對WTO“契約模式”的背離,與WTO的性質不符。
(二)與民主理念相悖
傳統觀點認為,“司法積極主義”最主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其“反多數”的特性。因為無論是國內司法體制,還是國際司法體制,其司法者本質上都不是民選的,而是權力機構任命的。“司法積極主義”會使得司法部門成為一個“超級立法機構”,從而“損害權力分立這一重要的憲政原則”。
對于“國際立法”而言,無疑需要征得各主權國家的同意。因此《馬拉喀什協定》規定,“部長級會議應履行WTO的職能,并為此采取必要的行動。”“在部長級會議休會期間,其職能應由總理事會行使。”因此,真正合法有效的決策與議事機構應當是部長級會議和總理事會。而DSB的“司法積極主義”無疑是讓這些非民主的外交官員、貿易政策制定者或者法律專家來通過能動的司法為廣大的WTO成員方創設新的權利與義務,不僅違背了DSU中對DSB爭端解決權限的限制性規定,而且還進一步損害了世所公認的民主立法原則。
(三)與國家主權原則沖突
主權是國家最重要的屬性。國家主權原則既是“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核心”,也是“構筑國際法大廈的基石。”基于國家主權理論,在國際貿易關系的實踐中,各國國際貿易政策的決策者均認為,國際貿易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只有通過談判而不是“司法機構”的法律解釋所能產生、修改或增減的。因此,WTO決議需要在全體成員方一致同意的基礎上作出,并須經成員方批準。而DSB卻在司法實踐中,通過“積極主義”的司法,在維護“貿易自由化”的名義下,不斷地為成員方創設新的權利與義務。這種做法不但構成了對成員方WTO權利的侵犯,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還違背了國家主權原則。
(四)與“規則取向”相悖
與GATT相比,WTO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規則導向”。“WTO總理事會的規則制訂權與爭端解決機制及上訴機構的準司法權和貿易政策評審機制的政策審查權的分離加強了國際層面的制衡,它與DSU對專家組及上訴機構成員獨立性的規定一道極大地限制了非規則因素對爭端解決的影響,從而成為‘規則取向得以確立的組織保障。”
但是綜觀近年來WTO“立法”與“司法”的互動過程我們發現,正是司法權的過分熱心,才助長了成員方的惰性,導致“立法懈怠”現象比較突出。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指出,“今天的世界仍然是靠實力,只不過冷戰前更多依靠軍事實力,現在更多依靠經濟實力。”雖然WTO目標是“規則取向”,但“世界經濟的現實狀況與WTO規則的逐漸完善,遠未達到能夠支持以純粹的法律規則為評判標準的WTO機制的運行階段。”這就使得WTO所追求的“規則導向”缺乏相應的經濟基礎。DSB“積極主義”地司法也未能如預期的那樣促進WTO立法技術的提高,反而使得DSB日益趨于動用司法力量來發展WTO規則,加劇了“規則取向”的異化,使得WTO并未能真正擺脫“實力”與“外交”的傳統窠臼。
(五)導致WTO決策權從政治部門向司法部門的轉移
從司法角度而言,為了使規則適用于具體爭端,DSB必然會就爭端方間對規則的不同理解做出澄清。雖然依據DSU第3.9條的規定,部長會議和總理事會享有專有解釋權。但由于WTO的結構性缺陷,部長會議和總理事會對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所作的解釋缺乏有效的“立法回應”。DSB事實上已成為解釋WTO規則的“權威”,而且其“司法權”也開始侵蝕部長級會議和總理事會的決策權。因此WTO的決策權開始從政治部門(部長會議和總理事會)向司法部門(DSB)轉移,從而破壞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可預見性和安全性。
三、“司法積極主義”與WTO的“合法性”危機
當前,混亂正充斥著世界貿易體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它不得不面對許多棘手難題:環境問題、勞工標準問題、公共健康問題及人權問題等。在一系列棘手的“與貿易有關的”問題面前,DSB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在“司法積極主義”理念的指引下,以“判例”形式對WTO規則作出與時俱進的發展。維持WTO合法性所必需的“有效性”基礎卻因DSB“司法之臂”的不斷延伸而不斷削弱。隨著1999年西雅圖會議在抗議聲中草草收場,2003年坎昆會議的無果而終,WTO也面臨著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十字路口”。
辨證地說,WTO在它取得成功的同時就已經蘊育了今天的困境。因為“WTO爭端解決程序‘司法化的本身,就可能導致某些政策制定全被創設的司法機構所‘侵占”。而以WTO為主導的世界多邊貿易體制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國際機制,所以更多的人開始把WTO視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協調杠桿,認為相對“發達”的爭端解決機制意味著涉及范圍很廣的“與貿易有關”的問題都可以在WTO內得到解決。因此許多爭端——如 “美國汽油標準案”、“海蝦——海龜案”等——都迫使WTO不得不對超出其能力范圍的事務做出判斷。
以DSB的“司法積極主義”為龍頭推進規則發展的模式給WTO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實踐表明,主權國家的權利正在逐漸被削弱。一小部分貿易官員與國際貿易法律學者正代表全人類進行著政策選擇與“國際立法”。但基于各國觀點的紛繁復雜,僅由DSB的幾位專家學者就為世界上幾十億人口進行政策或法律抉擇,無疑極大地損害了WTO所賴以生存的建立在“經濟合理性”上的“合法性”基礎。
當然,能動性司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的局限性與社會現實發展之間張力的結果。但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司法積極主義”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而且必須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方能達到理想效果。在WTO中,“不適當的專家組‘積極行動主義姿態將會疏遠成員方,因而威脅GATT/WTO爭端程序本身的穩定性。”從而將WTO推入“合法性”危機的泥沼。
注釋: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the 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 (1979).760.
趙維田.特殊的裁量機關——論WTO的司法機制.國際貿易.2001(1).
See Robert Howse,“the Jurisprudential Achievemen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 Preliminary Appreci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2002).12.
李鳴.國際公法對WTO的作用.中外法學.2003(2).
王鐵崖.國際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02.
張文彬.論私法對國際法的影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0.
張春林.從“歐共體——美國‘301條款爭端案”的審段看WTO爭端解決機制規則取向之異化.國際經濟法學刊(第8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340-341.
[美]德威特.市場經濟大師們的思考.中譯本.2001.203.
[德]M·希爾夫. 權力、規則和原則——哪一個是WTO/GATT的法律導向?.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夏季號.
See Anne O. Krueger(ed.),The WTO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215.
[馬來西亞]許國平.世貿組織和多邊貿易體系:現存的問題和未來的構架.國際經濟評論.2002(4).
See Kal Raustiala,“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ism”,1 Chi. J. Int'l L. 401,Fall,2000.401.
[美]約翰·H·杰克遜. GATT/WTO法理與實踐.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