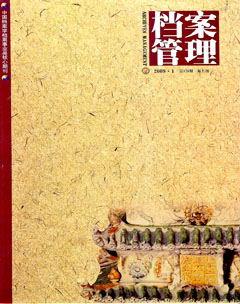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
任漢中
當年。吳寶康先生提出要建立“國際檔案學”,我曾經為之感到興奮。檔案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應該有些共同的規律可探尋,建立基本的管理原則或原理還是有一定基礎的;但20年過去了,我卻越來越感到茫然。甚至感到所謂“國際檔案學”就如“讓世界充滿愛”一樣是遙遙無期的美妙幻想。這讓我認識到還是“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來得更為實際,特別是對于檔案學這樣一門年輕的學科。
檔案學是一門社會學科。大凡社會學科,在國際上取得如“牛頓定理”一樣普遍認同的基本理論是不容易的。同樣是號稱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古巴、越南、朝鮮,以及新近由共產黨掌權的尼泊爾,卻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對于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西方和東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卻有著不同的解釋。互相依照自己的理解指責對方不民主、不講人權。更何況檔案是一種國家的重要信息資源,他關系到國家主權、國家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于政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和控制。對檔案的控制與管理被認為是政府的職責之一:指導檔案管理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和歷史。這必然導致檔案管理的制度與方法千差萬別,這也是檔案學沒有像圖書館學那樣建立世界廣泛認可的理論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所說“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并非是要固步自封、畫地為牢,而是要從本國的檔案工作實際出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再尋求國外的先進理念和原則技術;而不是不顧國內檔案工作實際,盲目引進國外的管理技術和方法,來使之與國際接軌,“文件中心”便是一個失敗的先例。檔案學是一門應用學科,理論對于實踐的意義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檔案學術研究中將進一步得到重視和體現。檔案學這一門年輕的學科,更應該從檔案工作的實際出發,其正確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決我國檔案工作的實際問題,正確解釋檔案的諸多現象,勇于接受檔案實踐的挑戰;而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先進而先進,為接軌而盲從。
“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代表的是一種求實的精神,這對于檔案學尤其重要。各國的檔案實踐各有不同,在其實踐基礎上產生的理論原則并非都具有普遍價值。即使目前大家相對認可的來源原則、全宗理論、鑒定理論、開放原則,在具體實施上,各國的差異也是十分巨大的。這說明,“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并非“中華民謠”。
其實,中國這個山頭是檔案管理實踐的富礦。我國有著幾千年的檔案管理歷史,曾建立了世界上最豐富的檔案館藏,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世界上僅見的二十四史和豐富的文化典籍,如果沒有先進的檔案管理理念和良好的檔案管理技術方法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卻沒有去大力開發和研究。且不說司馬遷2000年前就提出的“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這一檔案工作的終極目標,即使當下最時尚的“大文件觀”也并不新鮮,我國古代學者劉勰和近代學者許同莘就有過深入的研究,大可不必陷于“西方語境”不能自拔。
檔案學,還是“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