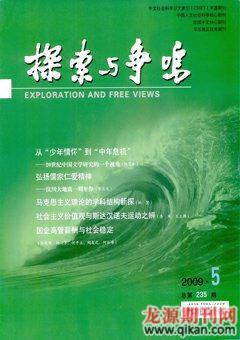我為什么建議“廢除或淡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
內容摘要 觀察和研究社會,從宏觀分析層面區分,主要有系統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分別運用這兩種方法分析研究社會的理論,可以稱為社會系統理論與社會沖突理論。人們選擇理論模式與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相關,革命和戰爭年代強調矛盾和斗爭,以社會沖突理論指導實踐無可厚非;和平年代則宜采用系統分析,突出人與人之間和諧合作的一面。“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仍然沿用戰爭思維,因而不適合當今時代的需要。1982年憲法實際上已經廢除了這一提法。
關 鍵 詞 社會系統理論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和諧 沖突 憲法
作者 謝維營,上饒師范學院政法系教授、《上饒師范學院學報》副主編。(江西上饒:334001)
首先感謝何敬文教授,他對筆者的《哲學的魅力——思想探索的快樂》一書第六章第三節做了認真研讀,并寫了批駁論文——《憑什么“建議廢除或淡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以下簡稱“何文”);其次感謝《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編者,他們把“何文”在2008年第1期予以發表,并在“封面要目”上給予重點介紹。
自從筆者2005年提出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重新評價以來(參閱謝維營:《理論與歷史的背反——對“人民內部矛盾”提法的反思》,以下簡稱“反思”,載《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后收入上述著作,作為該書一節),已經引起了一些關注,但遭到嚴肅的理論反駁還是第一次。筆者這兩年對此問題的研究有些進展,盡管筆者的基本觀點不變,但對原有表述已經有所超越,因此筆者不想就“何文”的所有具體批駁一一作答,而是想把“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社會系統理論進行比較研究,以表明筆者之所以“建議廢除或淡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的原因,并對“何文”的一些關鍵批評作一些解釋和辯護。
觀察和研究社會的兩種理論
觀察和研究社會,可以有多種方法,也可以有多種理論。從宏觀分析層面區分,主要有系統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相應地,分別運用這兩種方法分析研究社會也就產生了兩種理論,即社會系統理論與社會沖突理論。
1.系統論與社會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提出于20世紀40年代,真正作為一門科學被確立則是60年代的事情。一般系統論通常把系統定義為:系統是由要素組成的具有一定層次、結構和功能并與環境發生聯系的有機整體。這個定義包括了系統、要素、結構、功能四個概念,表明了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方面的關系。系統論認為,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衡性、運行有序性等是所有系統的共同基本特征。
自從系統論提出以來,其理論和方法在研究人類社會時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用系統方法研究社會的理論稱為社會系統理論。社會系統理論的提出,不僅為觀察研究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和方法,而且也為統籌解決現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方面的各種復雜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社會系統理論對于人們研究、分析和處理社會中的個人行為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認為,社會中任何個人行動的實現程度與個體的意識、心理、經驗及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因此,在治理社會的過程中,在判斷個人行為時應力求全面,任何簡單化、公式化、極端化和片面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容易在復雜的社會現象面前形成某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從而造成種種失誤。
2.矛盾與社會沖突理論
矛盾概念在中外歷史上源遠流長,由于毛澤東的《矛盾論》及相關的其他著作(包括《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空前普及,矛盾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矛盾理論廣為人知,矛盾分析法成為生活在現代中國的人們分析研究一切事物、一切問題的重要方法。不過,矛盾概念本身是有多重含義的:辯證法說的“矛盾”是“對立統一”,即矛盾的雙方既有互相對立、互相沖突的一面,又有互相促進、互相合作的另一面;日常語言中(也包括毛澤東的大部分著作)的“矛盾”則大多是指事物或行為互相排斥、互相抵觸、互相沖突。例如“矛盾百出”、“自相矛盾”、“矛盾升級”、“矛盾激化”,等等。所以,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使用“矛盾”一詞時,幾乎總是在“強調”事物、事件、行為、群體之間互相排斥、互相沖突的一面,而“忽視”它們之間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依存的另一面。
運用矛盾分析法研究社會,可以發現人類社會就是由“矛盾”構成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有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等等。其中,由于根本經濟利益的互相沖突引起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最為重視的,這方面的論述貫穿于馬克思恩格斯各個時期的著作中。運用矛盾分析法研究社會的理論可以稱為社會沖突理論。
社會系統理論與社會沖突理論都是分析研究人類社會的重要理論武器,它們本身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而且這兩種理論本身并不是水火不容、涇渭分明的。社會系統理論也要用到矛盾分析法和社會沖突理論的某些原理,社會沖突理論也會兼顧系統分析、全面分析。不過一般而言,就這兩種理論各自側重的方面來說,社會系統理論比較強調社會系統的和諧性、有序性、協調性,比較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合作性、互助性、共生性;社會沖突理論則比較強調社會各方的矛盾性、沖突性、對立性、排斥性,比較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斗爭性、互相限制性、互相制約性,等等。因此,可以把社會系統理論和社會沖突理論視為主要是兩種不同的思維類型起作用構成的理論體系。前者是系統型思維、協調型思維、合作型思維、和諧型思維;后者是矛盾型思維、沖突型思維、斗爭型思維、戰爭型思維。相應地,兩種理論也有不同的適用領域。
“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屬性
“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在性質上屬于社會沖突理論的范疇是毋須證明的。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社會一直處于激烈的戰爭狀態,毛澤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革命中學習革命,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毛澤東駕馭戰爭的杰出本領,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在領導革命武裝斗爭時處理各類復雜矛盾的能力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相對而言,毛澤東對領導經濟建設、對領導科學技術的發展等則存在一定的理論盲區。全國解放前夕,面對勝利,毛澤東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毛澤東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并提出“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1]問題在于:“意識到”是一回事,實際去做是另一回事;想做好是一回事,能否做好是另一回事。任何人在處理問題時都有自己的“思維定勢”,在遇到難題時這種“思維定勢”就會頑強地表現出來。因此,在和平時期的某些特殊情況下,毛澤東仍然沿用戰爭年代的思維來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是不奇怪的。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正是把社會上的一切人,按照戰爭年代的特點分為兩種:一種是“敵”,包括所有敵對階級、敵對分子,他們共同構成了“敵對勢力”;另一種是“我”,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其他勞動人民、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都是“人民”。然后,毛澤東又把“人民”分為幾個部分,每一個部分內部和每一個部分之間又都存在各種“矛盾”。[2]毛澤東希望能夠“正確處理”這兩類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我們不是從表面上看待毛澤東的以上論述,而是從思維類型上把握其本質,那么就應該承認毛澤東在這里堅持的仍然是矛盾型思維或戰爭型思維。“人民內部矛盾”的“兩分法”是以“敵我矛盾”的“兩分法”為前提的。
關于“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邏輯缺陷以及在和平時期難以把握的原因,筆者在“反思”一文中已有詳細分析,在此不再重復。筆者在這里想提出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在實踐中究竟應該由誰去“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正確處理敵我矛盾”由誰處理呢?當然是“我”處理了。在“敵我矛盾”中,“我”只是矛盾的“一方”,另一方是“敵”。在軍事常識中,一般而言,“敵”是不受也不可能受“我”支配、控制,因而可以被“我”任意“處理”的。在“敵我矛盾”中,如果一定要準確表述“我”的態度、“我”的方針、“我”的策略,似乎只能說“積極開展對敵斗爭”、“正確制定和執行對敵政策”,等等。企圖“正確處理敵我矛盾”,是在潛意識里把“我”當成不但是“我”本身,而且又是可以超脫于、凌駕于“敵”、“我”之上的裁決者、支配者和控制者了。
同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有一個由誰來處理的問題。就拿建國以來“政府和‘鬧事群眾之間的矛盾”來說,就算它是“人民內部矛盾”,那么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必然有一個由誰處理的難題。首先,這種矛盾不能交給第三方,如“上級政府”或“全體人民”,因為它只是“上交矛盾”而不是“處理矛盾”;其次,這種矛盾也不能交給矛盾的一方——“鬧事群眾”,否則必然使事情越鬧越大;最后這種矛盾也不能交給矛盾的另一方——“政府”(這里的“政府”不是廣義的抽象的政府,而是與“鬧事群眾”發生矛盾的某一級別的具體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來處理,因為在這種矛盾中,政府本身是當事人,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把“鬧事群眾”與“政府”之間的“人民內部矛盾”交由“政府”來處理,最后的“處理結果”就很難保證公正,甚至根本就無法保證公正。但是在“人民內部矛盾”框架下的社會現實中,所有這些“矛盾”最后又不能不交給政府處理。這是實踐中為什么屢屢強調“正確處理”,而往往得不到“正確處理”的根本原因。
或許可以認為,毛澤東這里說的“正確處理”是由“黨”來處理,即不管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最終都要由“中國共產黨”來處理。這也是似是而非的,“黨”其實也是由“人”組成的,任何人都沒有能力任意處理“敵我矛盾”;至于“人民內部矛盾”,由于實際政治生活中的黨政不分,由“黨”來處理與由“政府”來處理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
筆者之所以特別提出“由誰處理”的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被某種“無意識”或“下意識”遮蔽了,也就是說,人們在說“正確處理”某某矛盾時,是認為處理這類矛盾的“主體”是無需特別指明的。但實際上,像“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有極大廣泛性和包容性的概念,由“誰”來處理至關重要。只有把自己視為超越于“敵”、“我”,超越于“人民”之上的不受“敵”、“我”和“人民”制約的人物,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能力。
應該說,毛澤東當年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是確實有自己的良好愿望的,筆者不同意某些人說毛澤東1957年是“引蛇出洞”之類的評價。問題在于,戰爭有戰爭的法則,和平有和平的定理;軍事有軍事的邏輯,經濟有經濟的規律。指揮戰爭、武裝斗爭和治理國家、發展經濟決不能等量齊觀。“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兩類不同的事情,需要兩種不同的理論指導。戰爭中,是“兩軍相遇勇者勝”,是“軍令如山倒”、是“氣可鼓不可泄”;和平時期,則是“和為貴”、是“家和萬事興”、是“后退一步天地寬”。在戰爭時期,片面夸大敵情會動搖軍心,瓦解自己,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片面強調自己的優勢,把敵情估計不足,則容易犯急性病,盲目樂觀,盲動蠻干,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和平時期,則正好相反,夸大敵情易犯“左” 傾錯誤;對敵情估計不足則容易犯右傾錯誤。
事實再一次證明,客觀事物的運行機制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即使如毛澤東這樣一位偉大人物也不例外。毛澤東在提出“兩類矛盾”時應該說是非常自信的,對“發動群眾”給黨整風也非常樂觀,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人”而不是“神”,當后來的事情發展超出其預先設想的范圍、框架,特別是當他認為有可能失去對局勢的控制時,原來的自信和樂觀受到很大打擊,多年來形成的戰爭思維立即重新占了上風,認為“樹欲靜而風不止”,重新打出“階級斗爭”的大旗,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對敵斗爭”。
誠然,社會沖突理論在和平時期也不是絕無用武之地,強調“社會沖突”的目的可以是鼓吹革命,崇尚斗爭;也可以是呼吁合作,促進和諧。不過,退一步說,就社會心理而言,人們還是希望使用正面意義的詞句來表達自己的真實感情和思想。那就是為什么“和諧社會”比“矛盾社會”或“沖突社會”更深入人心的道理。
那么,在和平時期是否仍然需要開展對敵斗爭呢?在“人民內部”(姑且使用大家熟悉的語言)又是否需要斗爭呢?筆者認為仍然是需要的,關鍵是以什么方式開展斗爭的問題。筆者認為,和平時期或者說一個國家在政局穩定時期,對敵斗爭并不可少,對“人民內部”發生的違法犯罪現象和不道德不文明行為也需要展開“斗爭”。但是筆者始終認為,所有這些“斗爭”,都必須嚴格限制在社會主義法治的范圍內,不應該也不允許再用運動的方式開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斗爭。這樣的主張,該不是“法治萬能”、“法律萬能”的觀點吧!
對“何文”若干批評的辯護和反駁
1.關于“人民內部矛盾”概念提出的時間
“何文”說筆者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是毛澤東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說法“不確切”,認為毛澤東在此之前幾個月就以“人民內部的事情”、“人民內部的問題”、“人民內部的斗爭”、“人民內部的矛盾”等形式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概念,并且扼要地闡釋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些“核心理論問題”。“何文”斷言筆者“把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時間推遲了三個多月,實際上是要回避1956年下半年的國內外社會背景,而這個背景對正確理解人民內部矛盾概念至關重要”;接著“何文”簡述了毛澤東在這一時間的談話,分析了為什么毛澤東要提出這一概念的原因。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就學術上的“提出”而言,應該指正式發表,在此之前的“談話”、“內部講話”、“指示”等不能作為“發表”的證據。因為一般群眾并不知道這些“談話”、“內部講話”、“指示”。“何文”說筆者有意回避也是“不確切”的。我們如果承認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有始終一貫的理論體系,而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或權宜之計,那么毛澤東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的思想并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實際上,前面筆者已經說明了毛澤東提出這一概念的現實和思想根源:毛澤東企望用領導軍隊的辦法領導國家、用領導革命的辦法領導建設,把和平時期復雜的治理社會的系統工程設想得過于簡單了。
2.關于“依憲治國”問題
“何文”認為,實行“依法治國”最根本的是要“依憲治國”,這是至理名言。“何文”說:“我國憲法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規定是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最根本的法理依據。”為了說明問題,“何文”舉了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作為例子。但是“何文”卻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與1982年憲法在這一問題上的重大區別。1975年憲法在“序言”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接下來,憲法還專門提出“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3]1978年憲法仍然在“序言”中重提“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準備對付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顛覆和侵略”。并且保留了“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4]1982年憲法(也就是現行憲法)把這些內容全部刪去了,其中就包括“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當時憲法修改時的激烈爭論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把曾經寫入憲法的內容又在新的憲法里加以刪除(也就是“廢除”),這些內容在新時期里最起碼已經不適合或不恰當,則是肯定的。硬要把憲法已經廢除的概念和詞句重新提出,并把“堅持”這些“思想”說成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請問何教授:這是否有點一廂情愿?是否有點強詞奪理?
3.關于“法治萬能”、“法律萬能”的問題
“何文”批評筆者提出的“‘依法治國要求國家公務部門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把法律作為裁決一切是非對錯的準繩”,是“法治萬能主義”或“法律萬能主義”,是“試圖靠依法治國來‘包打天下”,真讓筆者大吃一驚。何教授應該知道,“依法治國”是寫入新憲法和新黨章的根本指導原則,是中國人民吸取“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的沉痛教訓后,取得的最寶貴的思想成果和制度建設成果。國家公務部門不“依法治國”,難道要以“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治國?要以“領導講話”或“首長批示”治國?1982年憲法第五條鄭重宣告:“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5] 在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莊嚴地寫進了憲法。世界上當然沒有“萬能”的東西,“法治”和“法律”也不例外。但是何教授應該知道:“法治”是和“人治”相對立的概念,“法律”是和“臨時政策”、“領導講話”、“內部精神”相區別的強制性規范。為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不使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隨著某些領導人的進退而改變,為了國家的根本任務、基本國策不致因為某些領導人的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除了大力加強“依法治國”、大力加強法治建設以外,別無他途。因為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法治”過了頭,而是“人治”現象還極為嚴重,靠“臨時政策”、“領導講話”、“內部精神”、“首長批示”治理國家的現象還司空見慣,“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還任重道遠,在這種情況下批判“法治萬能”、“法律萬能”,豈非南轅北轍?
4.關于“憑什么”建議廢除或淡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
“憑什么”建議廢除或淡化“人民內部矛盾”的提法?就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已經實際上“廢除”了這一提法,憑中國人民的立法實踐已經邁出了這一可貴的步伐。至于黨和國家領導人至今仍然對這一概念時有提及,并不能說明這一概念就是應該永遠保留下去的“科學概念”。筆者個人理解,領袖人物對這一概念的沿用,既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著名學者”們還鮮有對這一概念的批判性理論分析,中國的“著名理論刊物”也鮮有刊登這一類文章的膽識,因而領袖人物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也有可能是人的“思維定勢”和“語言習慣”,導致了人們總是喜歡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無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認為領袖人物的“講話”或“指示”比現行憲法更“權威”,認為領袖人物的“講話”或“指示”有使憲法已經廢除的內容在社會生活中重新發揮作用的必要。至于“何文”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批評筆者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反思”,筆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牽強附會”。筆者認為,憲法規定我們對一切違法行為都必須進行追究,懲辦違法者,這是先確定“行為”的違法性,然后才“懲辦”違法者;而“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分,是首先認定某公民是“敵人”還是“人民”(恕筆者直言,這句話是不通的,參閱“反思”一文),然后才確定是給他們“民主”還是對他們“專政”。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治國方式。哪個對哪個錯,哪個好哪個差,歷史早已經做了結論。
筆者曾經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學術的根本價值在于有根據地懷疑,是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是提出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思想。學術的目的是使人們有理由、有根據地懷疑原本堅信不移的東西,并在此基礎上創新。[6]學術的良知和學者的責任是統一的,他們存在的價值貴在“批判”,即根據一定的原則對一切曾經被認為是所謂“天經地義”的東西進行“審查”、“解析”、“評價”,提出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為決策人或決策機構提供參考。這種“審查”、“解析”、“評價”并不能保證不犯錯誤,但正是這樣一種“審查”、“解析”、“評價”,使人類不斷產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觀念,不斷使科學取得進步。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史上,這方面的范例比比皆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史上,這樣的事例也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光是30年中國社會面貌的巨變,就得益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啟蒙”,得益于前一輩探索者的不懈追求。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每一步都凝結著探索者的艱辛和決策者的膽識:沒有對“社會主義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公有制經濟”的質疑,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不會有“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沒有對“人民公社”制度的批判,就不會有“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創造;沒有對“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否定,就不會有“干部離退休”制度的問世。至于否定毛澤東提出來的“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否定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探索者甚至付出了自由、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今天,我們享受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成果,理應為改革開放的深化和“進一步解放思想”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1481.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317.
[3][4][5]許崇德. 中國憲法參考資料選編.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78、86-87、108.
[6]謝維營、劉曉雪. 對我國“學術失范”現象的制度倫理分析.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
編輯 杜運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