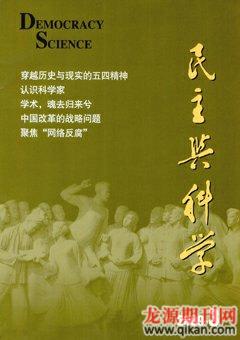五四雖已遠去,啟蒙仍需努力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各種紀念和解讀都會出現。進入21世紀以來,對“五四”的反傳統、反封建精神,海內外都出現了一些新質疑,大體可歸納為三類:
一類意見是學理上的,例如林毓生、余英時對“五四”有一些新的說法。另一類意見是“中國特色”的,例如一位倡導“國學”的大學校長認為,“我們國家的整個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經學就相當于國學。遺憾的是,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其實蔡元培也不都是對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說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廢止讀經反對尊孔,出任北大校長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學管理制度,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但我國60年來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蘇化”,如果為了反對“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讀經”,難免有繼續愚民之嫌。第三類意見出于信仰危機甚至逆反心態,導致對“五四”歷史及其思想遺產的鄙棄。從“反傳統”的意義而言,這類意見反倒像繼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卻不是封建傳統而是“革命傳統”。
“新文化運動”經常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稱“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前者是后者的發生背景和思想基礎,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及其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發展并豐富了新文化運動。對這兩個相互關聯的運動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種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清末中西文化對撞下思想啟蒙潮流的繼續。從政治解讀而言,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五四”以后出現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以陳獨秀為代表)積極投身政治,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而首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是孫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并對此作了政治解讀。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但后來的解讀卻更多地是政治化的。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港版)中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雖是極而言之,卻道破了中國封建文化扼殺民族創造力的特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長期教化與壓抑,培育了中國人平時順民、亂時暴民的“國民性”,并隨著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而引發社會危機。“五四”的反傳統精神,即是對五千年封建“殺子文化”的反抗。自“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中國何時才能走出兩種文化循環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并包”的新文化?仍是一道待解之題。
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有成,但貧富差距懸殊,文化失去創造力。面對普遍的信仰危機,一些人又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當陪祭,“老調子”至今唱個沒完。蔡元培民國元年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初,下令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不久再度下令廢止師范、中、小學讀經科。他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故各級學校不應祭孔。針對守舊派尊孔及“以孔教為國教”等主張,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創議。在民智未開、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皆是保護少年兒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舉,但未見其有禁止大學講授經學的政令。他后來執掌北大,也是兼容新舊之學,提倡學術自由。“經學”與“讀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指責“蔡元培當部長,把經學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據?中國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論。洋人講“中國學”或“漢學”皆有科學定義,國人籠統以“國學”自詡,甚至將“經學”與“國學”混為一談,皆有偷換概念之嫌。文化學是一個大概念,其實無分中西。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巨子,都是學貫中西、受過全套傳統教育而又從封建營壘中殺出的人物。就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學術風氣而論,胡適整理國故,得益于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蔡元培辦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代學術大師。顧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孔子作為中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對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教定于一尊、實行文化專制的反動,縱有矯枉過正之處,其進步意義同樣不容抹殺。“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對傳統文化的認真反思與批判繼承。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二者豈有偏廢之理?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托空言。中國在“五四”后出現了一批學術大師,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也在海外成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是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90年后環顧神州,“五四”已遠,新啟蒙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