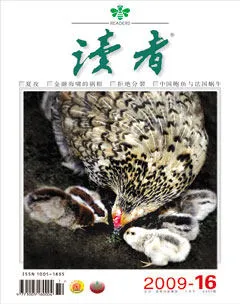塞林格的“洛麗塔”
YEE
喬伊斯,沒(méi)有指針的鐘
在喬伊斯的記憶里有兩個(gè)父親:一個(gè)活在白日,他會(huì)穿著干凈的襯衣,為母親煮上一杯咖啡,為她和姐姐準(zhǔn)備好早餐,在晨光里讀上一段新聞,然后上班;而另一個(gè)父親屬于夜晚,他會(huì)突然沖進(jìn)她的臥室將她叫起,讓睡眼蒙眬的孩子去看他畫室里的畫,或者紅著眼睛在屋里大吵大鬧,抱怨生活。
母親有著猶太人的血統(tǒng)和黑皮膚,熱愛文學(xué)、藝術(shù),尤其是詩(shī)歌。雖然,過(guò)早的婚姻生活和不太明智的伴侶選擇讓她過(guò)早地結(jié)束了學(xué)習(xí)生涯,但她并不愿意承認(rèn)這一生唯一的一次自我選擇是一種失敗,她將之稱為一種奇異的組合。這種自我掩飾有時(shí)會(huì)出現(xiàn)在給女兒的信中。
母親偷看完十二歲的喬伊斯的日記后給她寫了這樣的信:雖然你們的父親和別人的父親看起來(lái)不太相同,但沒(méi)有這樣的父親也不會(huì)造就現(xiàn)在這樣的你。
從看完母親的信的那一天起,喬伊斯就不再繼續(xù)寫日記了。直到多年后,她意識(shí)到一個(gè)母親告訴她的孩子不能說(shuō)出自己最痛苦的感情,這是一種誤導(dǎo)。她將成年后長(zhǎng)期困擾自己的自閉和憂慮歸因于童年時(shí)不協(xié)調(diào)的家庭關(guān)系。
耶魯?shù)某笮▲啠利惖穆妍愃?/b>
在寫完最后一份學(xué)校申請(qǐng)時(shí),喬伊斯并沒(méi)有意識(shí)到自己正陷入飲食紊亂的困擾。在升學(xué)的壓力下,喬伊斯吃不下任何食物。進(jìn)入耶魯時(shí),喬伊斯幾乎變成了一個(gè)紙片人。
那是個(gè)活潑而迷惘的年代,耶魯?shù)拿恳黄椒矫咨隙紦碛羞@世界上最具才華和野心的年輕人。喬伊斯只是個(gè)穿著鄉(xiāng)下衣服的丑小鴨,在這個(gè)各自放縱、各自煩惱的校園里,她覺得自己就是一個(gè)異類。
她又重新回到了給報(bào)紙雜志投稿的老路上。
十八歲時(shí)她有了新的計(jì)劃。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總統(tǒng)大選正在進(jìn)行中,她給《紐約時(shí)報(bào)》周末專欄遞上了一份十八歲年輕人對(duì)現(xiàn)今社會(huì)和生活的思考——《十八年華回首往事》。帶著自傳的性質(zhì),她將十八年的苦惱和困惑一股腦兒倒出。時(shí)報(bào)刊出了她的照片,大大的眼睛,瘦小的身體,洛麗塔一般童稚的目光。
一夜之間,她的名字成了街頭巷尾的話題。她意識(shí)到所有這一切已經(jīng)不再是一種個(gè)人的行為。
喬伊斯將兩個(gè)郵包的信倒在了床上,來(lái)信除了表示認(rèn)同的,還有很多是表示憤懣、諷刺和指責(zé)的。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她的注意,這位寫信人要求她將他的信件保密,并且告訴她,他能想象出她一定是在中學(xué)舞會(huì)上常常獨(dú)坐一旁的“壁花小姐”。接下來(lái),這位讀者還誠(chéng)懇地忠告她要珍視自己的才華,小心那些別有用心的出版商和制片人,落款是“真誠(chéng)的J.D.塞林格”。
走出塞林格
信封上的地址是用手寫的,科尼什新罕布什爾——一個(gè)由此向北約六七十公里的小鎮(zhèn)。喬伊斯也許是耶魯為數(shù)極少的沒(méi)有讀過(guò)《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人,但塞林格的名字就像可以呼風(fēng)喚雨的咒語(yǔ)。她只知道他過(guò)著隱逸獨(dú)居的生活,為了避免被人打擾,他搬到了一間山上的小屋里,山下有一塊著名的路牌,上面寫著:私人禁地,嚴(yán)禁擅自進(jìn)入。
她心懷忐忑地回復(fù)了這位神秘而名聲顯赫的作家的來(lái)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會(huì)記著您的忠告。”終于,她準(zhǔn)備收拾行裝去看他,她并不十分清楚這個(gè)五十三歲的男人邀請(qǐng)一個(gè)十八歲女孩共度周末意味著什么。為此她專門泡在圖書館里研究《生活》舊刊上塞林格年輕時(shí)的照片,發(fā)現(xiàn)他有一雙精致的手,潔白而修長(zhǎng)。
盡管照片中的黑發(fā)變得有些花白,但塞林格的樣子她還是一眼就認(rèn)了出來(lái)。在火車站,她向他跑去,而他只是微笑著看著她。他駕車帶她走進(jìn)了那個(gè)神秘的私人禁地。除了放未發(fā)表的手稿的那間密室,她幾乎參觀了他所有的屋子,還見了他的兩個(gè)孩子。
她帶著幻想向他走來(lái),覺得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歸宿;而他亦抱著幻想擁著她,麥田少年終于找到了可以守護(hù)的對(duì)象。為了和塞林格長(zhǎng)相廝守,她干脆回耶魯辦了退學(xué)手續(xù),收拾好行裝就搬到了塞林格的家。而生活和想象卻有著莫大的距離。塞林格迷戀著一種“克制”的生活,每日幾乎要花一上午的時(shí)間沉思打坐,通常要到下午喬伊斯才能見到他。而他對(duì)她的保護(hù)就是讓這個(gè)涉世未深的少女遠(yuǎn)離物欲,沉浸于生命的內(nèi)省和安靜的寫作生活中。
真正的隱逸生活對(duì)一個(gè)少女來(lái)說(shuō)確實(shí)是無(wú)法忍受的,她提出了想要一個(gè)孩子。塞林格明確地告訴她,他已經(jīng)有兩個(gè)孩子了,不想再要了。她開始害怕起來(lái):她十九歲了,會(huì)不會(huì)有一天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她太老了?當(dāng)她再次對(duì)他提出想要孩子的請(qǐng)求時(shí),塞林格對(duì)她說(shuō):“你知道,我不能再有孩子了,這一切都結(jié)束了。”
和塞林格在一起的一年,她寫出了《往事回眸》,再次登上《紐約時(shí)報(bào)》的照片欄。一年之隔,她卻仿佛蒼老了許多。一年前,他們開始通信;一年后,她被他趕出了他的私人領(lǐng)地。不過(guò)這本書還是為喬伊斯帶來(lái)了不菲的收入。她花了三千美元為自己買了一部車,剩下的錢則買了一套房子。
他們就這樣突然地失去了維系關(guān)系的繩索。雖然事后喬伊斯數(shù)次要求回到塞林格身邊,但都被冷冷地拒絕了。直到她從別處得知塞林格又有了新的女孩兒,她才明白過(guò)來(lái),自己并非他唯一的“洛麗塔”,也就逐漸放棄了這種無(wú)謂的掙扎。
她沒(méi)有了工作,也沒(méi)有再回到學(xué)校,《往事回眸》的版稅也很快用光了。她覺得走投無(wú)路,在新家里,她又開始了寫作。
雖然喬伊斯窮其一生都在尋找那個(gè)被拋棄的答案,但她的努力只是堆砌了幾部自我療傷的文字。在漢密爾頓的評(píng)論中,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句關(guān)于塞林格的注腳,也算是道出了喬伊斯的心聲:“那不是性的魅力,而是精神的力量。你感到他有一種力量,能從精神上禁錮一個(gè)人。和他在一起,應(yīng)該說(shuō)是一個(gè)人在拿她的精神冒險(xiǎn),而不是拿她的道德品行冒險(xiǎn)。”
(一 鳴摘自《優(yōu)雅》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