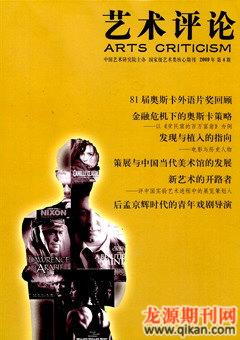新藝術(shù)的開路者
王 萌
在中國,身份比較明確的“策展人”(Curator)出現(xiàn)在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以“獨立策展人”(1ndependent-Curator)的出現(xiàn)為特征,后來進(jìn)入美術(shù)館。西方的策展人的原型是博物館中的“藏品研究員”,瑞士伯爾尼美術(shù)館(Kun sthalleBern)的館長哈拉德·澤曼(Harald Szeemann)離開該美術(shù)館后于1969年策劃了著名的“當(dāng)態(tài)度成為形式”的展覽,被認(rèn)為是第一個獨立策展人。
中國的這種策展人與西方有所不同,從表面上看是一個反向的關(guān)系,但更深層次里反映出的是上世紀(jì)自80年代以來美術(shù)界的巨大變化:從“新潮美術(shù)”開始,一種不同于“既有形態(tài)”的“新藝術(shù)”——前衛(wèi)藝術(shù)(Avant-Garde Art)——在中國出現(xiàn),伴隨著也出現(xiàn)了參與其中的批評家。由于“新藝術(shù)”在創(chuàng)作、傳播、組織和流通的方式上與舊的藝術(shù)運作系統(tǒng)不兼容,批評家開始自覺參與到組織展覽中去,作為早期新藝術(shù)運動的推動者與整合者,批評家以美術(shù)界“學(xué)術(shù)代表”的身份參與其中,出現(xiàn)了“批評策展化”趨向。
批評家上馬:“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
隨著“新潮美術(shù)”的不斷展開,青年畫家以勢如破竹之勢、如狂飆般猛烈沖擊舊有的中國畫壇。青年畫家和理論家的熱情空前高漲。1986年的“黃山會議”,通過了由批評家組織全國青年美術(shù)大展的計劃。展覽歷經(jīng)波折最終于1989年2月在中國美術(shù)館開幕。策劃者是當(dāng)年的青年批評家,高名潞作為展覽籌備委員會負(fù)責(zé)人,栗憲庭負(fù)責(zé)展廳的設(shè)計,范迪安負(fù)責(zé)展覽的宣傳,費大為負(fù)責(zé)對外聯(lián)絡(luò),孔長安負(fù)責(zé)藝術(shù)作品銷售,唐慶年負(fù)責(zé)經(jīng)費安排,王明賢負(fù)責(zé)其他日常事務(wù)。此外,劉驍純、周彥和侯翰如等人都是籌委會成員。
雖然由于一些偶然性因素,“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被迫停展。這個展覽成了80年代現(xiàn)代藝術(shù)運動的一個階段性的“暫停”,從此之后熱情空前高漲的青年美術(shù)運動停了下來。但是“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卻給傳統(tǒng)的畫壇帶來了一種新機(jī)制——“批評家集體策劃”。帶有“策展傾向”的批評家將零散于中國各地的“新潮美術(shù)”集中到了北京,起到了在整個現(xiàn)代藝術(shù)運動中不可或缺的“整合力”的作用,是中國策展人出現(xiàn)的先潮和前奏。可以說,從那時起,中國的批評家穿上“策展人”的鎧甲,騎到了馬背上,開始了他們的藝術(shù)征程。
1990年代初:“虎狼之圍”與“另辟蹊徑”
“80年代后期中國藝術(shù)家發(fā)現(xiàn)在他們生存的社會中存在一種他們無法抗拒的力量,而面對這種力量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實現(xiàn)自己藝術(shù)信念的能力。于是玩世和厭世的情緒開始蔓延。”這個特殊時期出現(xiàn)了“政治波普”(Political POP)和“玩世現(xiàn)實主義”(Cynical Realism)這種“有情緒”的藝術(sh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殊階段的社會心理。但前衛(wèi)藝術(shù)在國內(nèi)得不到公開展示的機(jī)會,“栗憲庭是在那個時期為數(shù)不多的持續(xù)關(guān)注實驗藝術(shù)的批評家之一,……他在80年代的經(jīng)歷則引起了在北京的‘外國圈子興趣……首先和栗憲庭打交道的是海外的畫廊和記者,比如漢雅軒畫廊的張頌仁和美國記者Andrew?Soloman。”栗憲庭希望能夠為身邊的前衛(wèi)藝術(shù)找到出路,于是在1993年聯(lián)合張頌仁在香港舉辦了藝術(shù)展,之后赴澳大利亞、美國等地巡回展出。
此時西方的一些策展人開始來中國尋找符合他們“需要”的前衛(wèi)藝術(shù)。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劃人奧利瓦“邀請了”13位中國藝術(shù)家參加他策劃的“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前衛(wèi)藝術(shù)仿佛在90年代初期找到了一條海外“出路”,而且進(jìn)入了國際藝術(shù)的“中心”,但如同批評家王林所指出的:“奧利瓦并不是中國藝術(shù)的救星”。前面所提到的外國記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Soloman)在1993年11月19日的美國紐約《時代》雜志將中國藝術(shù)家方力鈞的一幅《打哈欠的人》放到了封面,并發(fā)表了報道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的長文《不只是一個哈欠,而是解放中國的吼叫》(Not Just a Yawn But the HOWL That Could Free China)。這個“文化冷戰(zhàn)的高手”將當(dāng)時藝術(shù)中很自然的一種“情緒”武斷地“上升”到“意識形態(tài)”:相對于客觀的現(xiàn)實,這更多是所羅門所代表的政治集團(tuán)的某種“主觀需要”。這也讓人們看清了西方對中國藝術(shù)家的“邀請”僅僅是出于“后冷戰(zhàn)思維”及“后殖民話語”的需要。這種將前衛(wèi)藝術(shù)看做是國內(nèi)“持不同政見者的藝術(shù)”,用不客觀的刻意“夸大意識形態(tài)”的方式來塑造“另外一個中國”的做法是栗憲庭沒有意料到的。
一些帶有偏見的西方策劃人繼續(xù)通過不斷的展覽和闡釋來強(qiáng)化偏見,按西方某種需要“塑造”中國藝術(shù)的“集體肖像”。1994年“第22圣保羅雙年展”和1998年“第24屆圣保羅雙年展”延續(xù)了這種思維。前衛(wèi)藝術(shù)在國內(nèi)面臨了困境之后,又進(jìn)入了西方的“話語圈套”。在落入前后夾擊的危機(jī)階段,栗憲庭對實驗藝術(shù)的貢獻(xiàn)是巨大的,他在那個“緊張和敏感”的時期對前衛(wèi)藝術(shù)持續(xù)支持溫暖了那代藝術(shù)家好多年。
90年代初期,帶有變革性的藝術(shù)已經(jīng)不合時宜,國內(nèi)平和的氣氛促生了一種比較“溫和”的實驗藝術(shù)。從1990年開始,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的陳列館和畫廊連續(xù)舉辦了許多青年教師的展覽,引起了青年批評家尹吉男、范迪安、周彥、孔長安等人的關(guān)注,他們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身邊正在形成的新藝術(shù)現(xiàn)象,并于1991年策劃了“新生代藝術(shù)展”。
“新生代藝術(shù)展”是90年代實驗藝術(shù)本土化進(jìn)程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在80年代的思路之外“另辟蹊徑”,將“實驗”從“觀念”領(lǐng)回了“語言”,這種新的轉(zhuǎn)向?qū)?0年代中后期的裝置、錄像、攝影“媒介的實驗”有一定影響。批評家繼續(xù)在展覽的策劃、趨勢的整合過程中扮演關(guān)鍵角色,通過“將原本紛繁的‘創(chuàng)作碎片清晰呈現(xiàn)”的策展話語,把實驗藝術(shù)從80年代真正帶到了90年代。
海外策展潮與本土策劃風(fēng)
1980年代后期有一批華人藝術(shù)家和批評家陸續(xù)出國,他們進(jìn)入了“西方體制的內(nèi)部”,以法國的華人藝術(shù)群體最具代表性。1990年費大為在法國策劃了“獻(xiàn)給昨天的中國明天——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的會聚”展(CHINESE DEMAIN POURHIER),參展藝術(shù)家有陳箴、谷文達(dá)、黃永砯、蔡國強(qiáng)、楊詰蒼、嚴(yán)培明,是當(dāng)時在西方舉辦的規(guī)模最大的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活動。費大為此后還策劃了一系列海外的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展,包括“非常口”、“亞細(xì)亞散步”以及“美制之間”等。這一系列的展覽構(gòu)成了著名的華人藝術(shù)的“法國現(xiàn)象”,是前衛(wèi)藝術(shù)在海外繼續(xù)實驗的代表。
除法國之外,西方其他國家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華人批評家做的展覽。1991年鄭勝天策劃了“我不想和塞尚玩牌”,1998年聯(lián)合國內(nèi)的批評家張晴在溫哥華策劃了“江南”中國藝術(shù)展,展示了江南
地區(qū)實驗藝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luò)并探討了區(qū)域文化與前衛(wèi)藝術(shù)的關(guān)系。1993年7月,高銘潞在美國策劃的“支離的記憶”。他在海外策劃的展覽還包括“銳變與突破:中國新藝術(shù)(inside out:new Chi-nese art)”和“起點與起源”,在國際舞臺展示了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狀況。侯翰如也相繼策劃了一系列的展覽,包括“從中心出走”、著名的“移動的城市”、1999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法國國家館、2003年“50屆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之一:緊急地帶(Zone of Urgency)”和“第52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日常奇跡”。他的展覽將“邊緣”的非西方的藝術(shù)有效的融入全球文化的邏輯中,以此對所謂的“中心”進(jìn)行了顛覆,成為替“第三空間”吶喊的聲音。此外巫鴻策劃的“瞬間——20世紀(jì)末的中國實驗藝術(shù)”以藝術(shù)史的方法論梳理了實驗藝術(shù)脈絡(luò)。
這些海外華人策展人與藝術(shù)家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或是繼續(xù)了對中國當(dāng)代文化的實驗、與本土的實驗形成對照,或是向西方社會介紹更新的中國實驗藝術(shù)。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少數(shù)西方人“塑造”的“被歪曲的中國形象”,但尚未徹底改變這種狀況。
1990年代中期本土出現(xiàn)了一批年輕獨立策展人,正式將策展人作為自己的學(xué)術(shù)身份,并將中國實驗藝術(shù)的進(jìn)程帶進(jìn)了一個“實驗展覽”的階段。
“實驗展覽”最早主要是將“新藝術(shù)”的實驗焦點沿著自“新生代藝術(shù)展”以來的語言和風(fēng)格層面繼續(xù)推進(jìn)到“媒介的拓展和實驗”上。1996年3月朱其策劃的“以藝術(shù)的名義”,對于裝置藝術(shù)的“合法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當(dāng)時保守的藝術(shù)觀念發(fā)起了一場尖銳的挑戰(zhàn)。而1998年朱其策劃的“影像志異”更成為90年代觀念攝影的重要展覽。1996年吳美純和邱志杰策劃的“現(xiàn)象影像”,探討了信息社會中藝術(shù)與大眾文化的關(guān)系及現(xiàn)象與影像的關(guān)系,是90年代錄像藝術(shù)實驗的一次集中展示。他們隨后策劃了“97中國錄像藝術(shù)觀摩展”這兩個展覽對于90年代的錄像藝術(shù)具有重要意義。1996年張晴策劃了“是切斷,還是延伸——地景藝術(shù)展”,將“大地”作為媒介的觀念引入了中國。2000年栗憲庭策劃了“對傷害的迷戀”展,其中的作品涉及到了對“人體和動物標(biāo)本”的媒介嘗試,這個“尖銳”的展覽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可以說是實驗藝術(shù)家對當(dāng)時現(xiàn)狀不滿的最極端行為,展覽比較客觀地呈現(xiàn)了一種“過激”的實驗對一些傳統(tǒng)思想的反思態(tài)度。2003年皮力策劃的“非聚焦——一種繪畫的維度”,將90年代中期開始的“媒介實驗”領(lǐng)回到繪畫,展示了繪畫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的實驗可能性。
在“媒介實驗和拓展”的同時,策展人的“實驗展覽”也進(jìn)行了對展覽中“主題”的實驗。如張晴所言,“鮮明的學(xué)術(shù)追求和美學(xué)思考,整體的呈現(xiàn)實驗藝術(shù)的批判性和獨立性及其邊緣性,理清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luò)并引領(lǐng)藝術(shù)潮流”。黃篤策劃的“后物質(zhì)”揭示了后工業(yè)社會中的精神與物質(zhì)關(guān)系;冷林策劃的“是我”提出90年代實驗藝術(shù)的趨向重在回到自身的“是我”立場的確立:馮博一策劃的“生存痕跡”希望實驗藝術(shù)從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被選擇”關(guān)系中解脫,生成一種獨立自為的形態(tài);顧振清的“日常與異常”從差異的角度把握了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趨勢中的“日常與異常”關(guān)系;黃專與皮力策劃的“圖像就是力量”是對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圖像問題的探討;范迪安策劃的“都市營造”與張朝暉的“新都市主義”完成了對都市化進(jìn)程的一種視覺描述。類似的主題實驗還有易英與殷雙喜策劃的“開放的經(jīng)驗”雕塑展和唐昕的“感受金錢”等。
雄心勃勃的青年策劃人開始了更為大膽的嘗試,開始了對“展覽空間”的拓展。馮博一“生存痕跡”展在倉庫中進(jìn)行,李振華的“偏執(zhí)”展及吳美純、邱志杰策劃“后感性”展均在北京的地下室展出。在獨立策展活躍的影響和帶動下,出現(xiàn)了許多民營或半官方美術(shù)館,如成都現(xiàn)代藝術(shù)館、成都上河美術(shù)館、沈陽東宇美術(shù)館、天津泰達(dá)美術(shù)館、上海多倫美術(shù)館,成為“實驗展覽”的發(fā)生空間。
90年代本土獨立策劃人的“實驗展覽”推進(jìn)了“媒介實驗”的進(jìn)程,同時在本土舊體制之外成功打造了實驗藝術(shù)的“展覽體制”,是實驗藝術(shù)在那個“地下階段”的存活空間。對于90年代出現(xiàn)的中國藝術(shù)家找國外大牌策展人“排隊看病”的怪現(xiàn)象來說,年輕的獨立策展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與海外“話語強(qiáng)權(quán)”挑戰(zhàn)和較量的本土力量。
為學(xué)術(shù)尋找支撐系統(tǒng)
1992年呂澎和黃專聯(lián)合全國的批評家策劃了“中國廣州·首屆九十年代藝術(shù)雙年展(油畫部分)”,具體分工是:呂澎總策劃兼藝術(shù)主持,皮道堅擔(dān)任藝術(shù)總監(jiān),彭德是監(jiān)委主任,邵宏、嚴(yán)善錞、易丹、楊小彥、黃專、祝斌擔(dān)任評委,殷雙喜做監(jiān)委,陳孝信、易英、顧丞峰也分別擔(dān)當(dāng)不同角色,楊荔為學(xué)術(shù)秘書。這是中國前衛(wèi)藝術(shù)在本土打造收藏體系的第一次嘗試。對于剛剛啟動市場經(jīng)濟(jì)的中國來說,這個嘗試在觀念上非常超前,意義重大。
80年代活躍的批評家在90年代初停寂了兩年后開始繼續(xù)活躍,從1993年開始,先后組織了三屆“美術(shù)批評家提名展”,并以“學(xué)術(shù)主持人制”的方式進(jìn)行,眾批評家在主持人下組成批評團(tuán)隊,從眾多藝術(shù)家中“海選”出有學(xué)術(shù)價值的藝術(shù)家,把他們湊在一起組織非主題性的展覽,相當(dāng)于一次學(xué)術(shù)的認(rèn)可和亮相。不同于“現(xiàn)代藝術(shù)展”和“新生代展”的是,提名展以“畫種”為專題分年度進(jìn)行,有點介于“策展人制”和“全國美展”的“畫種制”之間第三狀態(tài)的感覺。第一屆的“水墨畫種”由郎紹君主持,海選出了王彥萍、田黎明、陳平等15位水墨畫家:第二屆關(guān)注油畫,由水天中主持;第三屆關(guān)注雕塑和裝置,由劉驍純主持。
批評家提名展的意義在于探討中國展覽體制改革,實行“畫家是展覽主角,批評家負(fù)責(zé)藝術(shù)活動,企業(yè)家負(fù)責(zé)經(jīng)濟(jì)操作。企業(yè)家不干預(yù)學(xué)術(shù)活動,批評家不干預(yù)經(jīng)濟(jì)操作”的原則。試圖在學(xué)術(shù)和收藏之間為當(dāng)代藝術(shù)打造一種良性運作的機(jī)制。
而將實驗藝術(shù)本土收藏的支撐系統(tǒng)探索深化的是批評家冷林。他聯(lián)合馮博一、高嶺、李旭、錢志堅、張曉軍、張栩等人分別于1996年和1997年“現(xiàn)實:今天與明天”和“中國之夢”當(dāng)代藝術(shù)展,展后由“中貿(mào)盛佳”舉行拍賣會。冷林在“廣州雙年展”的基礎(chǔ)上將收藏的方式往前推進(jìn)了一步,開始嘗試用二級市場的方式來推動實驗藝術(shù)的支撐系統(tǒng)建構(gòu)。
經(jīng)過早期批評家的努力,目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市場體系已經(jīng)比較成熟。除常規(guī)的一級市場畫廊、二級市場拍賣行外,北京目前有董夢陽主持、趙力擔(dān)任藝術(shù)顧問的“藝術(shù)北京”及“王一涵”主持的“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的“一級半市場”。此外比較有特點的還有在事業(yè)單位產(chǎn)業(yè)化道路中走出特色的由陳美伶和鄒建平主持的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圣之藝術(shù)空間”,開幕后先后舉辦了由呂澎策劃的“藝術(shù)史中的藝術(shù)家”及趙力策劃的“左燈右行”當(dāng)代藝術(shù)展。在90年代初摸索的基礎(chǔ)上,學(xué)術(shù)和市場的
對接機(jī)制已經(jīng)初見端倪。這將在贊助及捐贈免稅制度、基金會系統(tǒng)不健全的情況下,為實驗藝術(shù)找到現(xiàn)實中可用的支撐力量。
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合法化與“走出去”
經(jīng)過策展人這么多展覽的介紹,政府徹底了解了這種“新藝術(shù)”的藝術(shù)史價值并看到了在“本土體制”與“海外形象”的雙重困境。如果說策展人在90年代是一個“戰(zhàn)斗”的狀態(tài),那么2000年后政府的接納和扶持使得策展人進(jìn)入了一個“建設(shè)”的新階段。
2000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海上·上海:第三屆上海雙年展”的開幕,裝置等原先不被認(rèn)可的新媒介藝術(shù)公開入選,雙年展正式引入“策展人制”,還邀請了海外的侯翰如和日本的清水敏男聯(lián)合本土的張晴、李旭組成策展團(tuán)隊。這是政府正式接納實驗藝術(shù)的開端,不僅意味著實驗藝術(shù)的“合法化”,而且也使本土建造的雙年展“國際化”。
2002第四屆以范迪安為總策劃的“都市營造”大量吸納裝置和新媒體藝術(shù),進(jìn)一步鞏固了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合法化”的局勢。而由許江總策劃的“影像生存”、張晴總策劃的“超設(shè)計”以及2008年“快成快客”使雙年展逐漸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在本土的一個重要展覽系統(tǒng)。
2002年在王璜生的努力下,廣東美術(shù)館聯(lián)合巫鴻、黃專、馮博一策劃了主題為“重新解讀:中國實驗藝術(shù)十年”的首屆廣東三年展。之后邀請侯翰如和高士明分別策劃了“別樣”和“與后殖民說再見”的后兩屆三年展。
2001年劉驍純和顧振清等人策劃了“樣板·架上——首屆成都雙年展”。具有標(biāo)桿意義的事件還有2003年北京雙年展的舉辦,而且期間出現(xiàn)以顧振清、馮博一、張朝暉為代表的獨立策劃人做的如“二手現(xiàn)實”、“左手與右手”、“雌雄同體”等大量外圍展,沒有受到任何干涉,這意味著當(dāng)代藝術(shù)已經(jīng)徹底合法化了。這些本土雙年展同時也改變了90年代初當(dāng)代藝術(shù)被西方后殖民話語所“塑造”的尷尬處境。
2000年后另外一個重要現(xiàn)象是政府開始贊助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輸出,并在一些國家交流項目中放入當(dāng)代藝術(shù)。主流藝術(shù)已經(jīng)不再敵視“新藝術(shù)”,并開始徹底改變90年代部分西方策展人所制造的”中國前衛(wèi)妖魔化”的形象。策展人范迪安從2001年開始策劃了一連串以“讓當(dāng)代藝術(shù)正常展示”為訴求的國家級外輸大展,其中包括2001年與侯翰如合作的德國柏林漢堡火車頭現(xiàn)代藝術(shù)館舉辦的“生活在此時”;2002年與皮力策劃的第25屆圣保羅雙年展中國館的“此時此地”和克羅地亞薩克勒布當(dāng)代藝術(shù)館“金色收獲”;2003年中法文化年期間在蓬皮杜文化藝術(shù)中心的“中國怎么樣?”、法國巴黎金門宮舉行的“東方既白——另一種現(xiàn)代性”20世紀(jì)中國繪畫展(此次展覽是中國20世紀(jì)繪畫成就在歐洲大陸的第一次全面展示,并將當(dāng)代藝術(shù)置入20整個世紀(jì)中國百年美術(shù)中以獲取“上下文”的連貫意義。)2003年國家開始了在海外大展建造“本國基地”的文化戰(zhàn)略。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委托范迪安與王鏞、黃篤策劃了中國國家館“造境”展,但因為“非典”的原因轉(zhuǎn)到廣東美術(shù)館進(jìn)行。中國國家館第一次進(jìn)駐威尼斯是2005年6月12日在軍火庫和處女花園之間的“處女花園·浮現(xiàn)”(VirginGarden:Emersion)由范迪安、蔡國強(qiáng)和皮力完成。
范迪安打出的這套“組合拳”改變了90年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妖魔化”的長期尷尬局面。面對“西方誤讀”,這一系列“國家行動”與海外華人策展人及本土獨立策展人所策劃的展覽融匯成一道“文化激光”射向西方,徹底完成了“中國形象”在國際社會中“再定位”的工程。在與國際對話的交流中,他提出“讓當(dāng)代藝術(shù)正常展示”及“尋求內(nèi)外兩種目光的會聚”的立場,被媒體認(rèn)為“將當(dāng)代藝術(shù)帶向國際第一人”。
戎馬倥傯的藝術(shù)騎士
“新藝術(shù)”與“策展人”都是“改革開放”的杰作。在30年的起承轉(zhuǎn)合間,中國策展人盡顯了“斗士精神”:在新藝術(shù)的“本土化及全球化”進(jìn)程、“合法化與系統(tǒng)化”事業(yè)中“披荊斬棘”,“開路沒商量”;而在新生事物的“運行機(jī)制”層面為本土乃至全球創(chuàng)造了“批評家集體策劃”、“批評家提名”、“學(xué)術(shù)主持人制”等切合實際的新方式:他們在90年代的“另辟蹊徑”,從改變現(xiàn)實的觀念訴求回到藝術(shù)本體的“語言與媒介”實驗;在21世紀(jì)頭十年“中西對話”的“建設(shè)”階段中“打造系統(tǒng)”并“尋求內(nèi)外兩種目光的匯聚”……在新世紀(jì)即將跨入第二個十年的時候,當(dāng)我們回望過去,畫布上留下的是他們“馬背上矯健的身影”!
責(zé)任編輯李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