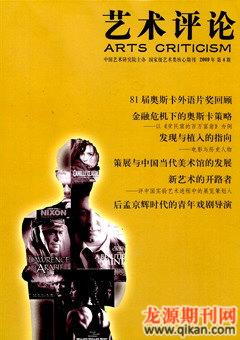發現與植入的指向
王志敏
電影與歷史人物的問題從屬于電影與歷史問題。
電影與歷史的關系比人們想象的復雜。使用文字表述歷史、見證歷史經歷了相當悠久的歲月,但是,自從電影誕生以后,表述歷史、見證歷史就不再是文字的專利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電影比文字更有優勢。這是一種對于歷史的電影寫作形式。所以,理解歷史與電影的關系固然重要,但是,要建立在正確地理解這兩者的基礎上。
《現代電影美學體系》一書中曾提到歷史問題,這里可再稍加發揮。由于解釋學的研究,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更深刻了。最終導致,對歷史的各種含義做出比較細致的區分。這樣一來,我們一般所謂“歷史”(History)的意義實際上是有三種:歷史本身、歷史本文和本文歷史。看起來我們使用的詞是只有一個,但在具體的表述中,我們加在歷史上的含義卻在這三個含義中間不停地漂移著,其后果是所述無謂。
歷史本身,即歷史全貌或真貌,有如下特點:我們可以斷定它曾經發生過并一去不再復返,如孔子所說,“逝者如斯夫”。歷史是一條長河,稍縱即逝。在這個意義上的歷史本身,是無人知曉的。因此,它不能完全再現。桑德·科恩指出:“沒有任何首要的物體或復合物能保證喚起‘歷史這一能指。”這就是美國電影學教授索布切克所說的“具有一個超越的大寫的H的歷史”。梅洛·龐蒂站在現象學的立場上,否認了這種歷史的存在,他試圖從胡塞爾還原現象的哲學嘗試轉向還原現象的本原或本質。他說,“這種還原給予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一種徹底還原的可能性。簡單地說,不存在‘具有一個超越的大寫的H的歷史——除非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即特定文化中的人‘確認并保證如此。”可以肯定,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否認歷史貌似機智,實則愚蠢。孑L子承認它的存在,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人同一條河流。”也承認它的存在。在邏輯上我們也非常清楚,如果否認這種歷史的存在,就是否認了歷史的能指,失去了能指的歷史,任何關于歷史的所指都成了莫須有的東西。我們沒有理由對于歷史再置一詞。
歷史本文,是作為人的思想、言論和行為的記載、記錄以及意志目的、行為后果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留下的痕跡的歷史,這種歷史是以具體的著作、影片、文物和古跡形式存在的歷史,屬于陳跡的歷史。老子的《道德經》、顧準日記,都是思想的記錄,孔子的《論語》、《柏拉圖文藝對話錄》和中國的《春秋》,是言論與行為的記錄。關于“911”的那段著名的資料片斷是那次事件的紀錄。用電影手段紀錄歷史有著更為長久的歷史。阿塔爾米拉洞巖畫、北京十三陵、萬里長城、秦兵馬俑是文物和古跡,還有博物館里的那些收藏物,都是歷史本文。電影具有介于文字和古跡之間的特點,但卻具有優于文字的“見證歷史”的特點。歷史本文和歷史本身相比,只能算是殘跡或痕跡之類的東西。我們對歷史本身的任何了解,都必須通過和依賴于歷史本文,而不能超越歷史本文。
本文歷史,是通過“歷史陳跡”對某一部分、某一階段“歷史本身”所作的說明和解釋,即對“歷史本身”的理解。如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等。當然還包括哲學史、藝術史等等。這種歷史是在我們的行為、對話和理論構造中形成的。這種歷史盡管可以在時空兩個方面具有概括力量,但是充其量只能觸及歷史本身的局部。我們正是通過接觸和處理歷史本文,或者書寫本文歷史,來參與歷史本身的。按照這種理解,某些電影資料片是歷史本文,而表現歷史的專題片或故事片則是本文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英文中的History這個詞,是英文的His和story,即“他的”和“故事”兩個詞的捏合,應該理解為本文歷史,這是著作的歷史,學術意義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和歷史本文。本文歷史通過歷史本文,指向歷史本身,但是絕對回不到歷史本身,回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關于與歷史有關聯的電影,我們必須說,電影不只是故事片,還有紀錄片(我建議改為資料片)和論述片。特別是論述片,雖然已經存在,但是并未得到很好的發展。有一些影片是歷史本文,如某些資料片,有一些影片是本文歷史,如某些歷史故事片。更重要的是,電影還以相當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延伸到電視,延伸到網絡。我們知道,從故事片的角度有電視電影、電視劇,從紀錄片的角度,有電視紀錄片,從論述片的角度,有電視專題片和政論片。索布切克的局限在于她只是把電影歷史故事片同使用文字表述歷史的學術意義的歷史相比較,所得出的結論相當有局限性:“鑒于含蓄模糊的學術性強的歷史題材作品是把現時的我們客觀化、形象化為彼時的他人,因而展開性的、明晰的好萊塢歷史題材作品便似乎是把現時的我們主觀化、形象化為彼時的我們。”特別是,宣稱“好萊塢歷史史詩與任何其他闡釋歷史的模式相比都同樣是真實的、有意義的”,是毫無意義的。只要把這個問題歸結為藝術的歷史和學術的歷史的比較就可以了。好萊塢電影的歷史和文學中的歷史小說是一樣的。學術著作中的歷史和小說中的歷史的關系幾乎等于常識,完全不需要認真討論。文字表述歷史有三種方式,學術性的、見證性的和藝術性的,電影也有同樣的三種方式。
這樣一來,就使問題變得簡單化起來。
故事片中的歷史人物,即藝術性電影歷史表述中的人物,這個問題一定會涉及到歷史本文和本文歷史,但是卻指向歷史人物本身,僅僅是指向而已,指向歷史人物的能指。問題在于,本文歷史的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權力書寫。而且,只有那些重要的和著名的人物,如馬克思、恩格斯、肯尼迪、尼克松等等,才會進入其中。一般來說,故事片指向的歷史人物本身,保存下來的歷史本文和現有的本文歷史越豐富具體,留給人們的創造空間就越小。正如“戲說”莎士比亞的影片《戀愛中的莎士比亞》(Shakespea re in love)的導演約翰·麥登所說:“其實沒有必要把莎士比亞拍得那么沉重。沒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樣子的,所以我們決定來個‘戲說,為此,我們做了很多努力。”沒人知道很重要,知道得很少也很重要。在目前情況下,讓陳凱歌或張藝謀拍一部類似的《戀愛中的梅蘭芳》幾乎沒有可能。這一事實表明,電影本文的歷史人物寫作牽扯到非歷史人物的利益,除了歷史人物的親屬之外,還包括當事人即創作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創作者是在利用歷史人物。了解歷史人物遺存的人很容易知道歷史人物本身的復雜性,但最重要的是歷史人物遺存的利用價值。值得研究的是,創作者究竟是如何利用歷史人物的?在這些遺存中發現了什么?選擇了什么?如果不能發現什么,可強行植入什么?在這里提到的兩種情況下,藝術創造能力都是可以派上用場的。
在歷史題材影片的創作中,影片《秦頌》(1997)的創作與臺灣電視連續劇《戲說乾隆》(1994)在創作觀念上具有明顯的承接性,例如公主和“樂圣”之間的愛情故事同乾隆與民女之間的愛情故事一樣,都是屬于“戲說”之列。歷史人物秦始皇同另一位傳說中的人物高漸離的個人關系被放大了,并放到了影片
故事的中心位置,影片還特意虛構了兩個人在童年時代的生死之交。關于這一處理的意圖,影片導演周曉文說得很清楚:“我這影片的初衷就是說其實誰也不能把誰的精神或靈魂征服了,或者說誰屬于誰,不管你有多大權力,要想征服另一個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最后留下的孤獨的人是贏政,他什么都得到了,唯獨得不到他喜愛的人。殺人容易,得到一個人的情份不容易”。我們得出結論,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關于秦始皇的全部歷史資料,無論從哪個意義上都不可能提供這樣的結論,這些新鮮的理念是創作者主觀植入到歷史人物秦始皇身上的。
在由塞夫和謝麗絲導演的歷史題材影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1997)所設定的故事情境中,鐵木真本人所采取的具有歷史性的最重要的舉動完全被做了私人化的解釋。影片的處理有兩點相當突出。首先是,作為一位已故部落領袖的后代,他本來已經放棄了任何在政治發展上的抱負,只是由于他的妻子孛爾帖被搶走這一事件對他個人的強烈刺激才激發了他為父親報仇及拯救部落的政治激情。更為突出的一點是,影片對鐵木真之所以能終于成為成吉思汗的性格上的寬廣胸懷和雄才大略解釋為對他童年時代殺了他的一個兄弟這一事實的不斷反省。這種解釋無論是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心理學的角度,都可能是有問題的,但卻頗具時代特征。
美國影片《戀愛中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in love)是一部“戲說”莎士比亞的影片。該片獲美國第71屆(1999)奧斯卡金像獎11項提名,獲“最佳影片”、“最佳原創音樂”等7項大獎,成為當年媒體最熱門的電影話題之一。影片把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創作歸結為莎士比亞一次刻骨銘心的戀愛的結果:1593年(正值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倫敦,充滿著勃勃的生機和浪漫的氣息。年輕的莎士比亞為他的新劇本取了《羅密歐與海盜之女埃塞爾》的名字之后,便陷入了思路枯竭狀態。他渴望著從女友羅薩琳那里得到創作靈感,卻偏偏撞上了女友在和別的男人做愛。絕望中的莎士比亞撕碎了劇本草稿。讓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在隨后的挑選演員的考試中,遇到了對他傾慕已久女扮男裝前來應試的上流社會美女薇奧拉。愛情火花點燃了莎士比亞創作靈感,也使薇奧拉的表演才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舞臺上的羅密歐與情人終成眷屬,薇奧拉反串大獲成功。但在現實中,薇奧拉卻被父親許配給了一位貴族,而且得到了伊麗莎白一世的準許,悔婚絕無可能。愛情的絕望使得莎士比亞重新構思他的劇本,把喜劇變成悲劇,并改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一部千古不朽的偉大的愛情悲劇就這樣誕生了。
該片的成功帶動了銀幕上的一股作家“情史熱”,于是,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浪漫故事也被拍成了電影《諾拉》。影片表現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與諾拉·巴娜克勒之間一生的愛情傳奇。無論身世還是才情都無法與喬伊斯相配的鄉村少女諾拉,靠著對喬伊斯的忠誠與溫柔,使得她成為喬伊斯畢生愛情的港灣和創作靈感的源泉。影片試圖告訴觀眾,沒有諾拉就沒有喬伊斯的一世英名。
這種發現與植入的指向,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對領袖人物表現中同樣得到了體現。究竟是發現還是植入,是一般電影觀眾甚至一般的研究者都沒有能力作的一件事情。發現與植入的權衡肯定受到各種制約。領袖人物在電影中的表現最早可追溯到影片《大河奔流》(1978),中國電影在這部影片中第一次出現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形象。這類影片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涉及重要人物并表現重大事件,一類則涉及重要人物卻并不表現重大事件。《開國大典》(1989)、《開天辟地》(1991)屬于前者,《毛澤東和他的兒子》(1991)、《毛澤東的故事》(1992)屬于后者。兩者都表現人物,但是前者事件突出,后者人物突出。人物的表現從偉大瞬間與神圣場面中轉變到平常與普通事務來表現。有的作品甚至開始有了對領袖人物的動作行為進行心理動機分析的藝術處理。
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革命歷史的人格化,其實質是領袖人物表現的形象化。影片《大決戰——遼沈戰役》(1990)中是這樣表現毛澤東的,遼沈大戰下來,毛澤東把戰場指揮權交給了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前線指揮員。休息之余,毛澤東要過過槍癮,周恩來、朱德等人先打,大致都是八九不離十,輪到毛澤東,他站在地圖前像拿鉛筆一樣把手槍揮來舞去,發表著關于戰略問題的見解,弄得周圍的人有些擔心。周恩來只好提醒他槍里有子彈,他才停下來開始瞄準,結果一槍未中。刻意表現了毛澤東性格中平凡可愛的一面,嘗試突破以往作品中反復渲染的神化了的領袖形象。在《開天辟地》、《大決戰》、《毛澤東和他的兒子》以及《周恩來》等一系列影片當中,歷史作為一種背景及人物活動的舞臺,成為領袖人物人格化表現的手段,著重表現了李大釗的叱咤風云、屢遭挫折,毛澤東的富于理想、高屋建瓴,周恩來的忠心耿耿、鞠躬盡瘁,鄧小平的沉著冷靜、樂觀堅毅等等。著重突出其雖光彩照人,卻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這種努力始于《孫中山》(1986)、《巍巍昆侖》(1988)和《開國大典》的創作。有所不同的是,《孫中山》的人物塑造以歷史事件為線索,不以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為依據。而之后《毛澤東和他的兒子》《周恩來》等這類歷史題材和人物傳奇相交溶的創作,導演對歷史更是采取了虛化手法,人物從歷史進程中游離出來,以加強對人物性格的細膩的紀實性的刻畫。
奧列弗·斯通導演的《刺殺肯尼迪》(1991)和《尼克松》(1995),一部事件突出,一部人物突出。更重要的是,后一部影片還特別對尼克松進行了某種精神分析。影片《尼克松》對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表現與精神分析學家對尼克松的人格描述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兩者最大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打破了美國公眾心目中的關于尼克松的印象,描寫了一個近乎“惡魔似的超凡的然而是悲劇性的,沉迷于過去而不能自拔的,既脆弱而又有領袖感人魅力的,受到驚嚇又十分強硬的”,酗酒成性的男子的形象。影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表現他妻子和母親的關系,希望我們從白宮的錄音系統去追溯童年時期母親對于他的絕對控制,甚至還暗示觀眾,他的失敗可能是反對這種控制的某種努力。
影片中的這種表現不僅引起了尼克松家人的抗議,而且幾乎引起了輿論界的公憤。有人甚至說,不要相信這部影片的任何一點兒內容。據說基辛格看過該片的劇本以后,以其整體上的虛假為由給予否定。人們還可以舉出影片中的許多牽強附會的例子:“尼克松酒精中毒不是真實的”。導演斯通原來想用湯姆·漢克斯來扮演尼克松,被拒絕了。隨后斯通竟起用了在《沉默的羔羊》中扮演變態狂的霍普金斯。這種選擇也說明一定問題。同時影片也注意通過視覺細節來表明尼克松的變態特征,比如他玩弄自己舌頭的那種惹人注目的舉止。可以說是對表現歷史人物的影片對歷史人物美化多于丑化傾向的一個反動。
陳凱歌把紙枷鎖的隱喻植入影片《梅蘭芳》的劇
情,盡管發人深省,但仍讓人感覺與整部影片的內容游離。即使經過思考覺得可以融進整個劇情,還是明顯地暴露出導演觀念植入的痕跡。發現的選擇性與植入的強制性暴露無遺:陳凱歌是相當仰慕梅蘭芳的,把梅蘭芳當成了閃閃發光的藝術大師來表現,仰慕其輝煌成就,尤其羨慕大師備受呵護眾星捧月的狀態,但似乎并未能深入其真實的內心世界。與此同時影片還刻意表現出某種憂慮,即憂慮人們對藝術大師的過分呵護,以至于很可能限制或影響了其個人自由與幸福。在此思想主線下,復雜難述的梅蘭芳其人其事都被大大簡化。特別是,梅蘭芳與孟小冬關系的柏拉圖式的升華,都是服從于這一創作動機的。盡管導演意識到了藝術大師的洗盡鉛華與繁華落盡后的實質,但是,還是竭盡全力地訴求于藝術大師的輝煌與幸福兼得的狀態。導演并沒有給這位藝術大師賦予傳統的藝術追求,反而是一種更為世俗化的追求,即片中所謂的“座兒”,影片似乎想告訴我們,這位大師是為了“座兒”而活著的。不管這個座兒究竟是應該轉換為票房,還是應該轉換為觀眾。你可以懷疑這部影片述說的可靠性,但它確定不移地指向梅蘭芳。
影片《羅丹的情人》表現的是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情人卡米耶·克洛岱爾(Camille Claudel,1864-1943)的故事。影片表現了年輕的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爾和羅丹的愛情關系和雕塑追求交織在一起的悲劇性故事。克洛岱爾是一位歷史人物,但時至今日,這位女性都只是19世紀末期世界藝術史上的一個腳注,一個作為羅丹的情人而存在的人。當羅丹的作品登堂入室之時,她卻被遺忘在這些作品的后面,人們頂多只能從這些作品中辨認出她若有若無的影子。盡管影片表達出一種傾向,即羅丹和克洛岱爾的愛情毀掉了一位可能青史留名或許地位并不低于羅丹的女雕塑家,但是人們還是不敢確認這一點:“影片《羅丹的情人》更關注于卡米耶-克洛岱爾的個性和激情,而非其藝術成就,因此觀眾很難從銀幕上得到的印象進行判斷,卡米耶·克洛岱爾是否是一個真正優秀的雕刻家。”“盡管受到將卡米耶·克洛岱爾塑造為早期女權主義者和被男性及藝術等級世界所迫害的犧牲者的誘惑,電影制作者還是選擇將重點集中到年輕女雕刻家堅定的表達自身欲望及同泥土的羅曼史上。卡米耶-克洛岱爾是一個有待被重新發現的天才雕塑藝術家。”這些評論清楚地表明,如果說導演真有這種植入的企圖,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美國影片《巴頓將軍》表現了二戰期間美國軍隊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巴頓將軍叱咤風云但卻迅速從歷史上消失的故事。這部影片在其國內大受稱贊,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片中的巴頓被塑造成一位熱愛戰爭視戰爭為生命的軍神般的性格化人物。仿佛人物只有這樣才是有性格似的。這位頤指氣使地隨意罵人和鞭打士兵的將軍形象幾乎成了性格化的典范。但是在影片的表現中卻幾乎是含而不露地植入了一個很快就要過時的歷史人物的暗示。影片中呈現的巴頓,仿佛是一位棱鏡中的人物,有時高大有時渺小。這使得我們可以斷定,這部影片堪稱一部有選擇地發現和不露痕跡地植入的典型。
如上所述,在我們所見到的大部分表現歷史人物的故事片中,無論是戲說還是正史,無論與真實的歷史事實有多大距離,都是指向這一歷史人物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創作者從歷史遺存中發現了什么又選擇了什么,在創作中又植入了怎樣的思想,而這些恰恰是容易為一般的觀眾和評論者所忽略的。這也直接導致了一個結果:無論在影片中呈現的人物形象看起來有多么接近這一歷史人物,創作者也一定在有意識地遺漏了一些什么的同時,又植入了另外的一些內容,在這取舍之間,作者的創作意圖盡顯。
責任編輯馮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