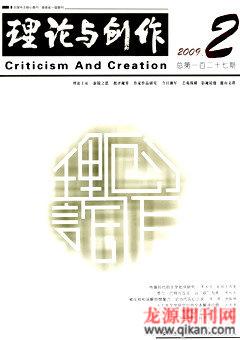生命中不能忽視之孤獨
鄧 磊 封旭明
沈從文和張煒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湘西邊地和蘆青河畔的廣漠平原濃墨彩繪,用筆下的民情故事和邊陲的天籟率真。共同構筑起詩性寫作的亮麗風景。可是作品卻透露出一股深沉的生命被放逐的悲涼感,人類似乎永遠被孤獨追趕著。連南方之水與北方之地都染上了悲劇色彩,且存在著人性至上和自然拜物烏托邦的救贖誤區。
一、孤獨生命的寓育:染上悲劇色彩的邊城之水與原野之地
現在對田園詩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誤讀,畢竟人們“對于自然的生活狀態有一種懷念和珍視,對于自然狀態下的人類生活狀態的消失有一種惋惜”。沈從文《邊城題記》言: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現在大家解讀的似乎都為“偉大處”,而忘記了“墮落處”。如有學者評論“如果說這種愛情還有一點悲劇色彩的話,那么,這悲劇既非鄉村環境所造成,亦非人性之惡所致。這種悲劇反倒是由于一個純真少女的值得贊美的本性,是由于老船工對于孫女的那種真摯的愛,悲劇最終成為鄉村人中的贊歌。”然而我認為悲劇真正的元兇是人生的隔絕和孤獨感。同時《九月寓言》發生的悲劇也是人生浮躁和孤獨造成的。沈從文與張煒在建構美麗夢幻的同時又在解構這一憧憬。《邊城》中“水”是文本的中心意象。《九月寓言》“大地”是其中心意象。由此人手我們來分析作家所賦予它們的潛臺詞。
孤獨是現代作家一個共通的情感特征,特別是京派作家注重內心的體悟和個性的張揚,使這種孤獨的情思表現得格外深刻。沈從文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中一再申明自己的文學事業“并不建筑在‘一本合用的書或‘一堆合用的書上,因為它實在卻只建筑在‘水上”。現代人類學研究成果表明,在人類社會初期,各民族都實行過兩性禁忌的隔離制度,主要是為了避免集團內部為爭奪女性而爭斗。在中國這種隔離制度與水密切聯系,經過無數次重復,最后成為人生孤獨的集體無意識。“女性原則和原始的水相聯系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主題。”比如牛郎織女傳說中那一條隔斷有情人的銀河。還有《詩經》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江水永矣,不可方思”,以及后來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洞房昨夜春風起,故人尚隔湘江水”等,水作為隔離、孤獨意象比比皆是。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中他還說:“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從孤獨中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然而,這點孤獨,與水不能分開”。這段話真正道出了作者的孤獨寂寞。
《邊城》開頭就對翠翠家傍水而居的情形進行了遠描,“有一條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有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無聲的溪水橫亙,首先給人一種孤苦無依的悲戚感受,而且天闊地廣下老人無兒女,小孩無雙親更讓人斷腸。同時“水”與人物心情相契合,比如翠翠十六歲時的端午節分外痛苦,此時“雨落個不止,溪面一片煙”。這里輕煙般的細雨與翠翠因被介紹對象不是二老,感到婚姻渺茫所引起的惆悵相契合,強化了文本的孤獨情境。實質上“水”這種寓意著孤獨的意象一直籠罩著人物。翠翠是“邊城”之魂,而恰恰她身上孤獨時刻存在。她自小失去父母之愛,對男女之事的了解只可能來自道聽途說。為此她不明白自己“在睡夢里盡為山鳥歌聲所浮著,做的夢也便常是頂荒唐的夢”,而這種夢實際上應該為春心悸動的表現。翠翠也不明白祖父,“因為兩人(翠翠與楊馬兵)每個黃昏必談祖父以及這一家有關系的事情,后來便說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時所不提到的許多事”。爺爺盡管將她視為掌上明珠,但并不真正理解她,并不知道她已戀上了二老。祖父還有這種想法:“你總有一天會要走的。”翠翠誤識二老但是又敢愛不敢言,且誤認為二老愛上了團總女兒。如果連愛人都不了解和信任,結婚不是有點盲目么,何況她首先也是著迷于二老“岳云”式的外表和“云雀”式的歌聲。而二老卻以為是她爺爺猶豫而導致天保之死,因此“他又過川東去辦貨”。有了這種怨恨他們的婚姻還能成功么?顯然不能。“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個死去的人,卻用一個凄涼的印象,鑲嵌到父子心中。兩人便對于老船夫的意思,儼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發下去。”那么后來老船工去世。“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個夜晚”。所以后來她不到順順家住,借口為“以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個生人家里去不好,還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駕船回來時,再看二老意思。”真實原因應該為害怕了世間冷暖和人情隔膜。
文中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因為翠翠的婚事,爺爺與二老父子的心理距離拉大了。大老與二老雖為兄弟但也缺乏心靈的溝通。父親與自己的親生骨肉也存在著隔膜。順順為二老相中的是團總的女兒,而二老想娶的是翠翠。為此沈從文寫道:“一切總永遠那么靜寂,所有人民每個日子皆在這種單純寂寞里過去。一分安靜增加了人對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夢。在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懷了對于人事愛憎必然的期待。但這些人想些什么?誰知道?”這難道還不是孤獨的世界么?
當代的張煒毫無疑問是最關注農村苦難和人性善惡的作家之一。他同沈從文一樣有著堅定的鄉土情結。那么在張煒筆下“大地”是什么?《九月寓言》中“大地”就是烏托邦的載體,它是一個元概念,一個頗具抽象意味的概念。在張煒看來,現代文明的困境根本就在于人與大地及人們之間的疏離,他強調人只是大地的一個器官。文本中大量描述了夜晚和奔跑的意象。“一伙兒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頭,竄到野地,他們打架,在夜里跑動,鉆到莊稼地深處歌唱,汗濕的頭發貼在腦門上”。表面的熱鬧往往印證著內心的孤寂。自由與孤獨往往相伴相隨,奔跑實際就是孤獨的表現。因此人們瘋狂的打架、打老婆和做愛。小村與外界的隔絕,造成人們與外界的對立與悲劇,進而村民的行動幾乎沒有理性可言。
作品不再把注意力投向歷史的苦難和人物的靈魂,而是投向文化意義上的小村和哲學意義上的大地。人際間那些雖然沒有公開亮相卻分明存在著的壓抑力量構成了孤獨的寓言,為此我們在閱讀中就一直感覺不到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只是被作者激情澎湃的言說給撞得暈頭轉向,當然作品的主人公是有的,它就是孤獨。可能作者的哲學思考和自我思索主宰了人物,使得他們不再具有主體意識,只是作者為了敘事變得方便的一個符號,諸如大腳肥肩、憨人、肥、賴牙、年九、彎口等,沒有任何個人的靈魂特征,很難給讀者清晰的印象,喊著這些名字就如喊著石頭一樣,雖然明白名字的所指卻無靈魂的溝通。這正是西方的存在主義的哲學內涵的詮釋。存在主義作家把人的存在作為全部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認為文學作品的主要任務是對存在做出正確的解釋。他們顛覆了傳統哲學所談論的抽象的意識、概念、本質等,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的肉體自然生命的存在或
者說是人的肉體自然生命的展開和實現。薩特認為,人在現實社會中的存在是不真實的,人生是虛無的,世界是荒謬的,他人就是地獄;同時人是孤獨的,人又是自由的,人在選擇時,既無客觀根據,亦無道德原則,更無法依賴他人。
為此張煒在《九月寓言》中構筑了存在主義的土地神話。所表現的就是人存在的荒誕性,雖然作者一直聲明融入野地是他的理想,我們也被他深深的大地情誼所震撼。但是在文本中人物真的成了存在主義人生哲學的最好詮釋。人生是荒謬的:長腿趕櫻、又白又胖的肥、少白頭龍眼、金發歡業、獨眼喜年、憨人、小疤美女香婉、三蘭子、爭年等,這些最年輕的一代,他們小時候在九月的夜色中歡快的奔跑,但是長大后他們的命運都是悲戚的——肥逃離了、龍眼井下遇害、歡業殺人、三蘭子自殺、爭年變呆、趕櫻也不唱“數來寶”了。他人就是地獄:小村人“輩輩相傳的美好習慣”“男人不打老婆又打什么?”大腳肥肩殘酷虐待兒媳婦三蘭子,金祥奸污小豆,龍眼、喜年們把挺芳扒光了往死里打。這些到此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誰叫大腳肥肩積攢下一身蠻力呢?她不往兒媳婦身上發泄往哪兒發泄呢?誰叫金祥是個老光棍,他那從未實現過的性欲不在送到家里來的小豆這兒滿足到哪兒滿足呢?而誰叫龍眼、喜年們到工區偷雞不成反被追趕呢?他們那惡氣不往工區子弟身上撒往哪兒撇呢?很明顯,所有這一切都是以放棄精神價值或者說作惡為前提的。人生是孤獨的:文中寫到野地夜晚的一切活動,尤其是青年人的夜游,讓人感到孤獨的存在以及人類的可冷。作者把他們放在食與性的生存基線上進行文化/哲學的審視,把他們驅趕到自我意識尚未萌生的野地,沒有審視出人性之美,反而展現了人性之惡。作者讓他們永遠的消失,這就更確證了存在主義的虛無感,即歸結為“死”,就像海德格爾所言“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二、靈魂救贖的絕唱:人性至上和自然拜物烏托邦的誤區
人生是如此孤獨,那么誰能夠救贖我們呢?他們的共同回答是:自然。這與沈從文、張煒幼年深刻的鄉村生活記憶,以及感謝和膜拜土地自然的養育是分不開的。“我一睜眼就是這樣的環境:到處是樹,野獸,大海,很少看到人。”“我大概也在這懷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鄉之美。那里好像到處都變得可愛了,再沒有了荒涼與寂寥之苦。”為此我們就應該明白他們的自然崇拜為何那么強烈,“太沉迷于自然天性的美麗,太急于將這種誠實美麗作為自己的旗幟和永久的歸宿”。
具體而言沈從文對自然的態度如同對宗教的虔誠,表現為一種強烈的心靈歸宿感:“即對于一切自然景物,它們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關系時,也無一不感覺到生命的莊嚴……然而人若保有這種情感時,卻產生了偉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藝術品。”沈從文作品所呈現的自然烏托邦情結與他獨特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以及“鄉下人”的文化姿態有關。他從當時的主流語境中跳出,潛心于表現人性之“常”,希望構筑起“優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湘西世界。張煒癡迷自然的野地情結與沈從文極為類似,但所處時代氛圍不同,促使他們追求的價值取向也有差異。
沈從文當時在城市歷經挫折,心中頗為低落和苦楚。他發現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國,卻成了一種畸形的存在,傳統文明又分崩離析,這種價值和道德的失范,使他惶惑不已,在《長河題記》中他說:‘現代一字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表現,不過是點綴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為廣泛的消費。挫折和惶惑感使得他無奈地將目光投向了湘西、投向了原始古樸的大自然,從而滋生出對自然的宗教式崇拜。張煒對蘆青河畔和廣闊的原野進行詩意的謳歌,與沈從文將湘西自然作為蘊藏人性是不同的。它從一開始就雜有不和諧的音符,這種不寧靜的緣由張煒將之歸結于城市,以及隨著市場經濟擴張而出現的喧囂與騷動。“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飾過的野地,我最終將告別它”。城市與野地在張煒這里形成了對立的狀態,只有在野地自然中人性才能激情飛揚,平實而堅韌的生存精神才能充盈土地。張煒的大自然有兩層內涵:它養育我們的祖先,并將繼續承擔養育我們的子孫后代的重任;它還是內心里一塊溫馨的精神家園,是張煒所認定的救贖現代人墮落、丑惡靈魂的良方。為此張煒的投奔自然,實際上有著強烈的涉世批判,他高亢的歌唱更主要的是為了召喚美麗心靈和健康人性。在近期小說中他的憂憤孤獨有時直接跳了出來,激變為了一種社會批判的符咒。可是張煒并沒有退縮,“我在這片莽原跋涉了這么久,并且還將繼續跋涉下去。我大概永遠也不能夠從這片莽原中脫身。”
沈從文筆下的自然之景,很少直接指向當時社會現實,更與階級分析斷層。他這實際上就是希望對人類實現救贖:將人物置于飽含詩意和自然靈性的環境之中,讓人性自由自在的張揚,讓人物的健康性格在其中孕育生成,映襯生命的原色,減少肉的成分,增加靈的氣息,從而以愛美之德調和人事。為此沈從文曾說:“我想造希臘小廟……在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
但是《邊城》的世界難道人性真的純凈如碧水么?難道無情欲放縱、無病態人生?難道這種人性美真的能使人返璞歸真?文本中“真真成為他們生意經的,有兩件事:買賣船只,買賣媳婦”。對于二老的性角色定位為“你這時捉鴨子,將來捉女人,一定有同樣的本領”。文章中這種男權主義思想本來就帶有歧視性。女人在社會中地位如此低下,人性得到自然全面發展值得懷疑。再來看老船工的死亡,他實際上是被合謀氣死的。當他問團總的媒人“小伙子意思怎么樣?”媒人騙他“他(二老)說: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條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現在就決定要碾坊吧。渡船是活動的,不如碾坊固定。這小子會打算盤呢”。當老船工想問清楚二老的主意時,順順又騙了他,“老船夫被一個悶拳打倒后,還想說兩句話,但船總卻不讓他再有說話機會,把他拉出到牌桌邊去。”或許沈從文感到如果他為此事而死,那么人性不就有惡的展現么?所以他安排了意外的大雨和白塔的倒塌。從而讓老船工的死亡不再成為翠翠和二老結合的障礙。可是二老的歸期又在何時?商業影子已經侵入了邊城,難道金錢的關系就不會腐蝕人性么?翠翠都認為:“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老船工也認為“有什么福氣?又無碾坊陪嫁,一個光人。”還有人高聲贊嘆:“這些關于一個女人身體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的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從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難道娼妓的出現就是為了自己的肉欲,而不是被生活的逼迫么?
實際中國的農村是殘酷的,一旦某地人口飽和了,過剩的人口就要宣泄出外,“這些宣泄外出的人,像是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找到生存的地方,又形成一個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樣的命運下被淘汰了。”
為了表達對人性的救贖是堅定的,他們作品中自
然而然出現了自然拜物教。有人認為這是他們創作中的民粹主義,而我認為這是農村出生的作家的自然崇拜。確實自然崇拜昭示著人對自然及生命的無限遐思,與沈從文對水的鐘情一樣,張煒承認“他的激情、欲望。都是這片泥土給與的。這樣,我尋求同類因為我愛他們、愛純美的一切,尋求的結果卻使我化為一棵樹。一棵樹最大的愿望就是抓緊泥土。”他們認為人必須依托于自然,并受自然的庇護,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才能幸福地生存下去。于是走向自然,回歸自然,人和自然形成一種詩意的和諧關系,就成為小說主人公的理想人生選擇。為了追求自然,張煒比沈從文更倔強,“他五年來未曾在城市居住,即使在城市也住在挨近郊區的邊緣。”
那么自然烏托邦難道就是美麗的么?張煒說“人在自然中的欣悅是無法形容的。人離開了這種交往,就是陷入苦惱的開端”。似乎大地真的成了樂園,動植物和本真的男女達到了天人合一,到處都洋溢著勞動的快樂和豐收的幸福。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隱去了野地的落后與荒誕。竟然這詩意的“大地”存在著食、色等日常生活,就必定隱藏著與野地歡娛不同的東西——苦難和孤獨。夜色下充滿著村民們的虐妻殺媳內訌相爭、饑寒困累、血腥殘酷等景象,但“苦難”在作者情感介入下,變成了生命激情的狂歡,小村世界“藏污納垢”特性也被過濾轉換成了單向度的純潔人性。“苦難”被張煒改頭換面,披了一件華美誘人的外套。為了調和這一矛盾與裂痕,他要改造“苦難”,但這種改造卻偏離了方向,顯得那么軟弱無力。正如他在《融入野地》結尾自問:“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其實在他悲然詰問中,已經否定性回答這個問題。
三、結語
由于孤獨的根性,毫無疑問《邊城》和《九月寓言》只能是人性與自然的烏托邦,在現實的空氣中都將不幸毀滅。但是把農業文明描繪的如此感天動地,依然讓我們震撼不已。當然我們明白這種人治文化與野地文化是前現代性的,而且中間充滿了張力性矛盾。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于現代文明的恐懼和對傳統的依戀,又由于對鄉村傳統本身的弊端,尤其是它的貧窮與蒙昧的體察,所以邊城中的二老為了經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張煒激情歌唱的“野地”也沉落了。在現代理性與傳統依戀間他們陷入了深刻的憂慮和猶疑。我覺得作者對作品中兩個青年的態度是很有深意的。對于二老和肥最終是否會回來,以及是否應該回來。都沒有做明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