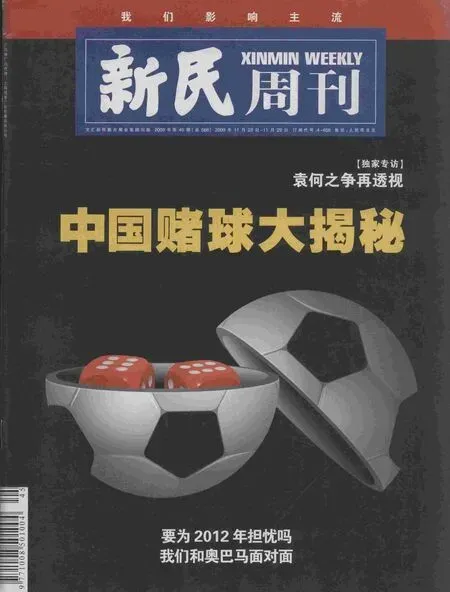《2012》:“科學神秘主義”提供的娛樂
江曉原
所謂的“世界末日”,我們既不必當真,也不必批判。但問題是,聽了這個預言之后,你準備怎么生活下去?你是不是打算按照兩年后世界要毀滅來安排你現在的生活?
我手里就有三部電影,都是以2012世界末日為主題的,它們在以一個“末日預言”作為包裝這一點上大同小異,只是對導致末日的直接原因各自編造得不一樣。比方說,影片《2012毀滅日》想象的是,地球自轉停下來了,而《2012超新星》是想象有一顆超新星爆發,巨大的能量要摧毀地球了。現在剛上映的這部電影,又有另一套看上去很“科學的”說法。也就是說,末世來臨的具體原因可以是各種各樣的,這些原因一般會被編得有點科學性,但是不管影片如何講故事,這個末日的說法本身是毫無科學性的。
末日預言在西方是比較流行的。主要是三個背景原因:
一是宗教情懷。宗教情懷就總是讓人更愿意討論救世、末日、重生之類的主題,許多宗教色彩濃烈的作品都不外乎這些主題。
二是文明周期性。西方人比較普遍地相信文明是一次次繁榮了又毀滅,再重新繁榮又再毀滅。這種周期性的文明觀在他們那邊是相當普遍的,這和我們近幾十年的教育所造成的一種直線發展的文明觀很不一樣。我們認為文明從初級到高級,無限地往前發展,而他們比較熟悉一個循環的觀念。
三是憤世情懷。喜歡講末日的人,很多是對當下的社會不滿的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太丑惡了,充滿罪惡,它理應被毀滅,所以他們呼喚著上帝快把它毀滅吧——就像《圣經》故事中索多瑪城被毀滅一樣。
這三個背景中的前面兩個,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具備的。關于文明周期性的觀念,在印度傳來的佛教中倒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佛教本土化之后,這一點并沒有成為我們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東西。對當下社會不滿的人當然任何時代都有,但是如果沒有前面兩個背景的話,就不會有第三個背景。對社會不滿的人就會從思想上找別的出路,比方說,呼喚一次革命,或者提倡順其自然逆來順受,爭取讓自己過一個還算過得去的人生。因為你沒有宗教情懷,沒有文明周期論,你就不會呼喚一個末世的到來,來改變這個世界。
2012.12.21這個日子本身就有數字神秘主義色彩,這個東西在西方是比較流行的,它已經變成了大眾文化中的一部分。拍幻想電影的人總是喜歡在這種神秘主義的東西里尋找思想資源。但是,他們做電影的時候,都只是拿它當思想資源。實際上,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災難片。他們只是給這個災難的預言披上一件末世的外衣,再給造成這個災難的原因披上一件科學的外衣,但它的主題并不在這個科學上,而在于災難。這些末日預言的電影,總是出現巨大的災難,巨大的災難是好萊塢喜歡的。
災難片有兩點好處,一是災難片總是能用特效來刺激人,拍出來的場面總是要具有沖擊力、震撼力,比如《后天》,大家就認為很成功,很有震撼力。即使是小一點的災難,比如《泰坦尼克號》,也很有震撼力,這樣的挑戰很容易刺激人不斷嘗試。第二,災難片還有一個好處,它總是可以拷問人性。在災難面前,人的各種劣根性就會暴露出來。
這次上映的《2012》,本質上也是一個災難片,它花了更大的功夫搞災難片的兩個要素。特效真是超酷,因為電腦特效技術不斷地在發展,比起幾年前的就能好很多。在拷問人性方面,它說制造了一個方舟(這次居然是“中國制造”!),好躲過災難,保存人類的精英,但是誰能進那個方舟呢?其實這種拷問已經老套了,以前的另一個科幻災難片《深度撞擊》(DeepImpact,1998)里早就用過了,說有一顆小行星要撞地球了,美國就造了一個地下掩體,就是方舟,他們指定的許多精英人士可以逃進去,剩下的位置呢,在全民中抽簽,抽到的人進去,抽不到的就在外面等死,這也是拷問人性。設置一個災難之后,可以從多方面拷問人性。
至于影片中所謂的“世界末日”,我們既不必當真,也不必批判。按照我們的唯物主義理論,這個世界有始也有終,地球本身也有生命,也有衰老死亡之日,那時候當然就是末日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末日總是可能存在的。但問題是,聽了這個預言之后,你準備怎么生活下去?你是不是打算按照兩年后世界要毀滅來安排你現在的生活?理智告訴我們,絕大部分人都不可能這樣來安排生活,他們肯定相信兩年后世界將是正常的。因為根據現有的科學理論,我們可以知道兩年后世界將是正常的,而科學在以往這幾百年里所取得的業績,讓我們相信這個理論是管用的,它對于大部分自然界現象的解釋是正確的。
有人斷言,這部電影上映之后,大家會熱衷于談論“世界末日”之類的話題。作為談助,看完電影后,沿著電影里神秘主義的話題繼續討論討論,這很自然。可是你不會因為這個而改變你對生活的安排——你明天該上班還是要上班。(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