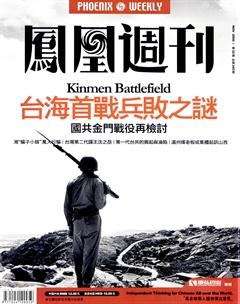中國財富增長“疑似”借助不平等
何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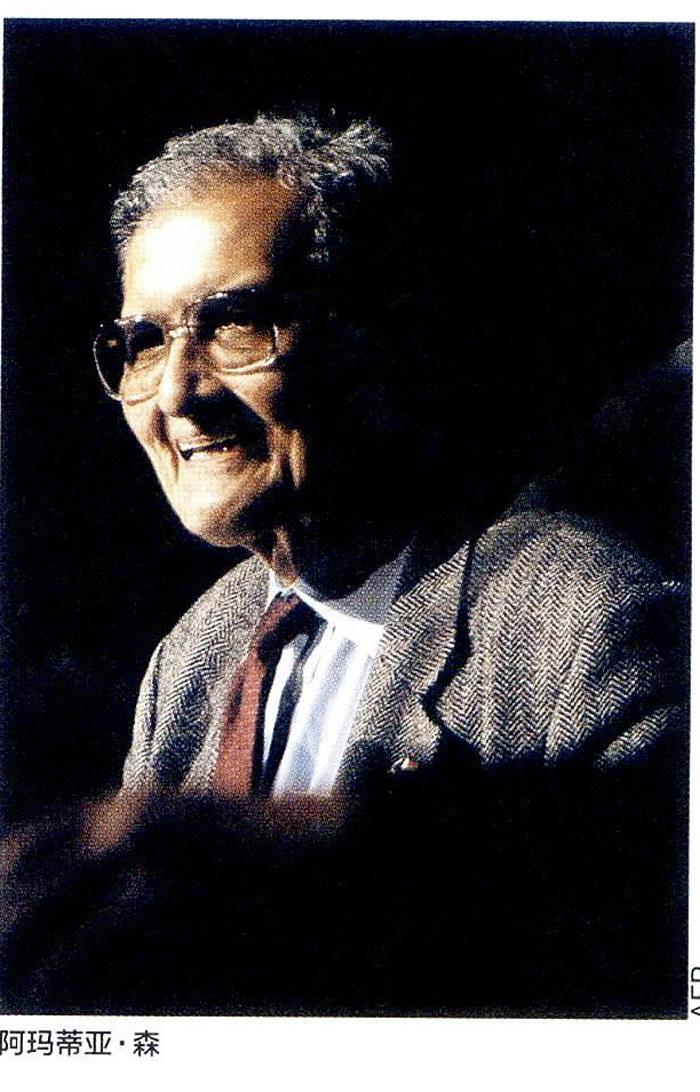
“慢下來吧,不要那么快,我們必須讓這個清晨持續下來。”疲倦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想起了西蒙和加豐科(Simon and Garfunkel)所唱的一句歌詞。
前行在貧困、不平等、環境惡化、全球化這些荊棘中,76歲的阿瑪蒂亞森無法將思考停下。
阿瑪蒂亞·森是印裔,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哲學教授,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被稱為“經濟學良心”。近日,阿瑪蒂亞·森帶著“裝滿思考”的行李來到了北京。《鳳凰周刊》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的先后協助下,對其進行了專訪。
鳳凰周刊:現在,中國政府最關心的是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速,在政府看來,如果不能保證8%的速度,很多事情沒法做。您覺得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同樣值得迫切關注的?
阿瑪蒂亞·森:不應把發展視為GDP的增長或人均收入的提高,應該以自由看待發展。自由首先是人的實質性自由,比如免受貧困、疾病、饑餓的能力、權利、過程和機會。為使人的實質性自由變為現實,還需要五個方面的自由: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性保障。
在全力進行普遍性經濟擴張時,我們有必要給予社會底層以特別的關注。金融危機中,受到失業威脅、缺乏醫療護理的家庭因遭到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剝奪而遭受打擊尤為嚴重。
現在中國對人民的生活開始給予更多的關注,有了更多的公其設施和社會服務來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鳳凰周刊:有輿論認為,中國4萬億元刺激經濟政策導致了“國進民退”。您是否把經濟不公的評測作為經濟和政策評估的主要指標?
阿瑪蒂亞·森:經濟蕭條時候,在非常局部的意義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能夠是我們的救星。盡管凱恩斯非常關注如何增加總收入的問題,但是他對財富和社會福利分配不公問題的分析,卻相對較少,對社會服務相對忽視。
現在我們要關注一下與凱恩斯同時代的對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看法,他在當前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了。正是他率先把對經濟不公的評測作為經濟和政策評估的主要指標。
鳳凰周刊:這些年中國在對絕對貧困人口進行攻堅的同時,相對貧困問題也凸顯出來,這其中與不平等有多大干系?
阿瑪蒂亞·森:貧困與不平等聯系密切。貧困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對剝奪的性質。因為貧困不是單純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收入增長非常快,以至于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其他領域進步得相對緩慢。在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引導下,中國取消了全民醫療保健制度,健康保險不得不由個人購買。由于這一轉變,中國在人均壽命等方面增速放緩。即便在中國的總體收入急速增長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當中國經濟急劇減速的時候(正如現在的情況),它便注定要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近些年里,世界基尼系數上升,中國收入增長的城鄉差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是,中國收入持續增長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過加大不平等來實現的。
而要消除貧困,促進平等,就必須從拓展能力的角度來推進自由。事實上,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甚至更有必要關注那些貧困人口的發展權利的剝奪問題,而不僅僅關注收入貧困問題本身。現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全球范圍內日益增長的公共討論中只關注消除貧困,而不關注不平等問題的趨勢。
鳳凰周刊:金融危機發生后,部分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批判。如何看待這種“反思”?
阿瑪蒂亞·森:金融危機后,很多人開始尋找一種被稱為“新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但我們當下需要的不是一種“新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對舊有觀念的新理解,比如亞當斯密的觀念,他的觀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們可悲地忽視了。
斯密的《國富論》闡釋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過生產專業化、勞動分工和充分利用規模化,從而極為有效地促進經濟繁榮。但事實上,市場運行的早期提倡者們并沒有把純市場機制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完美的運行體制,他們并不認為利潤驅動就是所需的一切。斯密的經濟學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給市場機制的“看不見的手”。他不僅支持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貧困救濟,而且還深深地關注可能存在的赤貧和不公正現象。斯密認為,市場和資本需要來自其他機構以及純粹利潤追求之外的價值的支持。
可惜的是,現在人們對斯密的印象似乎只有“看不見的手”。隨著充斥著衍生物的二級市場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發展,與交易相聯系的道德和法律的義務及責任在近些年來已經變得難以辨認。所以,面對危機,我們需要找回斯密、庇古,而不應是凱恩斯。
鳳凰周刊:這幾年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被網民抨擊為“替資本說話”。這是主流經濟學還是經濟學家的錯?
阿瑪蒂亞·森:主流經濟學在實證分析中想到的是交換主體的逐利動機和行為,受限于一種理性經濟人的邏輯假設,而與弱勢群體的經濟生活已無實質性關系。
經濟學應該關注的是現實的人,關注人的生活質量。在歷史上,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發展起來的,這一事實對于理解經濟學的本質至關重要。
如果經濟學關注的是真實的人而非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或抽象化了的人,則經濟學研究不僅與人類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類對財富追求之外的目標相關。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這種天然關聯規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責任,就是在財富創造目標之外,經濟學應致力于評價與增進自由、公正及人文關懷之類的更基本的目標。
鳳凰周刊:目前印度哪些經驗值得中國借鑒和思考?
阿瑪蒂亞·森:現在很多人在談論中國模式、印度模式、韓國模式。我覺得這是一種不恰當的方式。我從不相信什么固定模式。
從競爭角度看待中印兩國,這是把全球性的溝通與理解的實踐淪為一場賽馬。人們應該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相互可以學到什么,而不是誰將會超越誰。
印度需要更多地向中國的經濟增長、扶貧成就學習,而中國也應向印度學習關于公共交流和民主的經驗。
這次來北京探討的一個話題是貧困和兒童營養。現在印度在全國實施了一個公共項目:提供熟制的中間餐給入學學生。發放午餐包可以增加學生來學校的吸引力,更加集中注意力學習,而學生在學校里一起吃午餐,使他們在社會價值方面可以更好地趨同,創造均等化的社會。印度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我認為中國可以借鑒印度在這方面的做法。
鳳凰周刊:每當有全球性經濟首腦峰會舉行時,場外圍總有反全球化的示威。如何看待這種“背反”?
阿瑪蒂亞·森:很多人確實想把已經鋪開的“全球化”地毯再卷回來。人們抱怨的主要原因不是全球化和環境惡化之間的關系,而是在其他的方面,從某種角度上講就是分配的問題。我們的確得問一下,全球貿易帶來的益處是不是遍及所有的人類,對于這些利益的分配是公平的嗎?如果不看到公平和正義,就沒有辦法全面理解環境問題。反全球化的論點是重要的,但這是在支持促進不斷擴大基礎教育、醫療健康和土地改革以及增加小額貸款的可獲得性意義上才重要。
對于反全球化者“減少世界貿易”的主張,這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如果說同樣的人口不是生活在城市當中,而是在鄉村鋪開,對交通的需求肯定是更高而不是更少,總的污染程度不見得就會變得更低。
鳳凰周刊:歐美通過科學話語和法律機制的建構,成功地將“東西問題”和“南北問題”替換為全球環境話題,進而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道德”威懾來為其新能源集團服務。如何看待這種全球化下的“強權”?
阿瑪蒂亞·森:這里面存在的爭論還是一個公平和正義的問題。要強調一點的是,在任何領域雙方都可從合作當中受益,不論是貿易,還是環境等。比不進行合作來講,總是有很多可替代選擇的方案,能夠讓各方受益。環境問題最終需要轉向全球性的環境協議,但是不同的合同卻使得我們的義務有不同的分割。如果將一些配額機械地強加在某一些國家上面,而沒有去考慮這個國家的發展進程、需要去扶貧的努力以及是否有能力和財力去使用環境友好型的技術,那么,強加這種配額是愚蠢的,也是不公平的。
但我也對歷史公正論的論調持懷疑態度。正如中國和印度現在經常抱怨歐洲和美國在消耗全球共有物方面的做法造成的影響,我想在未來的某一天非洲很多國家也有理由質疑中國、印度、歐洲、美洲過去大量消耗全球公共資源的做法。氣候問題上,20國峰會要遠遠地比8國峰會更具代表性,盡管如此,20國峰會也不能夠很好地代表窮國。
雙方采取批判式的邏輻推理方式,現在社會中被非常多地使用。但批判性的全球推理必須包含考慮公平和公正,包括在全球來實現公平和公正以保證未來能夠實現一個合理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