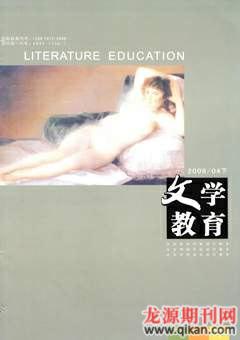樸素的寫作
吳遠道將新出版的小說集《哦,純姐》送我,讓我分享他成就的喜悅。我很高興能讀到他的作品結集,這不僅是因為他個人寫作取得的成績,也是因為在如此浮躁的社會氛圍里還有人執著于文學而感到慰藉。
還是我在文聯工作的時候,擔著《江山文藝》主編之責,遠道那時常到文聯和編輯部來,他在紙刊上發的第一篇小說大約就是在《江山文藝》上。他寫得很勤,我和負責刊物日常工作的譚冰還有小郭都有意扶他,刊物接連發表他的作品并議過想給他發一個作品小輯。我們見面,除了言說工作和生活,更多的是談道創作。他把他的小說發貼到網站里,引得眾多網民趨之若鶩,點擊率飆升。見到我時,他告訴我,要我到網站里看他的小說,以及小說五位數的人氣。我為一個作者從《江山文藝》走出去著實高興,也有了一點自得的感覺,并且想,文學這張要耐得住寂寞的冷板凳終究也還是有人愿意上去坐坐的,我們不必為文學擔憂,不要對精神和社會持悲觀的態度了吧。
吳遠道的小說,并不追求小說的技巧,一副簡單樸素的樣子。他所著力的,是在小說的內容上:小說的人物,小說的倫理價值,小說表現生活的真實性等等。
這個集子中的大多數小說都是寫人物的。遵循現實主義原則,把人物放在敘寫中心的位置,圍繞人物展開敘事,把描寫人物作為小說的主要任務和根本目的,是這些小說的明顯特點。這也是我說作者的寫法很傳統的一個依據。這些小說中,很多連篇名都是以人物命定的,如《阿三記趣》《劉老頭》《影兒》《東施》《若蘭》《夏教授》《新生》《鄰居的孩子》《小雪》《哦,純姐》《老Q》等。一些不以人物為篇名的,也還是把敘述的著力點放在人物上,如《農村那片天》《銜出相思二月天》《逃頂》等。作者對小說人物描寫,有幾點是值得稱道的。一是描寫人物類型之眾。作品表現了城鄉交緣地區多種人物,鄉村的,城市的,機關的,學校的,工作組長、婦女干部、父輩兄弟、鄉村木匠、農業局長、村支書記、按摩小姐、大學教授、純情少女、年輕夫妻……僅《阿三記趣》一篇就描寫了十六個人物。這些色彩各異的人物,使作品充滿了動感和生氣。同時也反映出作者有比較寬廣的生活面,以及表現城鄉生活的能力。二是注重人物的個性化描寫。個性化人物形象是經典現實主義寫作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作者孜孜以求的模范目標。從現有作品來看,他注重和擅長用細節和白描等手法,努力追求人物形象的個性化。中篇《老Q》中,老Q就是一個描寫成功的個性化程度較高的人物形象。老Q,用小說中人唐飛的話說:軍人轉業,善于應酬,酒量不小,沒什么組織能力,但能做具體事,個性較強,喜歡耍小聰明,占小便宜,“做了一大堆好事,動不動因為一句話或一件小事而一掃帚掃了。”營職轉業二十多年,一直未有一官半職,看著別人都跑到自己前面,“看透了官場”的他也想為自己的升遷做他不屑和不樂意的那些爛事:巴結上司,揣摸上意,溜須拍馬,投其所好,扯裙帶,走后門,依附人身。他長年請單位頭頭姜局長洗桑拿,到姜的情婦開的公司買返修車,支持處里的沈達斗倒唐飛當處長,在未如他當個副處的愿時,又受別人慫恿搶占住房,在組織考察時“發動群眾”給領導打不稱職。他失望,憤懣,消沉,但失望過后又“不得不昧著良心”向新來的領導討好。當夢想又一次破滅,他帶了憤怒回到老家,欲終老田園,卻在抑郁中死去。在老Q身上,可以看到過去用人制度之弊端怎樣扭曲了正常的人性,把一個普通人改變成為一個可笑的“社會人”。老Q這個人物集中了“官場人”的某些特征,比較典型地反映出還沒有來得及隨著經濟基礎變革而改變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現實。三是人物形象生動豐滿,生活化程度較高。遠道的一些小說,篇幅不長,又以寫人為主,因而對典型環境描寫有限,但因善于準確地運用白描和生活化的細節,人物血肉豐厚,妙肖生活,逼真有味。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阿三記趣》。這篇小說十六節,每節寫了一個人物,像是一些小篇的連綴,但人物之間又有相互關聯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關系,整體上又是一篇完整的小說。這里的人物形形色色:有頭頂油亮,淫人妻女的劉歪嘴;有“性情急躁,抓革命促生產來蠻的”的鄒大頭;有被迫由人玩弄,還被訛傳是“石女”的蓮花;有拿出自己的午飯收留懷孕女人的唐聾子;有做了公司經理的初戀情人;有純樸厚道的少年憨哥;有為給繼父治病出賣身體的小姐......這些人物都很鮮活,躍動,富有生氣。作品描寫人物往往僅靠一些密集的細節,這些細節來自生活,帶著生活的原汁原味,因而真實,可信,生動,有趣。例如,文革時期,工作組的鄒大頭在村里住隊,村里人迷信灣子池塘邊的一棵百年古松,“抓革命促生產”的鄒要搞掉這棵樹,無奈大隊長的父親反對,他便“來蠻的”,先開大會鼓動,接著親手奪過斧頭去砍,把站在旁邊大隊長的父親氣得破口大罵。就是這個工作組長,對女人也“來蠻的”,把蓮花她爹送進勞改隊,然后撥開蓮花房門,強行占有。而壞坯子劉歪嘴暗中窺得奸情,也趁機撈上一把,竟然于黑夜冒充鄒大頭去占蓮花母女的便宜,而蓮花為救她爹也愿委其身……這來自生活的一連串細節,猶如一道道聚焦的的燈光,倏然照亮了這些人物有差異的性格和各各不同的靈魂。
文學是人學。小說要寫人物,但它又應該通過人物形象表達理性的精神。好的小說要以其對生活的倫理判斷和價值取向作用于人心和社會。吳遠道的小說在這一點上也不含糊。他的作品滲透了對生活的思索、詰問、批判和期待,是一些有鮮明的傾向性的小說。《阿三記趣》與《老Q》以其對人物和生活的尖銳嘲諷和沉重的幽默,表現出對生活的批判精神。《阿三記趣》的描寫跨越了兩個時代,既寫了舊時代的可笑和不合理,也寫了現時生活中的某些負面,這是值得肯定的。作者沒有簡單地對生活進行今是而昨非的評價,而是把烙印著生活痕跡的人物形象展現出來,對人的生活的不幸寄予同情,對形成性格形象的社會環境作出傾向性的道德評判。這一點在《老Q》中更為突出。小說較為真實地描寫了一個正直的軍人蛻變成渺小的庸人的過程,一個被官場風習濡染而隨波逐流,攀附逢迎而終致低俗平庸,死不瞑目的一生。無論作者是否意識到,這個作品的價值,在于它表現出來的鮮明傾向性,即對殘存著封建官場陋習的某些現實生活負面的批判。它讓人們看到,在我們的某些人事生活、人際關系中,還散發著陳舊和腐敗和氣味,這樣的生存環境,還困扼著個體潛能的發揮。我相信,對落后、腐朽的痛絕是作者寫作這些作品的理性動力。
當然,遠道的小說也不僅止于批判生活,在另一些作品中,還表現出對生活的贊許的期待。這一點,尤以《農村那片天》最為明顯。這個中篇敘述了一個大學畢業生回鄉務農的經歷過程。王旺林職院畢業后在城里沒找到能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勇敢地回到家鄉種菜,種草,加工經營農產品,當村干部,招商引資發展村級經濟,與腐敗分子抗衡,帶領村民與黑社會斗爭,保護了創業成果,也創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這個人物和故事顯然寄托了作者對生活的熱情、贊許和期待,當然這種贊許和期待有著明顯的理想化痕跡,卻也鮮明地反映出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和信心。我們從這里也看到吳遠道的寫作是觸及到生活的主流,對生活的本質有過用心的思考的。
最后想說的是,由吳遠道的小說創作,我想到一個話題,那就是傳統寫作的生命力問題。小說寫作經過了80—90年代的實驗寫作,花樣翻新,窮盡了現代后現代種種寫作范式,使盡了各種時髦招數,及今已有人呼吁今天的小說陷入了黔驢技窮的“絕境”。然而,遠道寫作的些許成功,倒給了我們一個不經意的提示,那就是:傳統的寫實方法并未壽終,它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應該是我們觀照和解析生活的有力手段,是我們反映生活最基本的方式,是我們表達對生活的價值判斷最經典的,其他任何實驗寫作難以取代的成熟的寫作范式。我們不應因為傳統被濫殤或褻瀆而對它失去信心。舊刀多磨磨,說不定比新刀還要快,因為它的鋼火老到。在經歷了種種時髦之后,再回到寫實主義這種“樸素”的寫作上來,未必就不是出大作品大作家的希望之所在。
王浩洪,文學評論家,現居湖北黃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