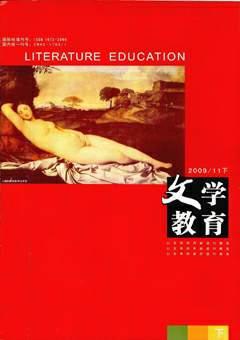以《狼圖騰》中狼的厄運來反觀草原生態
當今人類正在向生態文明邁進,這是一個嶄新的歷史進程。過去所經歷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都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由此造成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和人類自身生存的危機。《狼圖騰》的作者正是站在此的角度,“以人的生命存在為前提,以各種生命系統的相互和運動為出發點,把審視的焦點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所產生的效應上……”[1]顯示人與自然相生相宜的和諧美。當然,這種美被摧毀所產生的強烈悲劇意味,更引起我們對生態保護的反思。
一.狼的厄運
千百年來,狼就是草原之王。漢文化中,狼總是與兇險、狡詐、貪婪聯系在一起。而在《狼圖騰》中作者描寫的狼,打破了對狼的誤解與偏見,對狼有了一個全新的再認識。在草原生態系統中,肉食動物、草食動物與植物之間相互構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食物鏈。而狼在這個食物鏈中則是踞于高端的、捕獵者的地位。額侖蒙古人把狼作為圖騰來崇拜,正是建立在狼對生態平衡的關鍵性調節作用之上。當然,額侖蒙古人是以宗教的神圣形式肯定了狼對草原生命與生態平衡的決定作用,那里的人才不把狼作為不共戴天的死敵而趕盡殺絕,從而使水草豐沛的額侖草原維系了幾千年。
“文革”時期剿滅狼的運動開始了,狼群無法避免的陷入一場劫難之中。包順貴為了滅狼,主張火燒葦地,遭到許多草原人的反對,但他的身后是一個時代,一個“去陳出新”的呼喊聲高過浪潮的時代。于是,一場熊熊烈火之后,“幾千畝金葦變成一片焦土,又繁生出下風處的萬畝黑雪地。”[2]包順貴把草原上傳統的古老的生存方式相應的當成是被改造的落后對象,草原上人與自然的和諧、融洽生存狀態被打破了,草原上出現了人類對于自然的超越與凌駕。
二.草原的衰敗
狼是草原的靈魂,狼群潰敗,草原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隨著農墾文化的浸潤,草原生態的平衡開始迅速的被打破。
小說中的人物烏力吉一直倡導“既打狼又護狼”的政策,他說過草原怕的東西太多,但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來管草原,而這時烏力吉的擔憂變成了不可改變的現實。
小說接近尾聲時,當土著蒙古人“既打狼又護狼”的對策被“把狼全部消滅”的政策取代之后,狼群成了歷史,草原成了回憶,草原生態環境陷入了危機。“草原的騰格里幾乎變成了沙地的騰格里。干熱的天空之下,望不見茂密的青草,稀疏干黃的沙草地之間是大片大片的板結沙地,像布滿了一張張巨大的粗砂紙。”[3]在草原狼群的蹤跡消失之后,額侖草原上鼠害嚴重,常有馬蹄陷入鼠洞,人馬摔傷的事情發生。過度的墾殖使草場嚴重沙化,稀疏的草場上沙塵和沙礫清晰可見,草原已“今非夕比”,“草色遙看近卻無”。當小說的主人公在返城之后重新來到自己曾經生活了十幾年的草原時,映入眼簾的不是綠色的草原,看到的只有黃沙和即將干涸的河床,還有起風時那沖天而起的“黃龍”。昔日美麗的草原消失殆盡。
三.游牧文明的讓位
沒有了狼的草原,其他生物種群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且草原上人們的那種逐水草而居的與大地宇宙之氣相連的英勇豪放的游牧生活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廣袤的額侖到處都布滿了水泥樁柱和鐵絲網……牧區的草場和牲畜承包到戶以后……每個草庫侖中間都蓋有三四間紅磚瓦房和接羔棚圈。”[4]
其實,蒙古草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生活、生產方式只能以畜牧業為主。“在蒙古草原上,草和草原都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把草原上的大命殺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沒命”,[5]即便如此,在原始的環境里草原上的各種物種和人類為了生存,都在爭奪著“草”這一有限的資源。狼便擔當起維護草原生態環境的職責,維護草原和諧發展的重任。
于是,以畢利格老人為代表的富有智慧的獵手就出現了。他們既恨狼又拜狼、既打狼又不滅狼。而一個與草原的生命融為一體的畢利格老人則是這個智慧的代言者,他的死亡象征了古老的草原生活方式及其對狼的崇拜的終結,也代表了游牧民族的消退。小說最后寫道“狼群已成為歷史,草原已成為回憶,游牧文明徹底終結,……”[6]
四.“生態文明”時代的思考
作者姜戎在小說的敘述中借助陳陣之口,對一個無法挽回的消逝的草原生活方式發出的悠長的嘆息。找出了草原悲劇命運的直接制造者和社會根源,在更深層次上,“這實際上涉及到如何看待現代化對草原幾千年生活方式的影響問題。”[7]
當現代化的腳步直逼額侖草原,一下子就打碎草原上幾千年古老的生存狀態,使得草原人逃避不及。正如上面所說的那樣在滾滾的現代化潮流來臨之時,草原突然間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種極其悲涼的境地。
馬克思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著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日益控制自然,個人都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19頁)
小說當然不是從理論上獲悉這一切,而是拋棄了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觀點。不再以人的角度,而是以生態整體利益的角度極度痛惜、擔憂地展示了草原生態一步步遭到破壞的過程。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在返城之后重新來到自己曾經生活了十幾年的草原時,映入眼簾的不是綠色的草原,看到的只有黃沙和即將干涸的河床。綠洲變成了荒漠,到底是誰的過錯?沙塵暴、洪水、泥石流等的出現,這些都是人類文明與自然生態環境兩者力量出現偏移之后的警告。特別是寫沙塵暴肆虐,“整個北京城籠罩在嗆人的沙塵細粉之中,中華皇城變成了迷茫的黃沙之城。”[8]
迄今人類所經歷的現代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從而換取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濫伐森林、破壞草原,引發了大面積的水土流失,加速了土地的沙漠化。在這種生態環境下,《狼圖騰》的出現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引發我們的思考:“在人類生存與生態平衡、人口發展及人類欲望與生態資源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函數關系?”[9]從完整鏈條來看,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過大,否則,整個鏈條就會有因失去平衡而導致斷裂的危險。“當前的生態保護工作,是否應該從單純生態物種的保護上升到整體生態環境保護的層面,而不是僅僅局限在瀕危動植物保護的層面上。”[10]
小說還以草原的悲劇呼喚人類保護生態意識的覺醒,“在環境問題上要施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原則,或者說戰略措施,因為僅靠法治,以及行政與經濟獎懲手段,事實上不可能解決好環境問題,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的趨勢。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環境時代,人們必須按照‘天人合一的準則重新審視決定人們行為價值取向。”[11]小說中的悲劇的疊加正是從情感上讓人類深切的體會到生態環境的危機處境。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講,《狼圖騰》所揭示出來的生態智慧,為當下的生態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徐恒醇.生態美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P136.
[2][3][4][5][6][8]姜戎.狼圖騰 [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7]李永忠:都市化進程中的鄉土書寫[J].文藝理論與批評[M].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第五期.P85.
[9][10]韓宇宏,席格:《狼圖騰》及文化觀念轉型[J].中州學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六期,
[11]陳湘舸、林潔.論“環境時代”的生態文化[J].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期
宋彥虎,甘肅秦安縣教體局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