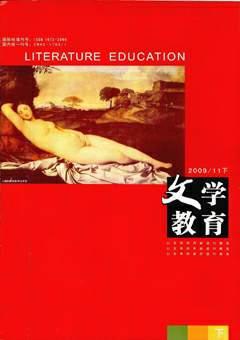我的高中生活
前幾天從廣播里聽到要在中學開設勞動技術課的消息,一時間思緒如潮水般洶涌而至、蔓延開來。
我是1973年9月升入高中的,1975年7月畢業。與現在的高中生相比,我們的幸福指數一定高出八十到九十個百分點!我們的作業一般在學校就能做完,這且不說,每學期都還要去工廠或農村勞動一月二十天。那時候,好多學校都有學工學農基地,學校每學期都會按計劃安排學生去工廠或農村勞動,又叫做“開門辦學”。我們太原五中的學工基地有山西第一機床廠、太原塑料廠、水利機械廠和電話機配件廠等;學農基地是小店區的大馬村、小馬村。在各種各樣的勞動中,我們不僅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強壯了身體;還掌握了多種勞動、生活技能,尤其是錘煉了思想和意志。
學工時,我們像真正的工人一樣每天帶著飯盒按時上下班。記得在機床廠學工那次,我被分配到電工班。每天上班后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整理衛生:灑水、掃地、擦桌、整理工具物品等。我的主要工作是跟著師傅去工人家里安電燈。師傅是個白白胖胖的小伙子,腰上挎著一套用上等牛皮制成的十分精制的電工工具套,里面插著電筆、改錐、鉗子、電筒等什物,肩上扛把梯子,神氣得很!我則挎著一個白色帆布做的大工具袋,里面裝著圓木、釘子、鏍絲、鎯頭、燈口、燈泡、拉線盒、電線等東西。剛開始主要是給師傅扶梯子,遞工具、物品等,后來就上手做一些簡單的事,比如用鉗子去掉電線頭上的膠皮、用改錐擰鏍絲等,幾天下來就掌握了安裝電燈的整套程序。從那以后好多年里,但凡家里、辦公室、宿舍等處電燈出了問題,都是由我來修理。這以后的數十年里,我常常自稱是“八級電工”(八級是當時工人等級的最高級別)。沒活兒的時候,我會跟電工班班長打個招呼,然后去看別的同學干活。一個秀秀氣氣的女同學是車工,長長的辮子被塞進工作帽里,站在龐大的車床旁,用一種坐式大老虎鉗夾住零件,機器一開動,就有很細很細的鋼絲打著卷兒被切出來。她還會時不時地用一把精美的卡尺一會兒量量這兒,一會兒量量那兒,真個是英姿颯爽!一個文靜內向的男同學開一臺沖床,一按電門,安著鉆頭的電鉆就呼嘯著高速旋轉起來,在鉆頭與零件接觸的一剎那,呼嘯聲一躍而為咆哮聲,驚天動地、驚心動魄!把我驚得目瞪口呆。再看穩穩把著操縱桿的男同學,真個是大將風度!心有余悸地來到鉗工組,就是別一番風景了。鉗工這活兒特別細致,好的鉗工個個心靈手巧。只見一個女同學兩手捏著一個車鏍紋的丁字型工具的兩端,正小心翼翼地在一只鏍母里做水平圓周運動,滿面愁容。我問怎么了,她說鏍紋車斜了,而且還滑了扣,師傅讓她重車。我接過來想幫幫忙,結果,千小心、萬努力,可傾斜的鏍紋依然,滑扣依舊。嘆息著來到電鍍車間,穿著工作服的同學從冒著一股酸味兒的水池里撈出一串閃閃發亮的零件向我展示;靠近車間門口的地方,有同學正在用電焊槍焊著什么,火花四濺……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同學們多能干呀!
在農村,我們像農民一樣扛著農具上下工。我們開荒、翻地、松土、間苗、鋤草、踩田埂;我們蹚過稻田,下過菜地,鉆過樹林;我們能分得清蔬菜、野菜和雜草,懂得什么叫間作套種以及這樣做的好處;我們會用镢頭、鎬頭、鋤頭、鐵锨等等農具。
有時,我們被派到村頭的小樹林鋤草。我們會一邊鋤一邊唱著“解放區呀么嗬嘿,大生產呀么嗬嘿……”、“紅米飯呀么南瓜湯喲嘿嘍嘿,挖野菜呀么也當糧嘍嘿嘍嘿……”就這么一邊鋤一邊唱,引得公路上的行人都忍不住停下腳步聽我們的歌聲。有時我們被派到大田里踩田埂。這活兒沒多大技術難度,就是橫著站在田埂上,雙腳并攏,一點一點平行向左側或右側挪動,目的是把田埂踩結實。剛開始還覺得挺有意思,腳下那么挪著,雙手閑著,眼睛可以自由自在地觀風景,可時間一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風景看完了,腳下的田埂卻似乎沒有盡頭。挪著挪著腰酸了,腿困了,腳不聽使喚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屁股上那兩塊肌肉又酸又痛!有時,我們被帶到菜地里間白菜苗,開始是蹲著間;腿實在麻得不行了,就跪著間;膝蓋疼得不行了,再蹲起來間,滾得渾身是土。有時我們去翻地,大家一字兒排開,一聲令下,個個爭先恐后挖過去,誰也不甘落后。一開始我還是挖一鍬直一下身,后來發現這樣很快就得被旁邊的同學落下,就再也不敢直腰了,汗水流到眼睛里也顧不上擦,心里下定了決心,只要不一頭栽倒,就絕不能被落下。當終于和旁邊的同學同時翻到地頭時,我擦著眼里的汗水,心里別提多高興了!干得最多的,是在玉米和大豆套種的地里鋤草。從玉米只有一拃高,一直鋤到沒過頭頂。我不僅學會了“前腿弓后腿蹬”,而且學會了換手鋤!就跟挑水會換肩一樣,是個挺了不起的技術。我可以一會兒左手放在前面,一會兒右手換到前面,鋤五六下邁一步,腳印疏密有致,那活兒漂亮著呢!我還學會在收工時用小石塊或瓦片把鋤頭上的泥土刮掉,讓鋤頭锃光瓦亮的,特別好使。
我們在農村并不單純就干點農活,還上文化課。尤其到了后期,學校越來越有經驗,學工學農已不是單純的體力勞動,而是開門辦學。1975年5月12日—6月28日在小馬村為期47天的開門辦學過程中,我們每天上兩節課,內容有語文、政治、物理、化學。早上6點起床,6:30—8點上課,8:20早飯,9—12:30下地干活,12:40午飯,下午3—7點勞動,晚飯后每周政治夜校一次、黨團活動一次。從6月24日開始實行半天勞動制,每天上午參加勞動,下午考試。
我們的課堂有時在麥田、稻田或糞堆旁。又高又黑又胖的數學彭老師在那里教我們拿著一人高的大圓規丈量土地、教授立體幾何,計算千粒重;在倉庫前的場地上,又矮又黃又瘦的化學王老師教我們用風化煤等原料按比例配制腐殖酸肥料;在氣象站,我們仔細觀察風向標、量雨器,觀看氣象員采集氣象數據和向天空施放乳白色氣象氣球的全過程;在大隊會議室里,我們進行政治學習。在我1975年5月13日、28日和30日三天的日記中分別記載了小馬大隊黨支部閆福作報告,小馬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閆根貴同志上黨課,小馬大隊團支部書記賈寶玲同志上團課,6月3日小馬村的王師傅還給我們講家史,憶苦思甜等內容。我還清楚記得,音樂李老師背著手風琴來教我們唱《河邊修起電灌站》。
在生活方面我們也受到了多種鍛煉。我們都是自己背著被包、提著洗漱用具和學習用具參加學農活動的。到村里后,被分配到農民家里住。有一年我們住得相對集中,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村里的水井打水。先用一根長木桿掛上水桶伸進井里,等水灌滿后把水拔上來,然后挑回去。路過一處男同學住的地方還要停下來高喊幾聲“到點了,起床吧!起床嘍!”聽到回應,再繼續往回走。回到院里把每一個同學的臉盆和牙缸里都倒滿水,再喊她們起床梳洗。有一年我們三個女同學住在一起。一天半夜,我突然又吐又瀉。身子單薄的張素英摸黑出去叫醒房東,又去村里請來大夫,再回去取藥、找開水,一連折騰了好幾趟。雖然畢業后我就沒有再見過她,但這份情意我永遠記在了心里。
我們的業余生活是豐富、愉快的。不上課的晚上,同學們圍坐在大炕上,有的打撲克,有的觀戰,有的鉤花,有的織毛衣,有的聊天。為了和村民聯歡,一幫女同學還排練了舞蹈《洗衣歌》,我在里面女扮男裝演炊事班長,為此還專門回市里借軍裝和圍裙跑了一趟。不夸張地說,那時的我們個個都是多面手,生活能力很強的。今天,我的同學們無論是在一線工地勞作還是在國外打拼,無論是在醫院行醫還是在學校任教,無論是在機關當干部還是商場打工,個個都是骨干,個個獨當一面。我們當中不乏博導、教授、主任編輯、商企精英和優秀管理人才。
現在似乎許多人對當年的學工學農或者叫開門辦學頗不以為然,可我覺得挺好。通過勞動不僅豐富了我們單調枯燥的課堂學習生活,調節放松了我們緊張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培養了我們團結協作、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鍛煉了我們的思想,磨練了我們的意志,強健了我們的體魄,尤其鍛煉了我們各種各樣的能力,成為一個全面健康發展的人!聯想到現在許多中學生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而他們將要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真是憂心忡忡。
好在中學要開設勞動技術課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毛主席他老人家當年高瞻遠矚提出的教育方針,在今天意義尤其重大。
田艷紅,武警太原指揮學院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