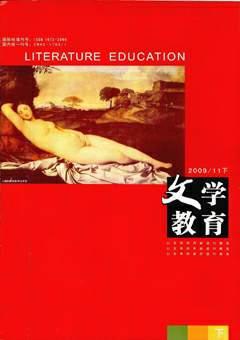疑惑影片《美麗人生》之美
影片《美麗人生》告訴人們,1939年人類正在開始經歷二次世界大戰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驚世駭俗的暴力運動。這是一場由法西斯發動的力圖剝奪其他民族自由生存空間、時常又表現為滅絕人性的種族滅絕傾向的游戲運動。希特勒在這里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不成熟的孩子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力玩具(坦克或更多)玩一場極不成熟的成人游戲。
希特勒,天真的以為依靠自己的粗暴武力可以永久征服這個世界,滅絕人寰的暴力是他游戲規則的核心,他沒有意識到當自己的過份貪婪污染到人類生存的每一個角落時,世界上所有可供反抗的可能與形態,都將被激發出來,到這份上他的滅亡似乎只能是一個遲早的必然宿命。
直至影片前五十分鐘,主人公基度在這場人生大游戲中將自己戲謔游戲姿態可謂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自稱王子;始終做著“意念決定一切的游戲”;自稱視學官在課堂上的橫加惡搞;闊步騎著野蠻人涂抹的“猶太馬”駛入酒店大廳將他人的未婚妻“公主”接走……
五十分鐘前基度的戲謔帶給我們的是愉悅,之后的畫面流動將我們拉入的是一場游戲背后的深沉壓抑之中。透過兒子祖舒華的兩個主觀鏡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基度前后兩次向兒子展示活力四射的“高抬腿”,均在一種被押送的呈現緊張的情境中彰顯:一則是走向市政局,預示一場悲劇的即將開始,在外婆開始認可女兒婚姻并給外孫過生日這一“喜”開始的同時,游戲的態度就有了荒涼的陪襯,成為隨后的影片敘述中不變的影片底色;另一則是被納粹士兵押往刑場,路過兒子所躲的鐵箱子時,再一次以高抬腿向兒子展示這場游戲中自己的游戲角色與本色。在這之前,父親還是作為實體的“生”而存在過。
或許出于這種人生態度的萌發,使得基度對于兒子的“謊”變得順理成章;或許由于納粹的極端恐怖與單純孩童世界的強烈對立,使得愛兒子的父親的“謊”無所不在。兒子在自己生日當天被捕,在押送車上天真地問父親基度:我們要到那里去?在與眾目睽睽的冷漠目光對比里,父親以一種嬉笑的表情與口吻,將此定義為一次很好玩的、不可輕易揭曉的、不為媽媽知曉的旅行。
到達集中營后,當以一場旅行來界定極端恐怖的地點即固定的集中營顯得不恰切的時候,基度改變之前的解釋:這是個游戲,是個游戲……我們一起玩,游戲必須守規則,男人一邊,女人一邊,還有軍人,他們主持游戲,很嚴厲,誰一犯錯,誰就要回家,也就是說,你要很小心,但你贏了,你就得到獎品——真正的坦克。
兒子:我已經有一架坦克了!
基度:這架是真的!
兒子:真的?
基度:真的,我本來不想揭曉的!
基度借這句話來貫穿自己定性旅行目的地不可揭曉的神秘感,更為了較好的保持謊言的延續性。坦克,是兒子祖舒華一出場就與之伴隨的、貫穿影片始終的道具:當外婆告訴祖舒華明天要給他一份生日大禮,祖舒華反問:是不是一個更大的坦克?當兒子嫌棄又臟又臭的集中營,想見媽媽的時候,基度拿坦克來搪塞他。
隨后,德國納粹軍官走進宿舍,需要一個翻譯來解釋營中規則,不懂德語的基度卻冒險自告奮勇走了上去。這是影片后半部分敘述中最精彩最滑稽荒誕的一幕,最叫人心潮酸動的蒙太奇段落。不懂德語的基度在繪聲繪色地翻譯著德國納粹長官的指令:“大家到齊了,現在游戲開始……”他是在假借“游戲主持者”的權威性,告訴兒子這確是一場游戲,來證明謊言的正當性,指出游戲有三種被淘汰的理由:哭,想媽媽,喊餓。所有的一切似是針對兒子的孩童世界的。然而,兒子從其他孩子那里得知他們并不懂得規則,他們不認可頭獎是坦克,也不懂積分。基度辯解:其它孩子太狡猾,不要相信他們,不可能沒有坦克。
洗澡事件過后的游戲規則對于孩子變成了躲藏,“讓人人以為你失蹤,人人以為沒有你這個人。”此時,在這座納粹集中營,能夠與希特勒的游戲規則進行抗衡的或許只剩下祖舒華這個孩子所因循的天真,他倔強地堅持不去洗澡,相信游戲,幻想坦克,只有他才留下了最后的一絲純真。
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游戲規則同樣是建立在坦克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坦克的支撐,謊言無從建構,游戲更免談規則,我們天真的孩子又怎能如此堅持?孩子再次執意要走,基度只好以順從的假像,旁敲側擊兒子:我們在領先,早已經告訴你,但你要退出,只好退出,我昨天才看過積分表,(對獄友巴圖)我們要走了,我們討厭這地方,坦克已經造成,抹干凈火嘴才開車,記得拉開油門,否則大炮會卡住輪帶,還有那支機槍,多么精致,開車前記得松剎掣,我和他要走了,祖舒華要退出,本來駛著坦克走,現在要坐巴士,我和祖舒華走了,大家再見。我們討厭這地方,(對遲疑不走的兒子)走吧,否則趕不上巴士,走吧,祖舒華!
祖舒華:我怕給雨淋濕,發高燒!
坦克,始終貫穿全片,是祖舒華的精神支柱,成為支持謊言的最強音。納粹鐵蹄狼狽逃竄后,孩子面前果真出現了一輛貨真價實的坦克,謊言從此變得不那么純粹。
影片到此,我想,若沒有真坦克的出現,孩子美好幻想或許將被徹底擊碎。這不出現的電影敘述拍攝本身,謊言的最終幻滅,納粹營恐怖電影場景設置,是不是都有可能在兒童演員的心靈成長歷程中留下陰影?
坦克最終呈現在了孩子眼前,這看似完美卻使我內心疑惑的燃燒則更為猛烈了。使謊言不再純粹的正是此前謊言的純粹性的延續,純粹性謊言卻并不因此停止自身的延續:
祖舒華:我們贏了!
母親:是的,我們贏了!
祖舒華:一千分,好開心啊!我們得到冠軍!坐坦克回家!
母親和祖舒華相擁的姿勢共同構成一個V(victory)的畫面造型,伴著母子倆甜蜜的笑容,爽朗的笑聲,最后“勝利”的表達在此刻最終定格。
母子笑到最后、勝利到最后,均是以建立在謊言之上為基石的。在這整場游戲中,謊言建立在坦克之上,孩子則要躲藏,需要沉默,需要靠坦克建立謊言,建立起孩子心中的坦克,心中的夢想,支撐著他走向最后的勝利。
謊言,即使是善意的謊言,說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世界的殘忍被迫只能以一種謊言的形式去遮蓋它惡的一面,又該是誰的過錯。
我們最終戰勝納粹,卻只能以暴力抵抗暴力,是以孩子幻想著的暴力(坦克的)出現這一事實的最終實現為終點的。
這是一個快樂的傳說?美麗人生?
“叫人不可思議”。可誰又能否認正是由于孩子對于坦克的依戀,對于暴力武器的崇拜,才使得自己的生命得以拯救……
秦洪亮,男,湖南科技大學文學系2008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