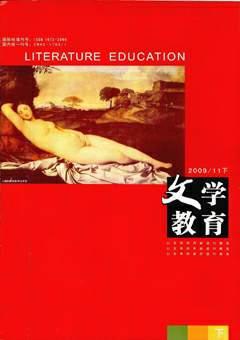《紅字》中海絲特.白蘭的倫理蘊涵
陳 了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作為美國19世紀影響最大的浪漫主義小說家,他的代表作《紅字》以主題思想深遂、想象豐富、寫作手法獨特而標志著美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被奉為美國文學經(jīng)典。就主題而言,《紅字》既是一部愛情悲劇,更是一部道德悲劇,作品中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主人公海絲特身上蘊含著明顯的清教倫理傾向的道德評判。下面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對主人公海絲特·白蘭的人物形象進行分析,從而對《紅字》的倫理內涵進行深入挖掘。
一.尊嚴的維護
海絲特的形象深入人心,作為一個堅強的女性,她具有一個抗爭的人生經(jīng)歷。海絲特珍視個人幸福,堅信自己的追求,為此,她抗爭,不惜單獨同那個社會的宗教與道德習俗作戰(zhàn)。雖然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斗爭,但她無所畏懼,決不退縮。在她的內心深處,對狹隘的宗教及道德習俗的偏見是蔑視的。
“紅字”本是恥辱的標志,但她卻精心地把它繡得金光燦爛,如一件精美的藝術品。“這個字以細紅布作底,四面圍以精美的刺繡和奇特的金線花邊,是煞費苦心、用無比豐富瑰麗的想象制作出來的……堪稱華美絕倫。”[1]小珠兒是她“罪惡”的結晶,她卻把女兒打扮得像個小天使似的,讓她在無憂無慮、無拘無束中自由地成長。在示眾臺上接受審判時,面對法官和民眾,她表情坦然;面對眾人要她供出自己孩子的父親的逼問,她斬釘截鐵地回絕:“決不說!”在判決后的歲月里,無論走在大街上,還是到別人家里去做女紅,她的衣服上總別著那個鮮紅的“A”字,坦坦然然,從不畏縮,從不以別人的躲避和沉默相向為意。蔑視教規(guī)的海斯特·白蘭表現(xiàn)出頑強的反叛精神,大膽的面對來自于社會、教會的羞辱和迫害。當她從獄中邁步到觀眾面前時,人們驚奇的發(fā)現(xiàn)她不但沒有在“災難的云霧中黯然失色”,反而閃現(xiàn)出非常美麗的光。她的臉上現(xiàn)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從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裝是十分華美的,就連那象征恥辱的紅字,都繡得異常的精美。在她心中,她的道德善惡觀與傳統(tǒng)教會灌輸?shù)氖清娜幌喈惖?與其說她堅強樂觀地生活,倒不如說她自從在恥辱柱戴上A字的懲處之后,便不再把教會和世俗價值觀放在心上。她在厄運面前表現(xiàn)出來的尊嚴,在教權壓抑下展示出來的人性力量使她的人格不斷上升,她改變了那紅A字在人們心中的恥辱含義,那紅A字發(fā)出了超凡脫俗的光芒,成了她行善積德美好人格品德的標志。她成了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能干的”人,成了善良的神的“天使”,成了“令人尊敬的”先知者。她還汲取了“比紅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惡還要致命”的精神,把矛頭指向了“與古代準則密切相關的古代偏見的完整體系——這是那些王室貴胄真正的藏身之地”,稱得起是一位向愚昧的傳統(tǒng)宣戰(zhàn)的斗士了。
霍桑用濃郁的筆墨將海斯特的反抗精神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出場到結局,她的反抗精神一直如生命之泉貫穿著整部作品。她形式上雖然接受佩帶紅色A字的懲罰,但在思想上卻沒有接受懲罰她的那些社會道德規(guī)范。
二.愛情的執(zhí)著
海絲特的愛情核心精神就是勇敢追求,永不屈服,決不向世俗妥協(xié)。盡管這種愛不受法律和宗教的保護,被人們視為罪惡,但她卻在她自己愛的世界里獨自做著愛情的享受,執(zhí)著地愛著。
愛情本是人類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義,亞當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園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歡女愛,不再靠上帝創(chuàng)造而由自己繁衍人類,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觸犯了基督教的第七戒。霍桑雖深受教會影響,但自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愛情早已成了文藝作品永恒的主題,時時受到歌頌,他即使再保守,也會認為是天經(jīng)地義的。海絲特是勇敢追求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的先鋒,海絲特對齊靈渥斯坦言,“我沒有感受到愛情,我也不想裝假”。黑格爾講過:“愛情在女子身上顯得最美,因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現(xiàn)實生活都集中在愛情里,她只有在愛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愛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會像一道火焰被第一陣風吹熄掉。”[2]在婚姻中從沒有嘗試過愛情的海絲特·白蘭內心有著大膽狂放的渴望,她敢于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愛的權利和力量,認為她與齊靈渥斯的婚姻是“一種錯誤而不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愛情的獻祭。她的“含苞的青春”幾乎被埋葬在這不合理的婚姻中。為了盡可能避免這種生命的難堪,獲得新的生命意義,海絲特掙脫了清教教義的一切束縛,聽從人類生命本性的呼喚,她勇敢地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溫文爾雅、一表人才的青年教士丁梅斯代爾,并與之有了愛情的結晶——珠兒,為此她犯了“原罪”,觸犯了清教條里“十禁”之一的“通奸”。事情敗露后,她被迫終身佩戴紅字,為了愛人的名聲,她獨自承擔了全部罪責與恥辱。即使是在七年后,當她看到情人丁梅斯代爾被內外的力量折磨得幾近崩潰時,在牧師外出布道返回的路上,在人跡罕至的密林深處,她仍然敢于與牧師幽會,把自己丈夫的詭計告訴他,并勸說牧師帶著自己和女兒離開這個充滿謬誤與偏見的地方,去創(chuàng)造新的生活。也正是出于對他的眷戀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遠離他所在的教區(qū),就是在他死后,仍然放棄了與女兒共享天倫之樂的優(yōu)越生活,重返埋有他尸骨的故地,重新戴上紅字,直到死后葬在他身邊,以便永遠守護、偎依著他。在她身上充分的體現(xiàn)出了“愛情”力量之大,死亡也無法戰(zhàn)勝。
三.“罪”的救贖
在霍桑看來,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為發(fā)生后個人對待罪惡的不同態(tài)度以及在他們心靈上所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在《紅字》中,體現(xiàn)在對人性罪惡的深入挖掘上,也體現(xiàn)在內心的懺悔與行為的過失獲得救贖的信仰原則上。
基督教教義中強調信救贖,認為人類因有原罪和本罪而無法自救,要靠上帝派遣其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做犧牲,作了人類償還上帝的債項,從而拯救了全人類。海絲特的救贖,或者說她相對于其他兩個男主角更早獲得的內心安寧和自由,是來自她對罪的公開與結果的直面和承擔。獄中的經(jīng)歷,刑臺的示眾,社會的拋棄,胸前的“A”字,以及珠兒作為“A”字的活的見證,如此“眾目昭彰”的刑罰倒成為她的某種“庇護”,因為她已無所隱匿,也就無所喪失。直至后來,彰顯羞辱的紅字甚至“含有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給予佩戴的人一種神圣性,使她得以安度一切危難”,并賦予她一種遺世獨立的自由,一種洞察人性的能力,一種體恤眾生的胸懷。她依從內心真實的情感和本能,追求脫離習俗羈絆的個體自由,并在離群索居中堅忍不拔。她堅信自己與丁梅斯代爾的結合是出于內心真摯的激情;此后在獨自擔當羞辱、絕不供出情人,并含辛茹苦養(yǎng)育女兒珠兒的漫長歲月中,更印證了其愛情的堅貞不渝和對生命強烈的責任心。這一切使她有充分理由相信她所做的“有它自身的神圣性”。人人都是有罪的,通過救贖來達到一種精神的超脫。
海絲特·白蘭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彌補自己的過失,以至于許多婦女向她傾訴自己內心的秘密,尋求安慰和忠告。清教主義者認為,人擁有一種趨向于德性的自然傾向,不過,只有通過了某種‘訓練,人們才可能達到德性的完美。海斯特·白蘭正是通過這種“訓練”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彌補所犯下的罪,“最終凈化了她的靈魂”。紅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恥辱火印,而是激勵精神復活的標志和象征。
從一開始的“她煥發(fā)的美麗,竟把籠盡著她的不幸和恥辱凝成一輪光環(huán)”,令人聯(lián)想起“圣母的形象”。到后來“并造就出一個比她失去的更純潔,更神圣的靈魂”海絲特身上還體現(xiàn)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于罪人原型的人物原型形象—圣母原型。早在海絲特站在刑臺上為通奸罪而接受懲罰時,霍桑就寫道:“在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這個美麗的婦人,她那美麗如畫的服飾和神采,以及她懷中的嬰孩,自然地會想起圣母的形象,即那個令無數(shù)杰出的畫家競相表現(xiàn)的形象;確實,這個形象只有通過對比才能使人想起的,想起那個懷抱為世人贖罪嬰孩的圣潔清白的母親。”不僅如此,她的經(jīng)歷也頗似《圣經(jīng)》中的圣徒:帶著上帝的使命,受盡人間磨難,正如圣徒保羅說:“在我看來,上帝把最壞的位置留給了我們這些使徒……我們遭辱罵時祈禱;受迫害時忍受;受侮辱時以好言回報。”自從戴上紅字,海絲特·白蘭的生活便如同信基督的信徒一般,忍辱負重行善積德,最終用善行和仁愛感化了眾人。海絲特·白蘭因背負上紅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而得到拯救,并在一定意義上拯救了眾人。在這里,當一切罪洗盡,海絲特·白蘭也就成了因世人的罪過而受難的圣母瑪麗亞式的女人。
陳了,女,湖北咸寧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武漢大學2009年文學專業(yè)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