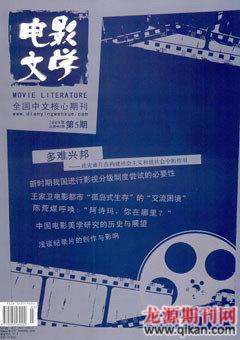一曲女性自我解放運動的悲歌
歐陽欽
摘要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壇的二顆璀璨巨星,錢鐘書與張愛玲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諸多鮮活的女性形象。巧合的是,二位大家在其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著力塑造了眾多幾乎是同一時代的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筆者擬通過對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比較分析,體驗40年代中國知識女性的生存狀態,進而深入探討女性悲劇命運的根源。
關鍵詞自我解放運動,悲歌,女性形象,原罪意識
作為中國當代的國學大師,錢鐘書先生一生博學多才,著述頗多,尤其在散文創作中更是別具一格。但其小說創作領域,卻僅有《圍城》這一部長篇小說和《貓》《紀念》兩個短篇小說,然而就憑這幾部作品,錢先生就已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小說大家地位。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異數”,張愛玲在小說創作的園地上碩果累累,《封鎖》《金鎖記》《傾城之戀》《色戒》等,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巧合的是,二位大家在其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著力塑造了眾多幾乎是同一時代的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筆者擬通過對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比較分析,體驗40年代中國知識女性的生存狀態,進而深入探討女性悲劇命運的根源。
一、共性分析
1都背負“圍城”的重負,幾乎沒有一個能夠走出婚姻的城堡
“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圍城”于讀者而言是一個具有很大解讀空間的詞語,錢先生借西方的典故所暗示的寓意,將之置換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圍城”意象,益發凸顯了出入其中的艱難,同時也反襯了人們沖決出“圍城”的強烈欲望。
兩位作家筆下的知識女性多處于多重圍城之中,處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她們接受過較新式的教育,因而她們挑戰男權社會,改變現狀的自覺要求就更為迫切,這也就注定了她們的悲劇色彩的更加強烈。
蘇文紈,這位心氣頗高的才女曾一心想將方鴻漸圍捕進自己構筑的“圍城”,但未獲成功。遂而投入了詩人曹文郎的“圍城”,孫柔嘉算是成功地從“城”外擠入“城里”的女性,可最終也只能作繭自縛地將自己困入“圍城”之中而不自知,《貓》中風光、美麗,長久享受著男人眾星捧月般恭維的愛默,更是心甘情愿地沉溺于“圍城”之中而長眠不起,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個丈夫少不得,仿佛阿拉伯數碼的零號,雖然本身毫無價值,但沒有它十百千萬都不能成立”,《紀念》中的曼倩,在情人逝去后努力維持著她的“圍城”,她與天健“兩個人的秘密”是她身心的一次秘密突圍后留給她賞玩不已的精神財富,憑著這一塵封心底的財富和還未失去苗條輪廓的資本,女主人公期待著再一次突圍,《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為“被女人捧壞,從此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的范柳原的財富和地位吸引,終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香港的淪陷,心甘情愿、如愿以償地擠進了范的“圍城”中。
相比之下,《霸王別姬》中的虞姬則更是將這“突圍”的行為推向了極致。在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始終只是英雄高亢呼嘯的回音中的一個微弱顫音后,當漢軍已經圍攻上來后,在項羽一再要求她隨同突圍時,虞姬做出了一個出乎意料的舉動——拔刀刺進自己的胸膛,同時留下了謎一樣的話:“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收梢。”
張愛玲借這一歷史形象概況那個時代具有新思想、要求獨立的女性的普遍困惑:既意識到自己對男人的依附,又洞悉到這種依附后面的空虛。在這兩難的苦苦掙扎中,艱難地探索著突“圍”的道路。
2都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艱難
女性生存的艱難是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恒的話題,在中國這個封建舊思想蒂固根深,男尊女卑觀念深入人心的國度里,這個問題越發突出。知識女性們雖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所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封建觀念的捆綁,并為改變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而竭力抗爭,但卻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在社會中從屬、附庸的角色定位。
張愛玲的小說《封鎖》中有這樣一句反復出現的民謠“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雖說她小說中的女性并沒有真正落到沒錢過日子的地步,但作為一種存在的恐慌卻一直如影隨形地威脅著她們,因此,她們大多處于兩種生存狀態之中:一是急于成為有錢人的太太甚至是情婦,二是一旦達到目標后,又不自覺地為維護和改善已有的地位而費盡心機。”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為讀書投靠了一個給闊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為能事的姑媽,從此以后她逐漸成為了姑媽勾引男人的誘餌。雖然,她也有過追求新生活的念頭,并斬釘截鐵地宣稱要回去,而且買好了船票收拾好了東西,可臨行前的一場病卻使她懷疑冥冥中是否有什么東西讓自己留下來,于是她還是留下了,留在了那個明知可怕的“鬼氣森森的世界”里。于是。一個單純、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墮落到幻想貶值、自信破滅終至人格的喪失的風塵女子,這一痛苦的蛻變經歷將女性生存的艱難和盤托出。
相比之下,錢鐘書先生筆下的知識女性則更多地從精神層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艱難。在他的小說中,女主人公不必像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一樣為生存而出賣自己的肉體甚至是靈魂,但卻始終難以改變她們在社會中從屬、附庸的地位。蘇文紈婚姻落敗后委身于能寫幾句歪詩的曹元郎,最終只能通過走“單幫”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心氣極高的汪太太雖做了一次大膽的突“圍”行動,但在銀樣蠟槍頭趙辛楣的退縮后又投入到三閭大學的“一潭死水”之中。
轟轟烈烈的奮斗,抗爭就這樣以各種方式——或悲劇,或喜劇,或鬧劇——偃旗息鼓,“戰場”上的硝煙尚未散盡,張愛玲與錢鐘書筆下的蘇文紈們已在“圍城”內外領受了由男人們分配的角色,宿命難逃。
二、個性比較
1知識女性思想意識比較
與張愛玲筆下的知識女性相比,錢先生作品中的知識女性思想意識更為激進,因而在女性自我解放運動的征途上也就走得更遠。在分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時我們不難發現,在女人所承受的所有壓力中,生計問題被迫切地擺在第一位。在這一前提下,婚姻成了生活的保障,戀愛不過是得到保障的手段,她們所表現出的對金錢物質的迷戀和不能自拔使讀者們感嘆不已:粱太太、葛薇龍、教風、霓喜,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七巧,我們不知道她進入姜家之前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激斗,然而終于嫁給了姜家的癆病二少爺。這樁買賣雖然表彰了七巧的生存,卻注定了她要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七巧情欲受阻后,轉而擁抱物欲,然后以近乎殘酷的報復,從中獲得壓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
經濟上的不能獨立,導致其人格、心理上、感情上均有強烈的依附感和壓抑感。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均是男人和自己各種欲望的奴隸,這類人盡管都有著潑辣的生命力,但她們的地位卻始終無法確定,疑慮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了自私者。葛薇龍為求生存得輕松些,在一次次的誘惑中,不知不覺地墮落·《傾城之戀》中的自流蘇。為了擺脫寄宿娘家遭人白眼的處境,鉆頭覓縫要尋找一個安全歸宿,《連環套》中的霓喜,一次次與人姘居,卻最終
遭到拋棄。
相形之下,錢先生筆下的知識女性則要幸運得多,她們有著較殷實的家庭背景,且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于是,在擺脫了生計問題的困囿后,在婚姻問題上她們更多地表現自我價值觀的實現,而非謀生的手段。于是,淡薄了門當戶對觀念的她們,在愛情游戲中設立自己的游戲規則,主動出擊,甚至為將男人玩于股掌之中而神采奕奕,風姿瀟灑。
對于《圍城》中蘇文紈的走“單幫”,許多人覺得是蘇文紈的財迷心竅。但依筆者看來,恰恰相反,這是她不甘心做一個平庸的家庭婦女,她要做點什么,以驗證自己的獨立意識及駕駛命運的能力的一種表現。有心計,善經營的孫柔嘉,大學畢業后積極到三閭大學求職,并以自己的智慧將方鴻漸縛入“圍城”成就了自己的婚姻,貓一樣在家苦心經營女性王國的愛默,在沙龍里接待著社會各界的茶客,接受各界名流的膜拜。
錢先生筆下所有這些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知識女性,在擺脫了生存的危機后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了比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更為激進的行動,而這激進的思想和行動的背后,則是這些知識女性們不甘心在男權社會中受附庸、陪襯、邊緣角色的積極抗爭,雖然這樣的抗爭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女性爭取平等地位的另一個極端,但作為一種有意義的嘗試,其進步意義卻難以抹殺。
2對舊時代對女性的扼殺及戕害比較
與錢鐘書筆下的知識女性相比,張愛玲筆下的知識女性更深刻、更本真地暴露出舊時代對女性的扼殺及舊思想對女性的殘酷戕害。在張愛玲23歲時(1943年),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學說作為影響整個人類的一種文化哲學在中國內地得到廣泛的傳播。張愛玲自然也接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她運用弗洛伊德學說對人的心理,特別是變態心理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被娘家人賣給姜家作了二房“奶奶”,而陪伴她的卻是一個“沒有半點人氣”“沒有生命”的肉體。強烈的性欲望,使她的窺淫欲與施虐欲瘋狂地增長。在泯滅自己希望的同時,也扼殺了周遭人的希望:兒子房中“秘聞”,被她在牌桌上“略加渲染,越發有聲有色”地散布,把一丫鬟給長白做小,導致其被折磨至死,姨太太吞鴉片而亡。千方百計阻止女兒戀愛,惡毒地設計圈套,斷送了女兒長安的婚事……如此種種使其墮落到萬劫不復之境。其手段之低下,心底之陰暗,極盡讓人心驚膽戰。
弗洛伊德曾打過一個比喻:本我是匹馬,自我是騎手。曹七巧正是一匹失控的馬,她的生活愿望被壓抑后的極端病態心理所帶來的變態行動,是一種沒有分寸的瘋狂。弗洛伊德認為:人有死的本能,死的本能主要表現為求生的欲望,當它向外表現的時候,它是仇恨的動機,成為侵犯、破壞、征服的動力。如此可見,曹七巧的變態心理即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內部挫折剝奪所引起的一種非常規的滿足。越是受到壓抑,就越是拐彎抹角地尋找出路,尋找發泄,直至人格扭曲。
透過曹七巧人性背后,作品中分明展現給讀者一幅蒼涼可怖的人生圖景。曹七巧何以由一個女人而成為女奴,由女奴而成為女畸人、女虐待狂,其中內在的原因,即這種變態心理的背后,則是中國舊式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識”。在這種意識的驅動下,七巧身上多的是受壓抑。少抗爭。因此,小說中對于由其兄長一手安排的婚事,從沒寫七巧的竭力反對,而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她的害人與被害,從而以曹七巧這個最徹底的承受了所有舊時代婦女的不幸,最徹底的承受了舊時代婦女的心理重負的個性形象概況了舊時代女性的共性特征。
七巧內心的“原罪意識”被作者展示得淋漓盡致。張愛玲掀開了曹七巧心獄充滿瘡痍的一頁,描述了曹七巧蒼涼的一生,冷靜而深刻地展示她的人性泯滅的過程。
相比之下,錢鐘書筆下的知識女性則更多地在一個平面上“咀嚼”舊傳統思想重負下人性的弱點,如蘇文紈高傲自負、孫柔嘉的巧于心計、愛默虛榮高貴、曼倩的精致哀怨,雖被展示得淋漓盡致,而對于人性弱點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人物形象卻未能做進一步深度的開掘。
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為何如此之艱難,這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玄機”?
三、知識女性自我解放悲劇命運的根源
首先讓我們粗略地回顧一下新文化運動后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在“男女平等”口號指引下,中國的一批有著先鋒思想的知識分子從根本上否定禁錮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的男權至上的觀念,并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婦女的切實行動:如廢纏足,興女學,反對包辦買賣婚姻,出現了職業女性等等這些變革對于封建傳統的否定是相當激烈的,對于打破封建制度對女性的壓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在張愛玲的筆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卻仍在男權的社會的“圍城”中無法自拔,而錢鐘書筆下的知識女性卻開始邁起了走出“圍城”的第一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她們之間的差異呢?很明顯,經濟上的獨立是后者能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的一個關鍵原因。而伴隨經濟獨立的是思想上的自立,思想上的自立帶來的是行動上的更加激進,激進的行動帶來的是經濟上的更加獨立。
美國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前驅馬斯洛在人的“需要層次”論中處在最底層、也是最基礎的一層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張愛玲筆下的知識女性們為著生存不惜一切代價透支著一切可以透支的資本,又焉能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而錢鐘書筆下的知識女性們,在程度不同地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后,都在為實現自我的某種需要而苦心經營著。這里需特別強調的是《圍城》中蘇文紈的走“單幫”,論者對此普遍挖掘不深或嗤之以鼻,但在筆者看來,這恰恰體現出了這位在婚姻和職業上特立獨行的女才子的一種抗爭,一種自我實現以證明自身存在的一種抗爭,其做法雖有點與其身份不符,但在思想上卻邁上了與舊時代“賢妻良母”的思維定式分道揚鑣的人生道路。
遺憾的是,錢鐘書筆下的知識女性在即將邁出“圍城”的腳步后便戛然而止,這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而這一切卻都源于自身在中國這個封建舊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里特有的、與生俱來的女性弱點——對男權的依附,一種跨越了傳統的物質條件依附后一種更高層次的依附——精神依附。
透過婚后孫小姐加之于方鴻漸的種種折磨,我們不難體察得出這種精神依附背后的女性的心酸,她對方鴻漸的所作所為,絕不是想逼他走,而是想鎮住他。征服他。只有如此,她才覺得安全又放心,不然一旦丈夫負心,婚姻破裂,對方鴻漸是一種解脫,對孫柔嘉則是一場災難。
由此我們從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時不難發現,這些悲劇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她們為自己打造的,而要改變這種尷尬的處境絕非一日之功,在取得獨立的經濟地位后清除內心深處女性的“原罪意思”將更迫在眉睫和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