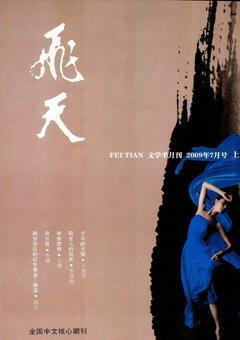《老人集合》敘述手法評析
2009-03-15 10:16:14魯莉郝明星
飛天
2009年16期
魯 莉 郝明星
歐內斯特·蓋恩斯是當代美國繼福克納之后最有影響的南方小說家之一。身為非主流的非裔作家,他的作品卻躋身美國大學必讀書目。他曾獲得美國政府終身文化成就獎、全美人文科學獎章等多項殊榮,其作品也贏得了包括美國全國書評家協會的“最佳小說獎”等在內的數十項獎勵。我國美國黑人文學研究專家稱之為(20世紀美國)“黑人文學大發展的最后三十年里尋求創新突破的黑人男作家”之一。蓋恩斯以“填補美國主流歷史學中有關黑人歷史的空缺和糾正歷史書中有關黑人歷史的誤載為己任”,他要“描畫出自己種族的真實面貌,以糾正某些美國白人作家多年來對自己種族有意或無意的歪曲”。其作品表達了對于民族和黑人文化的真摯情感以及他對美國種族問題的思考。他發表于1983的作品《老人集合》集中體現了其通過嫻熟的寫作技巧實現寫作意圖的努力。
一、故事梗概
《老人集合》所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路易斯安那州邊遠小鎮的一個農場中。農場主的侄女坎迪發現白人男子博被槍殺在老黑人馬蘇家院中。為了保護被她認為是兇手的馬蘇,她召集一幫黑人老頭帶著槍和空彈殼到馬蘇家院子集合。當警長梅普斯趕到后,坎迪和十幾名老人都聲稱自己是兇手,并力陳各自的動機和原因。無奈之下,警長只好先派警察去博家,以免其家族來報復尋仇,造成更多無辜傷亡。現場所有人都認為馬蘇是兇手,因為幾十年來只有他敢應對白人的挑釁。……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