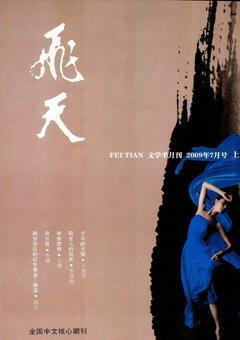隨物賦形 善利萬物
2009-03-15 10:16:14徐宏勛
飛天
2009年16期
“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這是蘇軾治平三年(1066年)所作《屈原廟賦》中的句子,竟如讖言一般,成為他自己31年后遠謫海南儋州時的寫照。紹圣四年(1097年)春,在惠州貶所的蘇軾寫了一首題為《縱筆》的詩:“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好,道人輕打五更鐘。”原本苦中作樂的小詩不意竟招來政敵的詬病,宰相章惇對蘇軾的“尚快活”甚為不悅,當年,一紙“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將62歲的蘇軾拋向遙遠的蠻荒之地。所幸屈原自投汩羅的結局并未成為蘇軾的選擇,相反地,這場磨難讓他的生命又多了一抹傳奇,一筆華彩。考察蘇軾儋州三年的生活軌跡,則發現其與“水”的意象有著許多契合之處。
一、隨物賦形,絕境求生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蘇軾《自評文》)。
水最外顯的特征便是能隨物賦形,能適應各種地形及環境,平溝越坎、滴隙掛崖,迂回曲折,無處不可存身;遇方則為方,遇圓則為圓,無處不可完滿。“隨物賦形”既是蘇軾作文之道,同時也是其處世之道,順境時濟世救民,絕境中樂觀求生。
蘇軾仕途頂峰時曾為翰林學士,官居吏部尚書、禮部尚書,但是因為被卷入黨爭,晚年屢遭貶謫,儋州之貶則堪稱絕境。一者,儋州瘴癘橫行,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都極為惡劣,對生長于中原富庶之鄉的官員來說,無異是生命的絕境;二者,儋州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文明程度遠不及中原,加之交通不便帶來交流的障礙,被貶官員將面對精神上的絕境;三者,儋州遠離內陸,也遠離了“君恩”,是仕途的絕境。……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