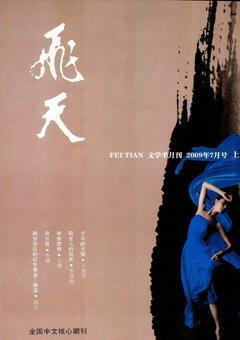《邊城》與《大淖記事》中女性形象表現的對比分析
2009-03-15 10:16:14谷雨周婧婷
飛天
2009年16期
關鍵詞:愛情
谷 雨 周婧婷
翠翠與巧云是沈從文《邊城》和汪曾祺《大淖記事》中著墨表現的典型女性形象,作者都給她們設置了不可抗拒的人生際遇,但奏響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命運交響曲。盡管從敘事結構來看,《邊城》與《大淖記事》有著相似的模式和格調,但又因沈從文和汪曾祺各自創作心境和美學追求的不同,所描寫的地理區域性和民族差異性顯著,從而在外觀上顯現了完全不同的瑰麗奇彩。
一、敘事基調的“悲哀”與“歡愉”
一位是文體出眾的“多產”老師,一位是“早熟晚成”的衣缽弟子。在鄉土愛情的記敘中,盡管均有傳統愛情模式的痕跡,但卻不難感受到兩位作者在敘述人物命運時“悲哀”和“歡愉”的基調。《邊城》采用了全知敘事[1],父母的愛情厄運一開始就埋伏在翠翠的故事里,祖父時常會體察到這樣的悲劇,但他愿意用自己的努力來換取更美好的結果。然而敘述者卻全知全能,不僅是兩兄弟都對翠翠心有所屬卻彼此不了解對方意圖,而且翠翠對于碾坊陪嫁的女子抱有些許醋意但裝作若無其事,哥哥失愛而喪命,弟弟親情愛情難調而出走。翠翠的命運就是在每個峰回路轉時都下降一次,直至像望夫石一般立在水邊等待那個外出的心上人: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也不會回來。
巧云的命運卻是在限制敘事中一步步展開[1],雖然每一次打擊都讓讀者為巧云的遭遇嘆一口氣,但這個堅強的女子表現出來的卻是少有的“果敢”與“執著”:她拒絕妥協,也壓制卑怯,大膽地“約”了相愛的人,在愛人被打傷后勇敢地擔負照顧他和殘廢爹的重任。……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戀愛婚姻家庭(2021年17期)2021-07-16 07:19:34
海峽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 07:49:1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文苑(2018年23期)2018-12-14 01:06:28
金橋(2018年9期)2018-09-25 02:53:32
小說月刊(2014年1期)2014-04-23 09:00:03
延河(下半月)(2014年3期)2014-02-28 21: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