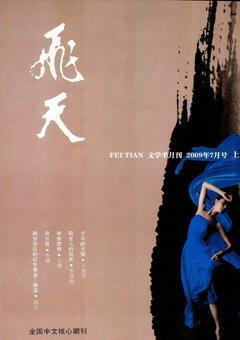誤讀與誤讀的意義
韓 笑
一、以讀者為中心的理論建構(gòu)
20世紀(jì)60年代以后,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重點(diǎn)轉(zhuǎn)向了讀者接受研究,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聯(lián)邦德國康斯坦茨學(xué)派是接受美學(xué)的肇始者。繼康斯坦茨學(xué)派之后,70年代在美國出現(xiàn)了以讀者接受為研究對(duì)象的批評(píng)流派,也就是讀者反應(yīng)批評(píng)學(xué)派。美國的“讀者反應(yīng)批評(píng)”和康斯坦茨學(xué)派相比,更注重的是讀者的主觀活動(dòng)。其代表人物費(fèi)什、霍蘭德從接受的不同角度論述了讀者在文學(xué)活動(dòng)中的決定性地位。
但是,即使將關(guān)注點(diǎn)都放在讀者方面的接受美學(xué)各家,他們的理論還是存在著很大分歧。作為接受美學(xué)的代表人物,姚斯在《文學(xué)史作為向文學(xué)理論的挑戰(zhàn)》中,提出了“期待視野”概念。他說:“從類型的先在理解,從已經(jīng)熟識(shí)作品的形式與主題,從詩歌語言和實(shí)踐語言的對(duì)立中產(chǎn)生了期待的系統(tǒng)。如果在對(duì)象化的期待系統(tǒng)中描述一部作品的接受和影響的話,那么,在每一部作品出現(xiàn)的歷史瞬間,讀者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分析就避免了心理學(xué)的可怕陷阱。”他將“期待視野”分為兩大形態(tài):其一是在既往的審美經(jīng)驗(yàn)(對(duì)文學(xué)作品主題、風(fēng)格和語言的閱讀經(jīng)驗(yàn)),接受者的知識(shí)背景基礎(chǔ)上形成的較為固定的文學(xué)期待視野;其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對(duì)社會(huì)、歷史、人生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上形成的更為廣闊的生活期待視野,這兩大視野相互交融構(gòu)成具體閱讀視野。而接受美學(xué)的另一名奠基人伊瑟爾則認(rèn)為,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文本在其意象結(jié)構(gòu)中總是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和“意義空白”,從而形成一種潛在的“召喚結(jié)構(gòu)”,促使接受者根據(jù)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yàn)、審美理想等去將其確認(rèn)、補(bǔ)充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