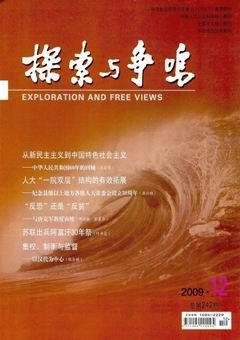當代家族小說創作的模式化傾向
內容摘要 在當代小說創作格局中,家族小說創作取得了可喜的收獲,但這些風格不同的敘事作品卻呈現出驚人的相似之處,人物性格的類型、情節故事的原型、結構形式的設置、敘述方式的創造均表現出較多的模式化傾向。這既是不同作家對同一母題原型創造性的誤讀,也是作家難以擺脫的藝術局限,自然也昭示出作家原創性的匱乏。
關 鍵 詞 家族小說 母題原型 模式化 原創性 藝術局限
作 者 曹書文,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河南新鄉:453007)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家族小說創作取得了可喜的收獲,出現了《紅旗譜》、《古船》、《白鹿原》等史詩性作品。但作為家族母題書寫的藝術形式,由于文學傳統、文化語境、生活經驗等的相似乃至相同,這些風格不同的家族小說呈現出驚人的相似之處。無論是人物性格的類型、情節故事的原型、結構模式的設置還是敘述方式的創造都表現出較多雷同化的痕跡,這在一定意義上昭示出當代作家藝術創新能力的欠缺與審美經驗的匱乏。
一
從1950年代的《紅旗譜》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當代家族小說給讀者創造出了一批較有思想深度與藝術力度的藝術典型,形成了舊家庭的封建家長、叛逆知識分子、農民革命者、淳樸善良的賢妻良母等形象系列,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思想內涵與迥異的個性風采代表了當代小說人物創造的藝術水準,尤其是對封建家長性格復雜性的揭示、叛逆知識分子矛盾的情感和心路歷程的刻畫、對農民革命者革命的積極性與狹隘性的審視以及對傳統母性人格悲劇性的書寫,共同構成了一道亮麗的藝術風景。
如果說在1950—1970年代的家族母題小說創作中,作家對封建家長性格的塑造聚焦于其思想的反動、道德的墮落、形象的卑微,突出其人情、人性、人格中的負面因素,造成一定程度上對反面人物形象刻畫上的臉譜化傾向,那么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藝術創作借鑒視野的開闊、思想的解放、主體意識的張揚都為家族小說創作提供了一個適宜的文化土壤,當代家族小說創作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自然,對封建家長形象的創造也開始走向新的超越。《白鹿原》中的族長白嘉軒、《第二十幕》中的家長尚達志、《古船》中民族資本家的代表隋秉德等成為成功的藝術典型,不少人對其思想性格刻畫上的成功之處給以積極的評價,但是,如果把他們放在20世紀文學的整體格局中進行理性的反思與藝術的審視,又會發現其思想性格上諸多的相似之處。如果說前一個階段作家對這一系列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多地指向人性的負面的話,那么,新時期家族小說對封建家長的刻畫則注重開掘其思想性格的積極內涵與人性美的光輝,相對淡化其作為反動階級的劣根性,流露出反其道而行之的傾向,這同樣說明作家創新能力的欠缺。如果單就某一人物來看,那的確體現出作家藝術上的創新探索,但如果同一時代的作家都表現出大體一致的審美意蘊,這也同樣顯示出一種藝術上的惰性與創造上的雷同。
接受了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青年一代在人的意識覺醒之后,與專制家長之間發生了尖銳的思想沖突,最后離家出走成為貴族家庭的叛逆,從而構成當代家族小說中不可或缺的叛逆知識分子的形象系列。在1950~1970年代一體化的文化格局中,叛逆知識分子呈現出兩個不同的人生選擇,一是走出家庭之后經過艱難的人生選擇走向革命之路,一是經過短暫思想激進的反叛之后最終走向對所屬階級的妥協。而到了新時期家族小說創作中,有關叛逆知識分子的書寫較之十七年時期表現出較大的藝術進步,在敘述的比重上有明顯的增加,但敘事模式上并未實現新的突破。無論是《白鹿原》中的白靈、《家族》中的寧珂,或是《故鄉天下黃花》中的孫實根、《最后一個匈奴》中的楊作新,他們反叛家庭走向革命的原因盡管不盡一致,但思想信念的堅定與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卻遠遠超過一般革命者,寧肯犧牲自己的家族利益甚至為此背叛自己的親人也在所不惜。即使如此,在革命大家庭中,這些叛逆知識分子仍然是一個“他者”,始終沒有與革命領導者結成為感情和命運的共同體。相對于他們對舊家庭決絕的反叛,他們所屬的家庭出身與血緣親情,卻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為其排憂解難,甚至是拯救了他們的第二次生命,然而,這反倒成了他們終身難以擺脫的“夢魘”,他們被自己忠貞不渝的領導與革命組織所懷疑甚至成為革命事業的異己,人格的侮辱、精神的折磨與肉體的蹂躪使其無法忍受。他們對革命的終身未悔與最終悲慘的結局,呈現出叛逆知識分子心路歷程與命運抉擇悲劇的相似性。
在十七年時期的家族小說創作中,作者賦予農民革命者更多的無產階級進步的思想性格,對其作為舊時代農民所受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而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造成農民英雄人物塑造的“理想化”色彩,甚至走向后來“高大全”式人物的出現。而到了新的歷史時期,家族小說創作中因作家啟蒙視角的滲透,農民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改變了以往的神化色彩,轉而對其身上所蘊含的落后、狹隘、自私、暴力一面進行冷靜的審視,較早出現的是《西望茅草地》中的農民革命者張種田,《桑樹坪紀事》中宗法式家長李金斗,《古船》中趙氏家長趙炳。在他們身上,我們再也看不到作為革命者思想上的先進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人性的善與人情的真,取而代之的是狹隘自私的農民意識,專制保守的封建思想,黨同伐異的宗法觀念。隨后出現在《舊址》中的“陳狗兒”、《罌粟之家》中的陳茂、《故鄉天下黃花》中的趙刺猬、賴和尚,成為農民革命者的人物群體,他們貌似“革命性”背后彰顯的卻是“流氓”無產者的性格。如果說十七年時期作家對農民英雄的塑造側重的是革命性的張揚,那么上世紀末家族小說中出現的農民革命者則呈現出作為農民本身的宗法性與生命本能,同樣是正負對立的兩極剖面。對農民革命者的書寫從理想化塑造一味走向原生態還原,顯然是一種類型化的表現。
二
當代家族小說人物塑造上的類型化不是一個單獨的文學現象,它與敘述者建構故事的雷同化傾向相互交織在一起,盡管在不同的家族小說中作家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審美經驗,不同社會空間、文化語境中的“異域風情”,不同家族在時代變遷中的興衰沉浮,但小說的情節原型卻并未出現實質性的變化,它們都是一個故事原型的不同變體,作家對同一個故事的幾種不同寫法。在追求個性化的創新時代,卻讓讀者看到他們創造性背后的相似和雷同。
為反抗封建家長的包辦婚姻,一代知識分子與舊家庭決裂后離家出走參加革命,在獻身革命追求民族與階級解放的過程中,他們無法回避自己愛情上的抉擇,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最后都難以擺脫情感的誘惑,成為革命加戀愛的形象注解。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文學的創作母題在當代家族小說創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在《白鹿原》中的鹿兆鵬與白靈之間,《舊址》中的李乃之與白秋云之間,《家族》中的寧珂與曲纟青 之間,《最后一個匈奴》中的楊作新與趙小姐之間,《第二十幕》中的蔡承銀與栗麗之間都重復著革命的驚心動魄與愛情上纏綿悱惻的傳奇故事。男性革命者對革命的堅定不移與獻身精神,非凡的意志和遠大的理想成為吸引女性的主要誘因,女性那種天然淳樸的美,對感情忠貞不渝的真,在生活中不計個人得失厚待同類的善,尤其是對男性所從事革命事業的支持贏得了對方的好感。早在十七年時期家族敘事性作品《三家巷》、《紅旗譜》中的革命者身上就彰顯出這種美好的愛情作為革命者動力的美好情愫。新時期家族小說中叛逆知識分子的愛情一樣延續著左翼文學革命加戀愛的模式。在這種戀愛的過程中,率先投入愛河一往情深的往往是美若天仙的女性,正是她們主動大膽的進攻才引起對方的注意甚至是感情上的青睞,他們之間的感情少有世俗的功利,而多是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盡管這種感情并沒有完全實現“終成眷屬”的理想,但都不會影響他們內心深處對情人的牽掛和忠貞。不管雙方面對革命與愛情如何選擇,女性都為這份真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少有理想的歸宿,這或許是革命與愛情之間的矛盾所在。
在封建貴族家庭中,長工無疑是家庭中被雇用的角色,處于社會的最下層,與主人之間存在著地位上的差別與人格上的不平等。如果從階級的視角來看,他們之間顯然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十七年時期的家族敘事無一例外地彰顯著鮮明的階級意識。新時期家族小說在寫人時實現了從階級意識到人道主義的超越,作家開始從人性人情的角度重新審視封建家庭中的主仆關系,發現二者之間除了身份角色之間的地位差異之外,也一樣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同情。較早的表現主仆之間真摯感情的是莫言的《紅高粱》,敘述者“我”對家族中的長工羅漢大爺對東家的赤膽忠心備加稱贊,同時期的《古船》也寫到少爺與女傭之間由同命相憐發展到男女之間的戀情。而在這方面描寫較為成功的則表現在《白鹿原》中白嘉軒與鹿三之間,在陳忠實筆下,這種關系超越了正常的主仆差別而發展為一種兄弟情誼。這種建立在仁義基礎上的主仆關系凸顯了民族傳統美德的發揚光大。這一情節內容在1990年代的家族小說創作中絕不是個案,在《家族》中的曲府大院之中,《舊址》中李氏家族的九思堂,主仆之間往往體現出儒家的仁愛美德。
在新時期家族小說中,不同階級之間并不都表現為超越階級之上的人情之美與人性之善,畢竟在不同階級之間既有生存在相似時空的情感聯系,更有出自不同階級立場的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在常態環境中由于受到社會地位與傳統倫理的約束而處于被壓抑的冬眠狀態,可是一旦處于統治地位的貴族階級成為階下囚的話,往日的積怨與屈辱開始借助革命暴力得以集中釋放,其人性的張揚因缺少理性的制約而發展成為獸性的泛濫。《舊址》中農民赤衛隊首領陳狗兒在1927年的農民暴動中,對女性的報復性占有遠遠超過階級翻身的界限,而成為赤裸裸獸欲的滿足。問題是像陳狗兒這樣的革命者不是個別的典型,出現在《罌粟之家》中的陳茂,《古船》中的趙多多,《故鄉天下黃花》中的趙刺猬、賴和尚,他們作為農民翻身的革命領導者皆重復著與陳狗兒相似的劣跡敗行。《家族》中身為革命領導者的殷弓對敵手戰聰的仇恨,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階級立場的對立,而是源于人性的嫉妒。作為敵人的戰聰,無論經歷、出身、學養還是八面討好的名聲,都體現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完美,這是殷弓執意要摧毀和打碎的原因之一。“從殷弓的內心深處來看,其革命動機似乎總是糾結著自身條件處于劣勢地位所故有的因自卑而生的變態報復。”[1 ]這種變態式的報復不僅體現為個別的農民革命者,而表現為家族敘事中一個不斷重復的情節要素。
三
當代家族小說中人物的類型化、情節故事的雷同化又與文本結構設置的模式化相伴隨。1950~1970年代那種社會進化的結構模式被新時期家族歷史書寫的歷史循環論所代替。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中,那種必然性的歷史要求與現實無法實現之間的沖突已經淡化,代之而來的是偶然性的事件影響了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不僅不同的歷史階段出現驚人相似的一幕,就是生活中不同尋常的經歷也不斷地重復著,從而造成整個家族小說結構上重復性敘事的藝術傾向,這不再局限于個別作家的無意識選擇,而發展成一種宏觀的審美走向。
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作為村落家族史的代表作品,敘述了馬村從民國初年到“文革”之間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小說選擇了民國初年的村長被殺、1940年日本來了、1949年的翻身解放、文化大革命四個典型的年代來解剖馬村歷史背后的隱形結構,作者發現馬村的歷史都是頭人們爭奪村長權力的歷史。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利欲望,各個家族、宗派之間往往流血犧牲,傷及數人,勝利者是頭人,而愚昧的百姓成了無辜的受害者。村落與家族史都在重復同一個規律。劉震云小說中出現的家族與歷史敘事結構上的重復,在周大新的家族小說《第二十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第二十幕》以尚吉利織絲廠五代人振興祖業為主線,突出再現了在社會動蕩中尚家不斷重復的“破壞”、“建設”、“再破壞”、“再建設”的歷史宿命悲劇,正是在尚吉利織絲廠的發展與權力政治的沉浮之中,小說展現了尚家作為民族工商業者歷經坎坷終不悔,執著如一謀求發展的堅韌的家族精神,政治與家族、歷史與人的命運之間互相影響,異形而同構。
如果說十七年時期的家族敘事采用的是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模式,借以凸出不同家族之間矛盾的階級立場,那么,新時期的家族小說則“陷入了另一種二元對立的模式,那就是兩個家族作為不同的利益共同體的對壘。白嘉軒與鹿子霖作為道德兩極的對抗,前者的仁義與后者的丑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反差”[2 ]。這種家族之間的矛盾對立又與政黨之間的政權斗爭始終交織在一起。革命與反革命一正一反構成二元對立成為多數家族小說的結構模式。土改中貧農團的激進鎮壓終于導致還鄉團的血腥報復,貧農團反過來更是對其家屬無以復加的摧殘,這在《古船》、《故鄉天下黃花》、《繾綣與決絕》中都重復著類似的結構。
從人物的塑造、情節的營構到結構的設置,當代家族小說創作都表現出鮮明的時代風格,在看似追求藝術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在長篇家族小說取得令人可喜成就的20世紀末,在被讀者與批評家視為文學經典的文本中,在作家紛紛表明自己文學獨特的個性追求時,我們卻從眾多同一創作母題的不同書寫的文本背后,看出了話語背后共同的結構、故事、人物的原型。這既是不同作家對同一原型母題的誤讀,也可視為作家難以擺脫的藝術局限,自然也昭示出在倡導創新時代話語中作家原創性的匱乏。
參考文獻:
[1]路文彬. 歷史想象的現實訴求.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263.
[2]黃發有. 準個體時代的寫作. 上海:三聯書店,2002:132.
編輯 葉祝弟